徐梵澄:圣人的虚静05
梵澄拒绝按“宇宙论”式的形而上学诠解《老子》,并非比照犹太经学,而是依据某种中国“哲学”:“就哲学言,绝对之无盖不可有”(页15)。将老子玄学化的王弼被当今的哲学史(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人民版1998,页650)定性为形而上学大家,梵澄则以为,王弼虽然大谈“有本于无”,实际上要说的恰是“绝对之无盖不可有”。似乎基于这样的中国哲学,梵澄才进一步以西洋哲学参证所谓“就哲学言,绝对之无盖不可有”。梵澄区分了西方两类哲人──古典类的(柏拉图、康德)和现代类的(思辩哲学),并且断言老氏近西方古典类哲学,“非如近世之纯思辩哲学,未为经验论所范围”(页101)。既然梵澄没有说老氏学是形而上学──像通常人们说柏拉图或康德哲学那样,而是说“精神哲学”。柏拉图或康德哲学何以是一种“精神哲学”?梵澄“适可而止”,没有讲下去。
用西洋哲学观来诠解中国古典思想文本──所谓经典,几乎是现代中国思想的世纪性特征。正如不难看到的那样,如此对中国经典的西化诠解──无论新实在主义、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新老马克思主义、弗洛依德主义抑或海德格尔主义的诠解,不少时候让人觉得实在有点过份。比如陈寅恪先生曾经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这话几乎已经成了金科玉律,经常被当作学术权威来引用,很少有人想一想大师会不会把柏拉图搞错了。直到前不久,才有人(肖殷,〈“老任务”的新世纪?〉,载《书屋》,3【2001】))出来说:
希腊词Idea的日常含义是“外观、外貌”,与动词idein是同一词根,都有“看”的意思。柏拉图就提到,悲剧诗人阿迦通“看起来非常俊”(tend’ounideanpanukalos,《普罗塔戈拉斯篇》,315e)。Idea的较为抽象的用法是“种类”、“形式”,苏格拉底在同友人讨论各种政体时问:“你还能提出任何其它形式的政体吗?”(etinaallenekheisideanpoliteias?《理想国》,544c)。最带有今人所谓Idea意味的,是苏格拉底说;“善的Idea是最大的知识问题”(Hetouagathouideamegistonmathema《理想国》,505a);“Idea是思想、而非看见的对象”(tasd’…ideasnoeisthaimenhorasthaid’ou《理想国》,507b)。无论哪种含义,都与“三纲六纪”八竿子打不着边。“三纲六纪”可能更接近希腊的所谓nomos,这个词的意思是成文法、习惯法、习俗,苏格拉底所谓:“每一种统治都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法律(tithetai…tousnomoushekastehearkheprotohauteisumpheron),平民政府制定民主法律,独裁政府制定独裁法律,依此类推”(《理想国》,338e)。司马迁说,“有国者”、“为人臣者”、“为人君父”者、“为人臣子”者,都得通《春秋》之义。为什么呢?“《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史记、太史公自序》)。
儒学不是“理念”哲学(形而上学)──也不是宗教(神学),而是礼法学,有如犹太经学既非哲学、也非心性学,而是律法学。国学家讲国学不懂分寸已久。梵澄不属于这类现代化的中国哲人,参证西洋哲学诠解中国古学时,他懂得守分寸,“适可而止”。
梵澄似乎没有一次说老氏学是“政治哲学”,而是说“精神哲学”,此外还至少两次说到老氏的“历史哲学”。与梵澄萦萦于怀的“精神哲学”有关系的因此可能并非“政治哲学”,而是“历史哲学”。什么样的关系?梵澄“适可而止”,没有明讲。
我们如果要搞懂梵澄的“一系精神哲学”,显然不可放过这样的问题。麻烦的是,在没有搞清楚为什么对于梵澄来说所谓“古之道术”就是今天所谓“精神哲学”之前,没有指望可以搞清“精神哲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
《老子》五千言虽然显得芜杂甚至不成条贯,毕竟有一个基本题旨或者说写作(编辑)意图。如果《老子》五千言主要讲的不是“宇宙论”的形而上学,要讲的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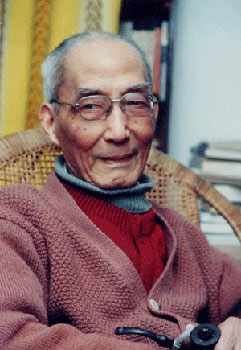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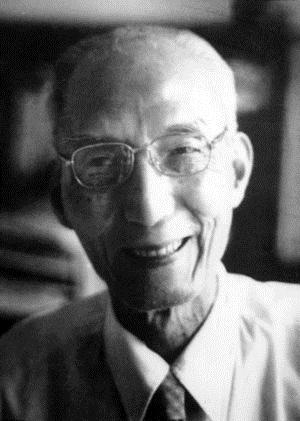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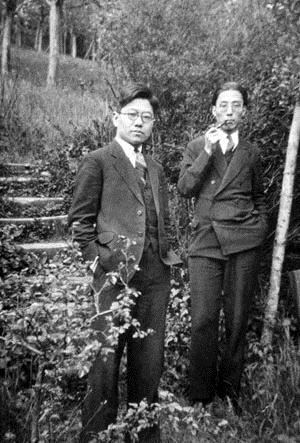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