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梵澄:圣人的虚静06
梵澄多次提到,《老子》一书为“侯王”而作,“侯王”就是“圣人”(页23、24、50、59、101)。“道经”章首句中的“道”,在梵澄看来,就是现世王者“化天下”之“道”(页3)。按梵澄的诠解也许可以断言,《老子》五千言的基本题旨或者说写作意图当是救济天下的政教之术。可是,这样一来又如何与梵澄所谓的老子“哲人”身份相一致?在梵澄眼里,究竟何谓“哲人”?要搞清《老子》五千言的写作(编辑)意图,不仅得弄明白谁在说、说的是什么,还得搞清楚它预设的言说对象是谁。也许可以说,搞清写作意图与搞清楚预设的言说对象同样重要、甚至是同一个问题。这些问题对老子的“哲人”身份问题非常重要,也对我们要弄清楚梵澄所谓老氏“精神哲学”的含义非常紧要。
据统计,《老子》中“圣人”一词凡二十五见,还有“我”、“吾”一类主词(凡二十四见)──“只有圣人、圣君方敢当其称”(尹振环前揭书,页114注释),加起来共四十九见。是不是可以由此断定,《老子》作者意识到自己是圣人,而预设的听者对象则为同“道”──也是圣人?倘若如此,《老子》就是讲圣人的书,或者说,是圣人写给圣人的书。梵澄多次用“哲人”称老氏,又一再说《老子》是为“侯王”而作,如果《老子》中的“圣人”就是“侯王”,或者反过来说,为“侯王”者首先应当是“圣人”,是否可以说,《老子》五千言讲的是如何当侯王,是侯王写给潜在的侯王的书。
这样说来,“一系精神哲学”,其实是当“侯王”的哲学。在说“朱、陆并尊”时,梵澄说“朱子之可尊”,不仅因为他是伟大的教育家,也因为他是“很能干的政治家”,“朱子平生的心力,是至少一半耗费在政治上了”(《陆王学述》,页23-23)。说梵澄的“精神哲学”就是古之道术“,错不到哪里去。但怎么又说是“历史哲学”?“历史哲学”也是“古之道术“?倘若“精神哲学”与“历史哲学”都是“古之道术”,何以要多此一举,标举两种“哲学”之名?
还得先搞清梵澄称老氏为“哲人”是什么意思。中国古代没有“哲人”之称。梵澄说《老子》中的“圣人”(“侯王”)就是“哲人”,是否意味着西洋所谓“哲人”就是中国古代所谓的“侯王”?这不是笔者也想来参证一番西洋,而是梵澄在参证。幸运的是,这一次梵澄有明确说法:老子理想中的治国之人就是“圣人”,“与古希腊哲学言圣王”相同(页33)。
古希腊哲人中谁在讲“圣王”?业内人士都晓得,是柏拉图在大谈所谓Philosopher-king。柏拉图在说到“善的Idea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和“Idea是思想、而非看见的对象”一类话题时,谈话背景的主题正是:哲人是否应该“当城邦的领袖”(《理想国》,468b)。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对这问题的回答起初满犹豫,因为他觉得,“大多数哲学家变坏是不可避免的”(《理想国》,489v)。尽管如此,苏格拉底还是认为,如果“极少数未腐败”的哲人治理城邦的话,“无论城市、国家还是个人才能达到完善”(《理想国》,499c-d)。说到底,在《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看来,“极少数未腐败”的哲人治理城邦毕竟理想而已。懂西学的梵澄对此显然知道得很清楚:“倘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岂不可期郅治?然此理想而已,自古未尝见于实事,东西方皆然”(页5)。“古之道术”之所以堪称“精神哲学”,意味着统治者或治人者自己首先得有成圣的功夫。称老氏为“哲人”,意思恐怕是说,虽然《老子》书讲的是“南面术”,但“南面”者首先得是“圣人”。
如果梵澄先生还在世,我想他一定不会对我在此提出一点儿异议不高兴。贤者在位“自古未尝见于实事”,恐怕不符合先生崇尚的儒家教诲。按我所知道的儒家教诲的一点皮毛,儒家向来称颂三代为圣王之治。可见,贤者在位并非“自古未尝见于实事”──无论考古家如何考证,贤者曾经在位至少是儒家相信的历史事实。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古代的“哲人”(圣人)可能并非柏拉图的“哲人-王”。因为,“哲人”在中国古代政体一开始就在“王位”,而非柏拉图的“哲人”想是否应和如何得王位。周公无疑是儒家的圣王,不仅是理想中的,也是历史事实上的。当年周公见到举国上下耽于宴饮,忧心如焚,发了篇禁酒通喻(《尚书、酒诰》)。其中说:“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自成烫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在这里,周公开出了历史上值得称颂的圣王清单,称为“先哲王”(【按】“今文不以帝乙为纣父”。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中华书局1989,页324-325)。所谓“哲王”,就是“畏天明命,下及小民,惟行其德,执其敬”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1986,页378)。“哲”的原初含义就是畏天明命、惟行其德,这不就是梵澄先生所指的“精神”?
梵澄作《老子臆解》时已经年过七旬,年纪大了下笔很可能走神。实际上梵澄当然知道“一系精神哲学”源于先王:“精神哲学溯源当在孔子以前,易经时代或当殷之末世”(《陆王学述》,页22)。“睿哲”本来就是用来描述圣王舜的(《尚书、舜典》:帝舜“睿哲文明,温恭允塞”),中国的“哲人”原祖不是像巴门尼德那样写教诲诗、或像苏格拉底那样耍嘴皮子、或像柏拉图那样写戏剧的人,而是像周公发诰示那样制礼作乐当王的人──文王演八卦,“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孟子、离娄下》)。春秋之际,“哲人”与王位分离,才有了“哲人”要当王的问题出来(孟子所谓“诗亡然后《春秋》作”,公羊子所谓孔子“以春秋当新王”),那是后话。如果史迁说孔子向老子请教“礼”是真的,再看《老子》中的言论是圣人(侯王)写给圣人(侯王)的,起码在老子的时候,圣人(“哲人”)与侯王的身份还没有德位分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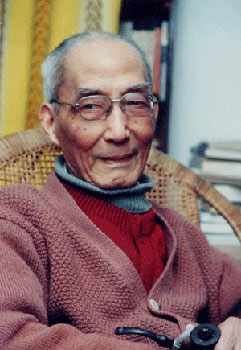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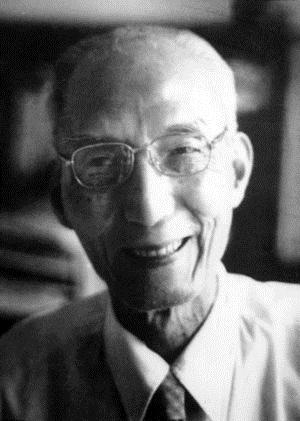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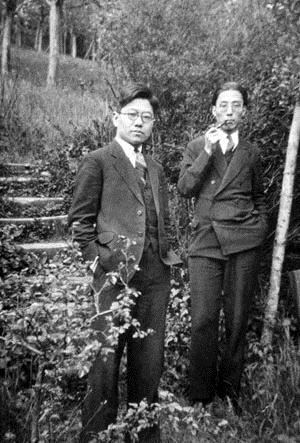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