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梵澄:圣人的虚静08
老子不是主张让百姓自治吗?
一心系于“精神哲学”的梵澄晓得,“化天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平民,上品君子少。其下品极恶者,亦少。为不善,为不信矣”──好象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说过大致差不多的话(参见《高尔吉亚》篇)。梵澄接下来说,“将与之争变诈之智,凶暴之为,以惩其不善不信,如今日之欧、美乎?”看来,梵澄不那么欣赏如今欧美的自由民主制,那不是“化天下”的政体。现代的自由民主政体让人闲放安佚,梵澄用老子的目光看到,“闲放安佚之辈多,奢靡淫逸之风盛,变诈巧怪之智起,盗贼劫杀之事生”(页82、86)。“化天下”当然是要治民,因此首先得有能“化天下”之人(侯王),这就是为什么“精神哲学”是首要性的。所谓老子教诲的侯王无为,不是不施治,而是让民被治时感觉不到自己在被治──这才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治(“化天下”):潜移默化平民于不知不觉之中,让“下品极恶凶顽刁诈猾贼之风”自然而息(页71)。如此说来,侯王老子的无为之治无异于模仿先哲王所谓的“玄德”(《尚书、舜典》:“玄德升闻,乃命以位”)。
经上有“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知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也”。梵澄诠解说,这意思是:不要让人民知道他们不该知道的,不让人民欲求不该欲求的(参见页6)。《老子臆解》多处提到“近代西洋文明之病”(页16、71、82),指的就是让人民知道了不该知道的,进而使得人民欲求不该欲求的。纵情声色是现代病,梵澄说,老子的圣人-侯王统治就是要“去其浮华而崇实际”(页16)。这不等于违背人民的某些自然欲望?梵澄的意思一点不含糊:“老氏之教,尚清虚寡欲。学人之所不学,以反众人之所为”(页95)。可是,不顺从人民的某些自然欲望,绝非等于圣人-侯王不爱民。梵澄看得很清楚:圣人-侯王的潜行不宣的统治(“玄德”)说到底是养民──老子所谓“爱民活国”(页14)。关键在于,“爱民活国”得有“术”──隐恶扬善之术:“古今中外,恶终不能胜善。然则化之必以善物。究其极,且将如舜之隐恶而扬善”(页71)。要隐恶扬善,首先得区分善恶。谁能区分?“百姓诚不能皆信皆善,生有不齐,品质殊异,才器各别,均之皆为中等,视为上者之倡导而转移”(页71)。没有尧、舜、周公一类圣人-侯王,隐恶而扬善的“化天下”何以可能?由此可见,圣人-侯王在得位之前的修养功夫何其重要。“立德行道,必先修于其身,先体验之以明其真伪也”(页78)。既然如此,虽然中国古代的“哲人”从历史上说一开始就在王位,从义理上说,柏拉图的“哲人”何以应该为王的问题依然在先──礼法学还得为“精神哲学”先留地盘。
梵澄不欣赏欧美的自由民主制,不等于反对或不赞同自由民主制本身。
经上有“古之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也,以其知也”。通常这被看作老子倡“愚民政策”的铁证,而“愚民政策”在今天等于骂人话,梵澄却似乎努力要理解侯王老子的用心:“不以智为国,而天下庶可休息于小康”(页96)。梵澄并非不识人间烟火,晓得现代化后“民智已启”。所以他说:既然民智已启,索性开民智到底,让民达到“大智”,这样就可以“使其自治”(页96-97)。让民达到“大智”,按“精神哲学”的理解,是不是要让民都成为圣人?人人可以成圣人,不正是宋儒的主张?的确如此。正因为如今已是现代民主时代,梵澄才觉得“有重温此宋明精神哲学之必要”(《陆王学述》,页16-18)。梵澄没有说老子学是政治哲学,看来有道理。说到底,梵澄还是恪守了现代的“政治正确”──赞成自由民主制。
为什么又说老子学是“历史哲学”?在海德堡大学学过哲学的梵澄,肯定不会不晓得,这个术语是德国近代哲学的发明。梵澄所谓“历史”说的既非西洋历史、也非黑格尔所谓“普遍历史”,当然是中国的“历史”。但什么意义上的“历史”──而且还“哲学”?
史书上传说老氏学“自黄帝始”,梵澄讲老子深谙《易》理(页32),有论者考证,《老子》是《尚书》的延续(尹振环前揭书,页247-260);《易》和《尚书》为先哲王所作,老氏书是侯王写给侯王的,与儒家经书一样,原本是圣王术的门道。梵澄说老氏学是“历史哲学”,指的是《老子》书有圣王血统(“历史”)?
又或,在如今的哲学史书上,老子多被说成与儒术对立的黄老之术,但在梵澄看来,其实这两种术在本义上相同,都讲究“以百姓之心为心”:儒家的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就是老子的“百姓治百姓”(页70)──其实都源于先哲王的“玄德”。老子的“道”是圣人之“道”,虽然无以名之,其实不外“远以治国,近以修身。治国,以谓任其道则万物宾服,人民不待法令而自然治平也”(页46)。老子是孔子的老师,这件事情据说已经坐实。孔子编辑六经无异于整理侯王书,孔子向老子请教礼,说明老子与孔子有授受圣王学的关系。梵澄说老氏学是“历史哲学”,指的是老氏学与孔学的如此“历史”关联?
既然孔子编辑而非作六经,孔子的身份已经与老子作《德道经》五千言的身份不同了。老子还有王位,孔子已经没有王位,这是否就是老子与孔子的根本差别──甚至经学与子学的决定性差别?如果的确如此的话,这难道不可以看作圣人失去王位或者说圣人的生存位置发生转变这一历史事件的后果?今文家坚持说孔子“作”六经,意在把孔子重新推上王位;即便如此,今文家说孔子为王指的是有德无位的“素王”──由此可证圣人-侯王的德位分离乃周秦之际的重大历史事件。梵澄似乎以为,老子很清楚这段历史的实际含义:“春秋之世,弒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此必有老氏所见、所闻,或闻于传闻者也。以哲人而处此,必思所以息纷争,止战祸,而安中国”(页89、111)。如果圣人在王位或者在先哲王的时代,想必不会有这样的春秋之世。所谓“历史哲学”,因此很可能指圣人的虚静之学──“精神哲学”在德位分离的历史事件中发生的重大转变。倘若如此,便需要进一步深究:“精神哲学”经历了什么样的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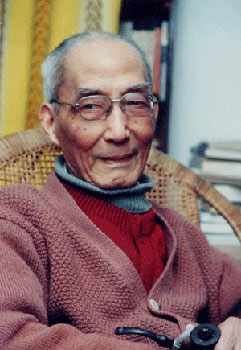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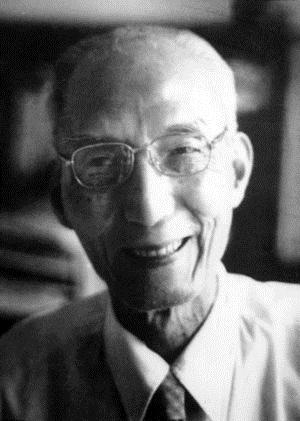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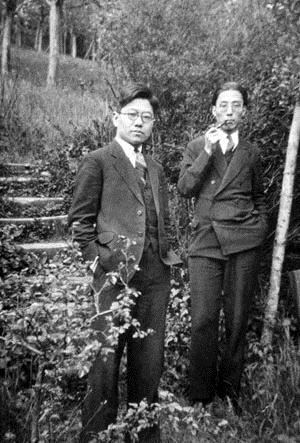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