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梵澄:圣人的虚静09
《庄子·天道》篇起首讲到虚静为“帝王之德”,与《老子》书中的说法完全一致,而且明确说到,这就是先哲王的“德”(“明此以南乡,尧之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可是,《天道》篇接下来说,虚静这一原本仅仅是处于在上之位的“帝王之德”,现在也可以是处于下位的人“之德”,甚至可以是“退居而闲游”者或“进为而抚世”者“之德”。差别在于,圣人处于上位时,虚静便是“帝王之德”;如今,圣人处于下位,虚静便成了“玄圣素王”之德。德位分离以后,虚静之德没有随王而去,而是由圣人葆守之。谁都清楚,“玄圣素王”分别指老子和孔子。两子在这里并称,显得不那么恰当。老子仍然在上位,可以说是承先哲王的后哲王,因而是“玄圣”;孔子已经处于下位,不再是哲王,至多是潜在的哲王(素王)。但是,“玄圣素王”的说法,不正表明了圣人-侯王的德位分离?古人不大可能随便把老子和孔子摆在一起,今天的我们看“玄圣素王”的并称不太恰当,对于《天道》篇的作者来说,却可能有深意──“历史哲学”的含义。
经历过晚周时期重大的政治事变,圣人的生存位置发生了根本变化。无论圣人在历史中的生存位置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圣人必须葆有“致虚静”的“德”,否则,圣人不复为圣人。然而,晚周“历史”之后,圣人是否有王位,已经成了历史的机缘,“精神哲学”因此必须成为“历史哲学”──如此“历史哲学”可以说与在近代欧洲出现的“历史哲学”(从维科、赫尔德到黑格尔、马克思)风马牛不相及。
在论“为何与如何”“重温宋明精神哲学”时,梵澄讲到现代儒生(马一浮、熊十力)甚至皈依佛门的欧阳竟无致力复兴宋明学的事情,说他们都“感觉到了民族的生死关头,还是孔、孟之学有益”(《陆王学述》,页19)。这是否意味着,宋明学其实也应该称为“历史哲学”?无论答案如何,“历史哲学”本质上仍然是“精神哲学”。因为,梵澄接下来说,毛泽东在现代之际还主张世界的王霸之辩(“广集粮、不称霸”),与孟子的义利之辩一脉相承。
听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有这么一件事情。一天,毛主席邀请几位民主派耆老到家中茶叙,有位耆老忽然壮起胆子问:如果今天梵澄的老师还活着,会怎样?主席笑瞇瞇地回答:要么他识时务,要么请他去该去的地方。
这故事八成是编出来的,姑妄听之。但什么叫“识时务”?或者问,“历史”之后,“精神哲学”该是什么样子?
处于“精神哲学”转变为“历史哲学”的关头──从先哲王过渡到素王的历史时刻,《老子》书已经大讲圣人“识时务”,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圣人的智能是“道”,其貌如水一样平静──老子善用比喻,“水善利万物而有静。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老子》书中大量类似的话表明,老子很可能已经意识到圣人的生存位置发生了变化。相当明显的是,如果圣人仍然是侯王──处于上位,何以会有“居众人之所恶”的问题出来?
梵澄对老子讲的圣人在人世不可与人争的话非常在意,多次提到圣人的虚静现在应该是“能挫人之锐气,解人之纠纷,和众之光明,同众之尘垢”(页6,参页10、98)。“精神哲学”转变成“历史哲学”的样子,意思首先指圣人已经失去王位,已经“居众人之所恶”,因而,圣人必须善于隐藏自己的才智。梵澄缘引古训“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页60)来诠解老子的话,但“深藏若虚”不仅因为“明哲保身”是圣人的天性──圣人懂得知人知世可能祸及自身(页75);更重要的是,才智这种东西对于人民来讲有害无益;“人未有无明无智而能为恶者,其为恶,乃用其明其智之不当耳”(页39)。即便到了当今的民主时代,这问题依然还在,甚至更为严重,因为“民智已开”──“如今西方的犯罪者,很少是无知无识的人,多是知识分子,而且精明能干,技术高强”(《陆王学述》,页49)。梵澄甚至明确表示赞同陆象山的看法,对有的人不能“以学问传授之”,否则无异于“假寇兵,齍盗粮”。联想到《老子》书中那些被指为所谓“愚民政策”的话,可以推想,虽然《老子》书是侯王写给侯王的,但老子已经意识到,能读书的已经不仅仅是有才器成圣之人了。
圣人与民众不同,主要因为对幸福的理解不同。民众有自己的“迷信”,举凡“卜莁也、星命也、风水也,繁多猥琐,不可究诘。……凡此皆正道之反,善德之妖也”;但之所以这类“迷信”“迄今两千数百年亦未拔”,都因为生死祸福问题乃百姓的首要大事(页84)。圣人之所以“异于庸人”,就在于不依生死祸福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尽管如此,圣人智能并非超然尘世,而是在尘世之中;这意思是说,圣人已经不是侯王,而是“居众人之所恶”。圣人如何与众人相处的问题就来了──“精神哲学”因此得像“历史哲学”的样子。经上有“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解其纷,是谓玄同”(“玄”者,隐而不宣也),梵澄解释说,“和其光”就是“不自耀于众”,“同其尘”就是“与众同其忧乐”;这不等于与尘世同流合圬,而是“内中有主”、大智若愚。到了孔子,圣人对此“玄同”的自我意识更明确──孔子所谓“和而不同”(页81、84;顺便说,对于所谓“和而不同”,庄子可能得其正解)。从老子到孔子,完成了从“精神哲学”到“历史哲学”的转变,而且圣人的写作方式明显变了──孔子作《春秋》、撰《孝敬》──到司马迁,索性只写史书,史学从此成为中国“哲学”之大宗。
梵澄先生回到北京后,一位编文化时报的青年友人请他“继续写点当年为《申报》自由谈写的那类杂文,并建议把当年的文章结集出版”。梵澄回信说:印度独立后,一位老一辈革命党人还“欲登坛有所言”,遭到尼赫鲁总统制止。
日月出矣,爝火不息;刻舟求剑,其可得乎?时过一甲子,而足下犹以“自由谈”为言,陈年日历,何所用之?若谓陈言犹不无可采者,此则依乎所言是否尚有真理。斯可见于学术派与新闻派之辩。(引自陆灏前揭文)
圣人的“虚静”──“一系精神哲学”在梵澄不是身体力行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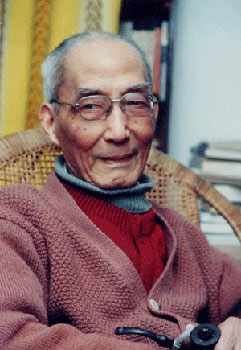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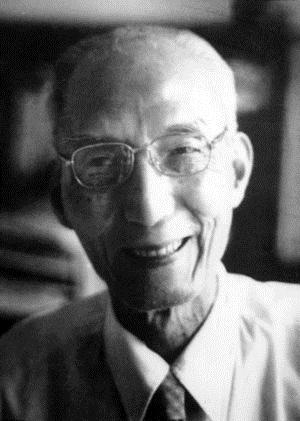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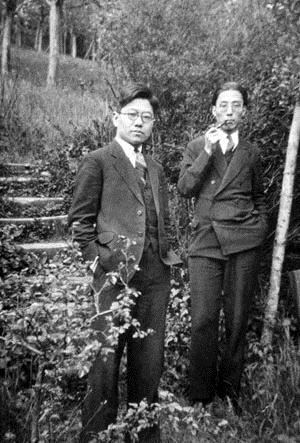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