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国回来的父亲摸了一下我的头就洗手去了
现在感到奇怪,我竟不记得那天的团圆饭是怎么吃的了。只记得那天晚上,父亲一直站在叔祖父的床前,恭立伺候,身上已经换上了长衫,但并没有说什么话。后来,叔祖父一挥手说:“歇着去吧!”父亲才轻手轻脚地从屋里退出。此后每天晚上都是如此。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于父亲怎么和母亲话说阔别之情,又是怎么度过分别十二年后的第一个夜晚的,我当然不得而知。但从母亲第二天那木讷的表情来看,那一夜恐怕并没有什么幸福可言。从那时起,父亲就演起了舍情求仁的悲剧来了。
空闲时父亲问我在哪个学校念书,几年级了,并爱抚地摸了摸我的头说:“怎么不把头发留起来?像个当兵的。”那时我是在正谊中学读书,父亲也在那里念过书,我们是校友。小学我们都上的是三和街小学,也是校友。我长得圆头圆脑,胖乎乎的,浑浑噩噩只知道玩耍,对于功课很不上心。当时男孩子都是光头。如果谁留洋头(分头),那倒是一件出风头的事。可是父亲有令,我只得留起洋头,还照了个相片寄给他,才算了事。记得父亲在摸了我的头之后,立刻去水缸里掏舀了一瓢水冲手,使我感到很新奇。但他从来没有亲过我或拉过我的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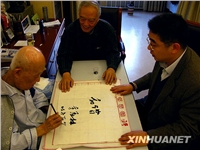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