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珈四季念师祖——深切怀念马克昌教授
何荣功
一
曾有一位武大校友这样描绘武大校园之美:“每年一至二月校园各处的白玉兰,满树银装。三月樱花大道洁白如雪;坡地上、挡土墙边伏地状生长的迎春,连翘开出串串黄花,拉开了春天的序幕。四月至五月间,运动场旁,湖边道上,桃花盛开;中心花园蔷薇科、木兰科植物群芳争艳,给校园的春天带来生机。六月至九月,高大的乔木,浓荫蔽日,洒下片片荫凉;石榴、紫薇、荚竹桃等夏季花木,为绿色的校园增添了色彩。十月来临……”
其实,武大之美,绝不仅在于四季之美、校园之美;更在于其有大学神韵,人文之美,有大师成全其美。
不知为何,我内心深处一直十分向往法学。2000年本科毕业时,我毅然放弃了哲学专业保研,破釜沉舟,转考了刑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从此正式成为“马家军”一员,有机会目睹先生的风采,恭听先生的教诲。那时,每次见到先生都使我兴奋不已。三年后,我又考取了刑法学博士研究生,开始有更多机会走近先生,
2006年博士顺利毕业,在先生和莫老师极力举荐下,我到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继续深造。那段时间,先生去北京很频繁,每次赴京,先生多半会到“师大”。由于我的“双重身份”,我和雨田师兄多有机会被安排照顾先生。2008年6月博士后出站,承蒙先生和教研室老师们的厚爱,我重返武大,回到先生身边工作。“近水楼台先得月”,沐浴先生教诲的机会就更多了。
先生在因“肛瘘”手术住院前,身体一直很康健,从不知疲倦。为了国家学术发展和法治建设,经常外出参加各种会议。考虑到先生毕竟年事已高,为先生健康、安全计,2005年以后,先生每次出差,
现在回想起来,
二
先生开创了武大刑法学科并推至盛世。先生深知要保持学科的可持续发展,须着力培养后辈年轻人,所以,他对晚辈,特别是年轻人的成长寄予重望,费尽心血!
上午9点,我按
直到今天,我仍记忆犹新:进门后,先生让我坐下,并端出水果和小点心让我吃。说心里话,当时我哪有心思吃水果和点心呀!先生对我来说,是“高山仰止”的人物。先生家是什么样的?像先生这样的大家,家里布置、环境一定会和普通人家有很大不同吧?!这些都是我急于破解的谜题。还有,怎么
很快,谜底解开了。先生的家就是寻常百姓家,不同的只是家里的书多些,书香气浓些。
通过我的神色,先生可能觉察到我的紧张情绪,便以“拉家常”方式和我攀谈起来。先是问起我家庭、生活的事情。我告诉先生,“我生活很好,没有太大压力,爱人也很支持我的工作。”先生听了很高兴,说,“青年老师刚起步总会遇到一些困难,要正确看待,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是很重要的”。先生的一番问话很亲切,顷刻间拉近了我
先生说,“在武大工作,作为一名老师,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特别需要注意三方面问题”。“首先,要重视做人,做人是第一位的。只有人品好,才能做好事、做大事。作老师,一定要有师德。”“第二,要认真讲课,要善于把知识传授给学生。要努力把课上好,受学生欢迎。”“第三,要重视科研。我们
先生的话,掷地有声,字字句句深植我心!但是,令我惭愧与不安的是,我生性愚钝,数年过去了,在先生和教研室师辈们耳提面命教诲下,在“为人、为学、为事”等方面,虽也有小觑长进,但与先生的要求与期待还相去甚远!
三
先生是一位极其重情讲义的人。
2008年9月,赵秉志教授因“欧盟一期死刑项目”组团到英国、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访学交流。鉴于先生在国际上的崇高威望,赵老师特邀先生担任访问团顾问。我因是该项目成员之一,承蒙赵老师关爱,也有幸第一次走出国门。
这次出行,活动紧凑,内容丰富。在英国,考察团先后访问了诺丁汉大学人权中心、伦敦布鲁内尔(BRUNEL)大学、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死刑研究中心。在匈牙利,代表团一行考察了匈牙利最高法院、匈牙利刑罚执行总局、赫尔辛基委员会和位于布达佩斯的埃特瓦斯-罗兰特大学。其间,忙里偷闲时,访问团还饱览了两国久负盛名的一些旅游文化景点,如英国的白金汉宫、大英博物馆、匈牙利的国会大厦、链子桥等。那时,先生虽逾80高龄,但仍步伐矫健,思维敏捷,与外国同行交流,应对自若,令考察团成员无不羡慕。先生与随团的另一位项目秘书、博士生
匈牙利访问结束后,按照计划,考察团一行要继续前往罗马尼亚。因先生和我未办理罗国签证,只能继续滞留匈牙利,等待考察团访问罗国结束后返回布达佩斯集合回国。先生此前没到过罗马尼亚,这真是件挺遗憾的事。好在东道主英中协会
查巴推荐我们到匈牙利北部城市埃格尔(Eger)一游。查
中午11点左右,我们从布达佩斯火车站出发,两个多小时后就顺利抵达。埃格尔,城市不大,在中国,充其量只能算个小镇,但古色古香,也不失清秀,散发着悠闲的地中海风韵。当时,时值9月,空气清新,阳光暖人,是出行的好时节。到达后,先生毫无倦意,稍作休息后,下午便步行徜徉在这座英雄古城。在接下来的一天里,先生先后畅游了建于13世纪的埃格尔城堡、埃格尔大教堂(Eger Cathedral)和其他一些景点。
离开埃格尔的前一天晚上,先生让我邀请查巴一起品尝产于本地的“公牛血”葡萄酒。先生说:“查巴陪同了我们整整两天,很周到。我们应该表示感谢。”查巴欣然接受了先生的邀请。埃格尔,如同欧洲其他城市一样,一到晚上,酒吧生意兴隆。晚餐后,我们三人一起来到一酒吧,每人点了一杯“公牛血”葡萄酒。先生因患口腔溃疡,不宜饮酒,向查巴说明原因后,多半由我代喝了。
酒间,先生对查巴说,“这是第二次来匈牙利,第一次是在1999年,是来参加第19届世界法律大会。匈牙利这些年变化很大”。“这次能到埃格尔很偶然,原本计划到罗马尼亚的,没能到罗马尼亚,一点也不遗憾,埃格尔果然名不虚传,我们不虚此行!要特别感谢你的导游和帮助!按照中国的礼节文化,以此酒略表谢意!”
我的英语水平有限,日常用语和简单句子也能对付。所以,先生的一番话基本还能翻译,只是“不虚此行”如何准确表达,当时真把我给难住了。一时没有办法,便硬着头皮译为“It is a pleasant trip”,显然有些词不达意。好在查巴能听明白,频频点头会意。快结束时,先生对查巴说,“欢迎您有机会到中国,到武汉。那时,我们请您喝中国的酒。”
回国后,我和查巴一直保持着邮件联系。他一直很希望有机会到中国来,到武汉来看望先生,品尝先生的美酒。
四
先生是一位极其平易近人、善于体恤后辈的长者。
一大早来站台上接我们的是先生
小陈把我们送到酒店后,按照林总的吩咐陪先生用早餐。先生怕耽误小陈上班,本想婉言谢绝,但考虑到是林总的安排,也免得让小陈为难,便答应了。
把先生送到房间后,我俩便各自离去了。小陈在餐厅等候先生,我回房间洗漱。我想,先生年纪大,行动稍微会迟缓些,所以,先洗个澡,再去请先生一起用早餐,一定来得及。冲完澡后,我便急忙去请先生。我刚出房门,小陈电话来了,告诉我先生已到餐厅了。先生怕我再去房间接他,便请小陈告诉我直接到餐厅来。我一路跑到餐厅,先生一见面就笑着对我说,“我洗漱完后,看你没来,就直接下来了,赶紧吃饭吧。”
早餐后,小陈回公司上班了,我陪先生回房间。路上,先生不时夸奖小陈是个优秀的小伙。当我问及先生刚才怎么如此快就下楼去餐厅,先生仔细对我解释道,“小陈送我们到酒店后,还要赶回去上班,我们就尽可能不要耽误他时间。吃完饭,等他走了,我们再认仔细洗漱”。
先生的话,丝毫无责备我之意,只是像爷爷一样在告诉我如何为人做事。听了先生的话,我感到非常惭愧!身为德高望重的宗师级前辈,面对孙辈,如此平易近人、善解人意,实在值得我学习!
这是我陪先生出差中遇到的很小一件事,也是我所见到的发生在先生身上无数的“小事”之一。虽已过数年,但我并没有忘却。每每想起先生对我的教诲,事情虽小,但只有涓涓细流,才能汇集成河。也正是因为如斯件件小事,慢慢地,我才感悟到俞正声书记在教师节赠送先生“上善若水”题匾的真正意蕴。
五
追悼会那天,殡仪馆天元厅哀乐低回,挤满了送
病魔无情,青山有意,又到嫩柳垂绿,湖波轻皱的美好时节。只是没有了先生的今春,珞珈山的寒意格外料峭,山麓的樱花较之往年,盛开得也分外迟些。但世人皆知,寒暑易节、四季轮回是人间社会的自然规律,当春去秋往时,珞珈山麓的樱榴桂梅各色花依旧会年复一年地次第盛开;如诗如画的珞珈山,依然还会一如既往的美轮美奂。只是永远缺憾的是:山上少了一位在这里度过60余载的风雨主人,少了那位腰间挂着计步器,每天散步的慈祥老人……
呜呼,先生安静地走了,一个时代也悄然终结了!我愿相信人有灵魂,先生生命虽然结束了,但我笃信他的灵魂和精神永在,守护着这片山,守护着这片地,守护他开辟的法学事业和我们这群徒子徒孙们。
有道是:“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本文作者系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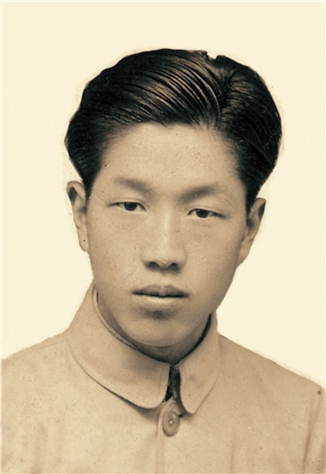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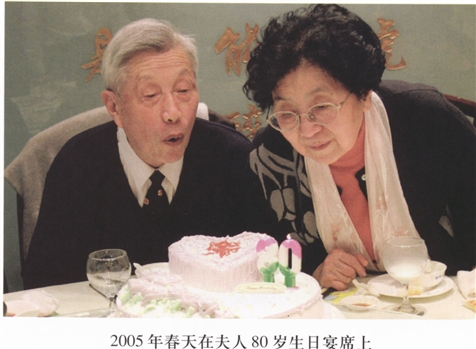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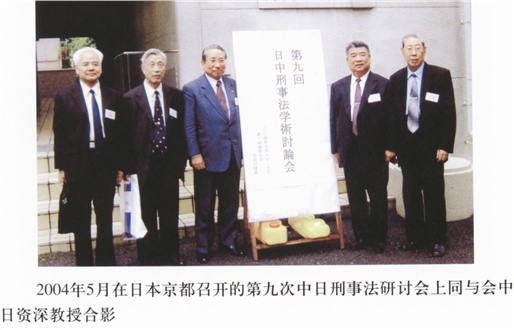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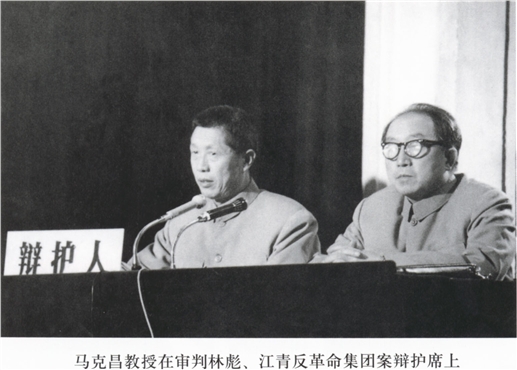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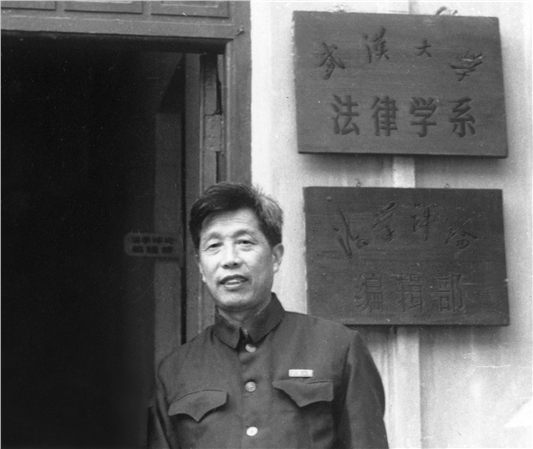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