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天六夜,押运东北———— 萧恒生
1987年,我24岁。参加工作已六年多了,是一名央企铁路职工。我的两个发小麻溜和老虎也是央企铁路职工。平时我们几个人上班都是吊儿啷当,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常聚在一起瞎混。再说单位管理也不严,想去玩的时候只要跟工长说一声,我这几天家里有事,就可以不去上班了。
我们那时候的工资每月是三十多块钱,对于经常去台球室,录像厅,溜冰场消磨时光的我们来说,钱根本不够花。额外的花销,只有靠一些野路子,利用坐火车不要钱的便利条件,经常去附近小站农贸集市上采购一些农产品回来卖,赚的钱就补贴平时的开销。
麻溜父亲是南下干部,他叔叔在东北老家的乡下当乡武装部部长。那一年,麻溜叔叔的两个东北老乡来南方做生意,我们请他们吃了餐饭。酒桌上聊起了生意,我对这两个东北人说,我们这里盛产桔子,很好吃,搞两火车皮桔子去东北卖应该能赚钱。东北老乡听了当时就拍板同意,说由他们回东北负责联系买家,我们负责组织货源和去铁路上批车皮计划。当时我们就谈好了条件,资金我们各出一半,利润分成也各拿一半。
不久后,东北老乡来信说已经找好了买家,是东北辽宁辽阳的一家化工厂。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东奔西跑,桔子的货源联系好了,也在铁路部门批到了两个火车皮,就在桔子装货的地方黎家坪,现在叫祁阳。
87年秋天的时候,大概是十月份,我们三个人在黎家坪火车站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边等装货,边在祁阳县城里玩了几天,还在风景名胜区浯溪照了一张合影。我们流连于浯溪两岸,浏览了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留在浯溪摩崖石刻上的诗句,年少轻狂的我们,不管是否能理解诗句里的意思,也沉浸在如古人游玩时的心境里,附庸风雅地感叹了一番。
在祁阳玩了几天,等到装好了一火车皮桔子后,马上就要发车,另一车桔子要等第二天装好后再发车。老虎和麻溜说他们两个人押运现在装好的这一车,要我明天押运另一车。毕竟我比他们两个人大了一岁,平时也是他们的老大,理所当然的我就要比他们多承担一点责任。把他们送上车厢里后,看着他们押运的火车慢慢远去,我心中仿佛觉得四周陷入到如荒郊野岭般地寂静。
第二天,我一个人爬上装满了一筐筐桔子的闷罐车里,在靠近车顶上的空隙间,装桔子的竹筐上铺了一床棉絮,带了一壶水,几个面包和一点零食,怀着一腔兴奋地心情,就乘着火车一路北上了。
货运列车没有时刻表,一路走走停停,我也搞不清楚它什么时候会到什么地方,有时莫名其妙地就会在一个地方“哐当”一声停下来,几个小时不动,货运车站里除了一长列一长列望不到头的黑色的火车厢,四处也见不着一个人影。我一个人呆在火车厢里,渐渐都失去了时间的概念。
列车一路北上,天气渐渐变冷。我上车时,忘了带一本书来看,白天时,也就只好打开一半车门,倚在车门边,神情漠然地望着外面一路经过的城市和村庄。天一黑就早早地躺下,在火车轮有规律地压着轨道的“哐当哐当”声中,半睡半醒。初上车时那种兴奋的心情慢慢地被寂静的白天和漆黑的夜晚所吞没,整个人变得百无聊赖,现在回想起来,那一路经过的地方既遥远又像是一场模糊不清的梦。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火车不知道停在什么地方,我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在撬车门。那个年代,常有窃贼偷盗火车上的财物。我忍不住对着车门外吼了一声,“别橇了,里面有人。”话声刚落,橇门声嘎然而止。只听到外面的人骂骂咧咧地走远了。
货运列车的停车场,基本上都是建在城市郊外,有时候列车停下来时,又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车,我也根本不敢离开车厢。生怕火车一启动,我人又不在车上,那就麻烦大了。小便还好解决,对着车门外一顿乱射就行了,可我现在怎么也回想不起来,那段时间的大便我是如何解决的?
几天几夜之后的一个下午,列车在一处货运站停了下来,我见不远处有一个铁路工人,就问他道:“师傅,请问这是什么地方?”
那工人远远地回了我一句:“山海关。”
我放眼望去,只见在站外的不远处,有一排房子,外面挂着“饺子”二字的招牌,还有露在房顶的烟囱正在冒着烟。终于见着有吃东西的地方了,我急忙跳下车,锁好车门,向着站外走去。
掀开挂在门上的门帘,屋内很暖和,我要了一碗饺子,一盘酱骨架,就狼吞虎咽般地吃了起来。在火车上吃了几天的面包,桔子,凉水,突然吃到了热气腾腾的饺子和酱骨架,真觉得是人间最好的美味。
我吃完饺子后赶紧回到车上,看着车门外天已黑透的寒夜,想着李自成当年就是在这里,与吴三桂引入山海关的清军大战,力竭而败,仓皇逃遁。最终中原大地沦陷在清军的铁蹄之下,山海关就此成了历史书中一个特殊的符号。我正在胡思乱想之际,火车轰的一声又启动了。此时东北已经下雪了,外面是一片在黑夜中或明或暗的雪色天地。
在一个飘着雪花的傍晚,火车轰隆一声停了下来,我看了一下时间,此时火车已经整整行驶了六天六夜,按行车计划来算,应该是到目的地了。我跳下车厢,在火车头前面的值班室里,问正坐在烤火炉旁抽烟的值班员,他告诉我说这是辽阳。
谢天谢地,火车终于到目的地了。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此时坐在车上傻等接货人来肯定不是明智之举,于是,我拿了提货单,带着行李下车,锁好车厢门,冒着雪花一路向辽阳化工厂而去。此刻的东北,已经是冰天雪地,等我踏着路上的雪泥到了化工厂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我现在已记不清我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当我被人领到了厂长办公室,领导见到我很热情地招呼着我说,辛苦了。然后指着一个小伙子说,小张,领客人先去食堂吃饭,叫师傅炒两个硬菜,整点好酒,饭后去泡个澡,晚上安排在咱宿舍里睡一宿。
我谢过厂领导,把提货单也交给了他,然后跟着小张来到了厂里的食堂。小张提了一瓶六十多度当地的特产“辽宁白,”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是叫这个酒名,我们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当即痛饮了起来。小张说他第一次接触到南方人,也从来没有到过南方,当我跟他说起一些南方风情,说男人也有许多人穿花衬衣,在舞厅里可以约女孩跳舞等等趣事时,小张惊讶地说,“啊?在咱这可不行,咱这里叫流氓。”听到他说的话后,我忍不住哈哈大笑不止。
饭后,我们去厂里的澡堂泡了个澡。泡在热水池里,那种感觉实在是太舒服了,我一个人几天几夜呆在闷罐车厢里,那种曾郁积在胸中的孤单与寂寞瞬间一扫而光,所以说,人生的愉悦感要从一种极端的孤寂状态,来到另一种极端的温暖之处时才能够深刻地体会得到。
晚上睡在开了暖气的厂区宿舍里,我和小张聊了很久。我们当时还互留了通信地址,此后几年,我们通过许多封信,在信中我对小张说,他要来南方出差的话,我一定会好好陪他玩玩。可惜小张一直没机会来南方,后来我们才慢慢地失去了联系。
第二天一早,我告别小张,坐上火车去了海城。辽阳离海城不远,一两个小时就到了。到了海城后,我在汽车客运站,买到了去岔沟乡的客车票。岔沟乡是麻溜留给我的他叔叔家的地址。
大客车到了岔沟乡时,已经是下午了。在我眼前,是一片白雪茫茫的银色世界。厚厚的积雪覆盖了所有的田野和房屋,目及之处,也不见一个行人。当然,乡政府里的武装部我很容易就找到了。里面的人一听我说是麻部长家的亲戚,马上就把我带到了麻部长的办公室。麻部长一见到我,很惊诧地对我说,啊,你没有在辽阳等?老李带着麻溜他们去辽阳接你了。李叔和王叔就是跟我们一起做生意的两个东北老乡。
麻部长说完,就把我带到了乡政府的招待所,是昨晚麻溜他们睡的地方。房间里很暖和,直到此刻,我才发觉外面是真的冷。只见眼前有一排土炕,我放好行李,往土炕上一躺,这也是我第一次睡在土炕上,才知道躺在这热炕上是真舒服。这时候我整个人全身心才真正的放松了下来,迷糊着就进入了梦乡。
门突然被推开,麻溜和老虎这两个小子从辽阳回来了,他俩一进来就大声地叫我,我睁开眼一看,外面的天已经全黑了。我一骨碌爬起来,几日不见,在这遥远而寒冷的东北乡下重逢,我们都很兴奋。这时麻部长带着李叔和王叔他们也跟着进来了,叫我们先去吃饭。
在乡政府的食堂里,已经摆满了一大桌菜,还有几瓶辽宁白。桌旁坐了五六个人,虽然大家都是第一次见面,但他们都很热情地和我们打着招呼,看来麻部长在乡里还是有一定的地位。东北人喝酒全是一口焖,不像南方喝酒是小口抿酒。我们刚喝完一杯,酒杯马上就被人倒满了,大家端着酒杯就对我们说,“来,下,下,下。”然后大家就都举杯一饮而尽。那时候的我们仗着年轻力壮,凭身体拼酒量,硬是把这一桌上的东北人全喝趴下了。
麻溜这次是第一次回东北老家,也是第一次见到他叔叔。他还有一个奶奶也是住在岔沟乡,离他叔叔家不远。麻溜奶奶听说孙子回来了,请我们去她家吃饭。她奶奶第一次见到长到这么大的孙子,笑得高兴的合不拢嘴。奶奶和麻溜的另一个叔叔住在一起,这个老叔叔五十多岁了,是一个标准的乡下老农,也没讨媳妇,一直和奶奶住在一起。这就是中国人的现状吧,混得好的儿子早已经远走他乡,只有混得差的儿子守在身旁。
我们三个人坐在麻溜奶奶的热炕上,吃着奶奶给我们精心烹制的酸白菜火锅,喝了一大瓶白酒,望着窗外那白雪映衬下的天空和大地,再感受着热炕上的舒适和亲情,吃着热气腾腾的火锅,饮下穿肠而过的烈性白酒,那滋味真是难以言说的惬意和畅快。临走前,我们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个大红包,悄悄地塞进奶奶的衣柜里,直到离开岔沟乡后,才告诉麻部长,要奶奶收好红包。
那几天呆在岔沟乡,我们每天就都是大醉而归。今天在李叔家饮酒,明天去王叔家吃肉,要么就是在小镇上的餐馆里,与一大帮东北人喝酒吃肉。我们也从来没有买单的机会,都是麻部长的朋友们抢着把账结了。东北的冬天,外面冰天雪地,无处可去,也就只有坐在家里每天从早吃到晚。李叔的老婆曾笑着对我们说:“咱东北人存不下钱,全吃进肚子里了。”
麻溜笑着对他们说:“吃光喝光,身体健康。”大家听后全笑了。就在这样的欢笑氛围里,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几天后,卖桔子的账结清了,我们也拿到了钱,就准备去丹东麻溜他姑姑家玩。一大早,我们就在岔沟乡的马路边等,这里每天都有开往丹东的大客车经过。告别了麻部长他们一行人,我们乘上了一辆开往丹东的大客车。
那时可没有高速公路,全是翻山越岭的泥土路。大客车上人也不多,我们上去后还有好些空位。越往东走,天黑得越早,我们到了丹东后,还是下午,天就已经完全黑了。等我们到了麻溜姑姑家里吃晚饭时,天已经黑了几个小时,那感觉就真像是在吃宵夜。
丹东是一座非常漂亮的边境小城,城市里高楼林立,街道宽敞整洁。我们站在鸭绿江边往对岸的朝鲜望去,那边就是一片荒凉,死气沉沉,一座像样的房子都看不到。我们在鸭绿江边坐上游艇,靠近朝鲜岸边游览,岸上看不到一个朝鲜人民,只有几个穿着军装的朝鲜军人在向我们挥手致意。在游艇上回过头来往丹东望去,只见城市里楼宇雄伟,街上车水马龙,显得生机勃勃,活力四射;再看看近在眼前的朝鲜,荒芜,破败,大地上残雪中衰草枯黄,满眼是令人窒息的凄凉景象。
当时我就觉得中国人都应该来这里看看,我们曾经也是眼前朝鲜的这副模样,幸好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绩,建设成了如此美丽的城市。丹东,是矗立在国门上的一张靓丽的名片,它与对面贫穷的朝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只有站在此地,心中才会产生出一种强烈的震撼。
生存还是毁灭?这难道是一个问题吗?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终于还是选择了打开国门,拥抱世界。而不是坚持固步自封,闭关锁国。“还好,我们没有像对岸一样,一条道走到黑啊。”这是我们三个人当时发自内心的由衷感慨。
在丹东玩了几天后,我们从丹东坐火车去北京。老虎的姐夫在单位里是负责开铁路职工免费乘车证的,我们铁路内部称之为免票,来之前老虎找他姐夫事先就给我们三个人开好了免票,我们拿着工作证和免票到丹东火车站售票窗口领到了免票专用的乘坐卧铺凭证,就可以睡在卧铺上去北京了。
到了北京,麻溜姑妈的儿子接到了我们。麻溜表哥当时在北京的一个对外贸易部门任职,是一个中层干部。表哥毕业于名校,属于那个年代的稀缺人才,参加工作不久就被破格提拔,正是前途无量的青年才俊。表哥带我们参观了他工作的办公室,那时他们正忙着于与世界各地做贸易,看着他认真忙碌的工作场景,想到我们平时偷懒耍滑的工作状态,不觉内心真有点惭愧。
我们拿着铁路工作证,住进了北京铁路招待所,这地方不比外面的宾馆条件差,甚至可以说真不错,主要是住宿价格还不贵。我们在北京时,当然也是去了一些热门景点游玩,像八达岭长城,故宫,颐和园,等等。那时候北京城里满大街是那种黄色的小面包出租车,俗称面的,便宜,快捷,我们出门就都是坐面的。
在北京玩了一个多星期,我们就准备回家了。同样也是在火车站售票窗口拿到了免票乘车凭证,睡着卧铺一天一夜就回到了家里。
这趟出远门,我们既赚到了钱,又玩得很尽兴,那六天六夜的货车押运旅程,对当时正年轻的我们来说,也算不上有多难熬。只是当我回想起这段往事时,老虎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就因突发疾病已经去世多年了,而麻溜在二十多年前一个人去广西玩后,也从此再无音讯,成了失踪人员。当我现在想起他们二人时,不免令我在伤感之际而唏嘘不已。
想来人生无常,岁月如歌,生命来不及感慨叹息,就如流水般默默前行。多少年过去了,我也已从青年步入到老年,许多人也成了我回忆里的故事,而我又何尝不是别人眼中的风景。
回首往事,多少年华已虚度;珍惜今朝,还需努力写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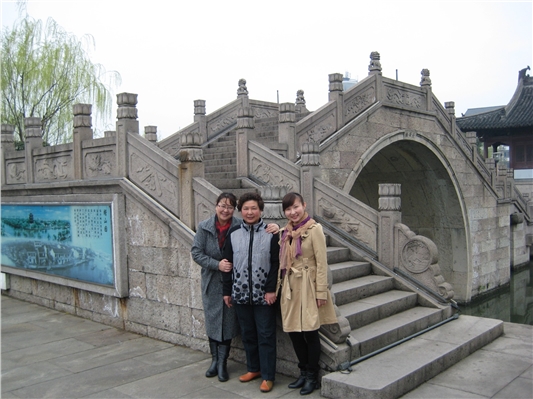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