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革命党与梁启超大论战(三)
1、满族是中国人,还是“异种”?满州之地是中国领土,还是“敌国”?满清入关是改朝换代,还是“支那亡国”?汉满关系宜两族同化,还是“驱除鞑虏”?
2、是单行“政治革命”还是“种族革命、社会革命、政治革命并举”(梁启超称“革专制而成立宪”为“政治革命”;革命党则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种族革命”或“民族革命”,称“土地国有”为“社会革命”)?流血革命是否必不可免?“支那立宪”是否必先排满?
3、革命是否会招致外国干涉、导致中国分裂?中国国民是否有“共和之资格”?仓促共和是否滋生内乱?君主立宪与共和立宪孰于中国现状为宜?建设立宪政体是通过梁启超所主张的“开明专制”,还是通过孙中山所主张的军政、训政而至宪政(即从军政府之军法专政,到革命党之“约法训政”,再到宪政机关分掌国权之民权宪政)?
4、孙中山所主张的“土地国有”、“单一税”政策是否“不必行”、“不可行”、“不能行”?
辩论这些题目,涉及对历史事实和现实国情的判断,对古今中外经验与教训的解释,对西方政治哲学和宪法理论的理解和运用。中国有成堆的问题,万国有纷繁的主义,卢梭、孟德斯鸠、亚当斯密、斯宾塞、伯伦知理、波伦哈克、笕克彦的理论被双方所征引。有时候同一个“西儒”,却被双方解读出相反的意思。
但是,在以上四组论题中,革命党立论最坚、阐述最多、影响最大的,也是这场论战中辩论最激烈的,却是比较没有学理与法理含量的第1、2两组题目,“满州非我族类”和“种族革命先于政治革命”,此即所谓“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至于“约法训政”和“土地国有”,那时还不十分紧要(那毕竟是革命成功之后才有可能实行的事情),也不太引人注意(但即使是对“约法训政”和“土地国有”,梁启超也提出了大量尖锐而精当的批评)。也主要是在“非我族类”和“排满革命”的问题上,革命党显得蛮横无礼,胡汉民、汪精卫“辞近诟谇”。他们非常固执己见,特别意气用事,几乎完全容不得任何反对意见。因此,在最基本的论题上,双方其实根本不存在理性辩论、诚意对话的回旋空间。这也就大大降低了那场论战的理论品质和政治价值。
革命党的大多数领袖和理论家们之所以坚决反对立宪派的政治主张,其首要理由无非是汉人不可拥戴“异族”。汪精卫说,“对于异族政府,无论其为立宪,为专制,亡国均也”。胡汉民说,“满政府不倾,而遂许其同化者,以狐媚为虎伥,无耻之尤者也”。朱执信说,“革命者,以去满人为第一目的,以去暴政为第二目的”。孙中山连主张“立宪救国”、“实业图强”的人也不放过,骂为“卑劣无耻,甘为人奴隶”。孙中山说,“于光复之前而言此,则所救为非我之国,所图乃他族之强”。可见“革命先行者”的心胸境界是何其狭隘。此外,还有更激烈的说法,如女侠秋瑾放言“大举报复”,义士徐锡麟宣称“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再图立宪未迟”。此类出格言论多出于“民族义愤”,是立场、态度、感情问题而非理性认识上的问题。言语出格未必不可谅解,但若以此等“共识”打造成熟、理性、对国家未来敢于负责的优秀革命党,则无可期待。
在反驳立宪派对“种族革命”的反驳时,革命党的文风是比较粗野霸道的。口诛笔伐,出言不逊,扣帽子,泼污水,爆粗口,诸事皆有。比如,汪精卫某檄文以《斥为满州辩护者之无耻》为题,未曾开辩即先定对手为“无耻”。在另一篇雄文中,汪宣称“不排满者如同汉奸”(汪精卫作为近代史上最出名且最无异议的“汉奸”,却原本是偏激的大汉主义者,这真是一言难尽),直截了当把梁启超划入“汉奸”行列;胡汉民在向梁启超挑战时以“汉民”、“辩奸”、“民意”作笔名(胡汉民原名胡衍鹳,后改胡衍鸿,论战之后即以笔名作本名。如同文革时期时兴改人名地名一样,当年革命党人也曾流行“姓名革命化”),不管有理无理,先摆出一副我是大汉英豪、你是满奴国贼的凛然架势,动辄大骂梁启超利用戊戌六君子沽名钓誉、是 “出尔反尔”的“反覆小人”等等,大搞人身攻击;著名学者刘师培为了证明“排满革命”的正当性,竟从史籍中“考证”出满州之地不属中国领土,而属“外夷”“敌国”。
梁启超全然不同意“排满”“仇满”论。梁认为,中国历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并非汉人独有;满人是中国属民,其入统中原是政权“易主”而非“亡国”。“中华民族”这一现时流行的概念,即由梁先生当年首创。梁说,满人经过清朝二百多年演化,“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满人排汉是极少数满族权贵所为,非全体满人所为,满汉不平等是政治性质而非种族性质。所以,中国只需要“政治革命”(即“要求立宪”),不需要悖情悖理的“种族革命”。 在《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这几篇最重要的论战文章中,梁启超指出,革命难免杀人流血,终究是不祥之事,是国家和人民的“大不幸”;在国内,革命易生内乱而酿分裂之患,对国外,易招干涉惹瓜分之祸;又“革命复产革命”,大乱之后易生恶政,人民最终只能将自由奉于一人或一党之手以苟全性命与财产,“此则民主专制政体所由生也”;且破坏之后建设不易,革命的成本代价不可能一笔勾销,终必由子孙后代加倍偿还。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轻言革命。汪精卫以《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和《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进行反驳(此二文有孙中山的授意),认为革命军只排满不排外,不扰“外人物业”,不改对外条约,列强不仅不会干涉,反而会同情中国革命。汪精卫还说,不革命反倒有瓜分之虞,因为满人当政才是中国衰弱的主因,“故非扑满不能弭瓜分之祸”。在对内方面,汪精卫认为革命军不会重蹈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群雄割据的覆辙,因为共和革命无帝位之争,没有内乱的理由,中国革命也将吸取法国革命恐怖专政的教训,所以,革命将皆大欢喜,并无任何外患内忧。
必须指出的是,梁启超虽然坚决反对革命党的“种族革命”与“社会革命”,却并未完全否定革命的正当性。他几乎是以恳求的语气希望革命党停止与立宪派争斗,你预备你的革命,我预备我的立宪,不要互相妨碍。他说,一党向政府请愿要求立宪,一党预备军力以备将来革命,可以两不耽误;若实在是和平立宪不成,到时再暴力革命不迟。针对革命党斥骂立宪派向“虏廷”请愿“无耻之尤”,梁启超不无天真地发问,“(向清政府提)要求果害于名节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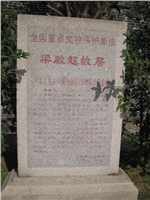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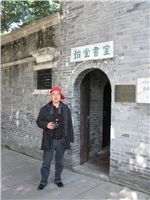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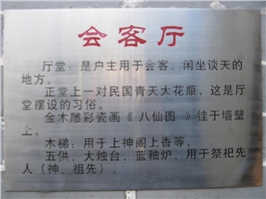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