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革命党与梁启超大论战(二)
事后,论战双方都宣称己方获胜。但客观地说,革命党声高气壮,略胜一筹。《胡汉民自传》回忆:“交战之结果,为《民报》全胜;梁弃甲曳兵,《新民丛报》停刊,保皇之旗,遂不复见于留学界,亦革命史中可纪之战争也。”其志得意满之态,溢于言表。胡汉民将《新民丛报》的停刊和保皇会的改名全都当成论战的功劳,这自然不是事实(注:《新民丛报》停刊的主要原因是梁启超事务繁杂,精力不济,致该报一再愆期,“定期出版的信用已失”。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康、梁“大喜欲狂”,认为保皇会宗旨已达,遂更名为帝国宪政会)。不过,那场论战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长了革命党和《民报》的志气,灭了立宪派和《新民丛报》的威风,扩大了同盟会及其“主义”在留学界、知识界的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
梁启超主编且撰文过半的《新民丛报》是一份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极大的畅销刊物,黄遵宪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严复称其“为亚洲20世纪文明运会之先声”(注:今人往往以为清朝末年暗无天日,其实彼时言论自由尺度远胜当今,《新民丛报》可在国内公开发售,《民报》亦有半数销往国内)。但在与革命党论战期间,该报销量有所下降,革命党的人气则大幅窜升。这种消长变化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最大的原因当然不是革命党很正确、立宪派很错误,而是清政府太愚蠢),但可从一个侧面说明这场论战的胜负——假如读者有资格做裁判的话。同盟会成立之前,孙中山一派革命党在留日学生中原本默默无闻、无人问津,这场论战极大提升了革命党的整体形象。通过与名满天下的“言论界骄子”梁启超过招,汪精卫、胡汉民等党中秀才脱颖而出,革命党从此不再被读书人视为无知无识的市井游民与帮会暴徒。以此而论,说革命党是论战的胜方,似为确论。
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说,“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那场论战留在鲁迅心目中的印象,也是革命党大胜、梁启超大败,与当事人胡汉民的叙述可相印证。但鲁迅的记忆不尽准确。事实是,当时的《民报》主编章太炎对于“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并不热心。在自编年谱中章太炎说,“余以胡、汪诘责卓如,辞近诟谇,故持论稍平”,可见他对胡、汪的文风不认可,不愿为论战火上浇油而宁愿为胡、汪纠偏。后来,孙中山的亲信声讨章太炎(因章参与“倒孙风潮”),也说“(与立宪派的)战斗皆精卫、汉民、县解、寄生诸君任之,章以与梁启超交厚故,未有一文之助力”(县解、寄生是朱执信、汪旭初的笔名)。的确,曾写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那种言辞偏激的诛心之文的章太炎,居然在热火朝天的两党论战中只写了《箴新党论》、《〈社会通诠〉商兑》等很少几篇批评立宪派的学术性文章,且“商兑”的对象是康有为、严复,却不加入围攻梁启超,这说明,在进入革命党核心圈之后,《民报》章太炎反而大大“保守落后”于《苏报》章太炎。当时革命党中学问以章太炎最深,文名以宋教仁为盛,与章太炎一样,宋教仁亦对论战保持相当距离且对立宪派人士保持尊重。
对于那场论战的胜负,也还有另一种不同的观感。在另一些人——比如那时年龄尚小的胡适、梁漱溟这一类人——看来,梁启超其文入情在理,未必落败,革命党其文强词夺理,未必得胜。胡适说他“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这“恩惠”的起点,正是从他1905年阅读课外读物时开始,那时即正是两党论战的期间。胡适说,梁启超的文章“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而革命党的文章胡适未予置评,显然并无同样的感染力。梁漱溟回忆说,他15岁时寻到了整整3年的《新民丛报》六巨册、《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本,“寝馈其中者约三四年”,“感受任公先生启发甚深”。30年之后他仍然认为,少年时代有幸阅读《新民丛报》上梁启超的文章是一生“莫大的幸福”。在梁启超与革命党之间,谁是真正的言论英雄,谁更有影响力、说服力,在胡适、梁漱溟们也是不言而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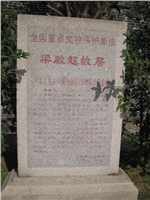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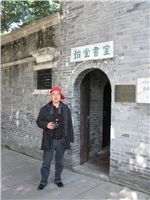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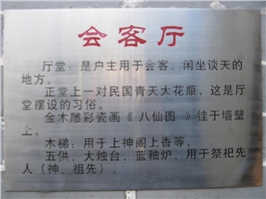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