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还是民主宪政
梁启超抓住了民主宪政的本质,在国体问题上,就持相对灵活的态度,辛亥革命爆发之前,他始终坚持君主立宪,以免因国体变更而发生社会震动,辛亥革命即已发生,他也非常欢欣鼓舞。一则因为这场革命既已发生、结束了中国几千年帝王专制的历史,的确可喜可贺,二则与古往今来的革命相比,它的代价是非常小的,三来这场革命的成功不仅是他本人十几年奋斗的结果,在革命爆发前后他也同样做了大量工作。
预见到“全国兵变与全国民变必起于此一二年间”之后,梁启超与其师康有为决心利用满族权贵的矛盾发动宫庭政变,正在这时,武昌起义爆发。经过仔细的考虑,梁启超调整了战略,精心制定了“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的新方针,希望此举能“纾革命之祸”,使“国会得有实权,完全宪政从此成立。”在梁启超指导下,立宪派大力开展活动,许多省份宣布独立,从而沉重地打击了满清王朝,对结束帝制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1911年10月30日,清庭下罪已诏,梁启超见过上谕后,把“用北军倒政府”的计划发展为“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八字方针。
孙中山曾说“革命改良决分两途”,但事实上绝非如此,连深受中共观念影响的李喜所、元青在其所著的《梁启超传》中也承认:“这也说明,追求温和改良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和执着于武装斗争的革命民主派虽然斗争的手段、途径迥然有别,但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方面是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
岂止如此,难道革命派的目的不也是民主宪政?武昌起义十八天后,梁启超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剖白自己道:“痛恨满人之心,吾挚又岂让革党?不过暂借为过渡,一旦立宪实行,政权归诸国会,皇帝充其量只是‘坐乾修之废物’”,存之废之,无关宏旨。
有些人逃出大陆后大唱高调,大骂当局,虽搏得了国际舆论的一些关注,对中国内部的变革却于事无补。如果他们留在国内又想做一点事,就会知道不仅语调要平实谦和,而且要尽可能地寻找当局所能接受的方法和道理,恐怕也只有如此,才能促进国家的民主进程,因为今日中国的政治改革终归只能在目前的权力构架中进行,只要能促进人大成为真正的最高权力机关,使宪法成为“天下之公器”而非一党之工具,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当然,在社会政治领域,再伟大的理论家发明了再伟大的理论,面对变革时期风云万变的局面,也不可能成为“常胜将军”。梁启超注定无法逃脱这一定数。
何况,作为一个始终没有掌握实权的政治理论家,他也根本没有机会按自己的意志实践自己自上而下全面变革中国社会的系统理论。在不能不一再依附其他掌权者以图谋贯彻自己意志的局面中,政局的发展也就不是由他而是由他所依附的强权人物的动向来决定了。
1911年底,梁启超和康有为提出了“虚君共和”主张,作为一个夹在革命派和北洋军阀中间没有军事实力作后盾的政治势力,他们的这一主张在“乱机已发”的局面中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此后,他们开始采取联袁拒孙的方针,梁启超一介书生,却自以为清王朝倾覆后可以左右政局,说什么“入都后,若冢骨(指袁世凯)尚有人心,当与共戡大难。否则取而代之,取否,唯吾所欲耳,”安知迄今为止中国的政争总是以军事实力为背景,他所倡导的以理服人的民主宪政时代还未到来,自己又能拿什么去对付兵权在握的传统官僚袁世凯和他的后继者呢?
这样,1912年11月中旬返国后虽然始终不渝地的坚持通过“开明专制”实行“保育政策”以走向完全的民主宪政的正确主张,但梁启超却因曾和袁世凯、段祺瑞之流同为前清臣僚而以为他们是能在自己辅佐之下完成“保育”工作的“开明专制者”,因而在政治实践活动中一错再错,以致最终被挤出了政治舞台。
民国初年,梁启超的政治口号是“国权主义”,通过本文以上分析,不难理解“国权主义”的立论基础正是“开明专制论”——因为他发现“开明专制”是实现“立宪政治”的必由之路。他举例说:“英国的克伦威示时代,普鲁士的腓力特烈时代,俄国的大彼得时代,荷兰的阿连治时代,法国的拿破仑时代,奥匈帝国的周瑟夫时代,都是史家所称的开明专制。当代有名的国家,几乎没有不经过开明专制时代而论‘径行完全粹美之宪政’的。”(李喜所,元清《梁启超传》P308)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才倡导国权主义,想通过袁世凯、段祺瑞之类握有实权的人,在“共和”的形式上,运用专制手段稳定社会,把国家引上宪政轨道。
与此同时,梁启超从理论上说并没有忘记对“国权”扩张为专制权加以防范。在联袁联段的同时,他一直致力于建立“强善政府”,也就是建立完全的政党内阁。即内阁由国会多数党组成,使内阁成为国家的指导者,而国会又为内阁的拥护者,阁会融为一体,政府便会强有力;另一方面,政府如以国会为后援恣行秕政,政府党便会失去人民信任,在选举中丧失国会的多数,而使内阁不安其位,如此则政府万不能为恶,否则便会因选举大权操诸国民之手而随时被更选……。完全的政党内阁又如何实现呢?他认为,这要以健全的政党发生为条件,尤其要有健全的两大政党,一党在阁,一党在野,在强健正当的对抗下,开展正常的政党政治。(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P310)。
历史的行程并没有按梁启超所致力的这一方向发展,却往他1906年便已指出并极力避免的“革命复革命,永无休止,流血复流血,国无宁日”的方向堕落。应当说,这种情况的发生梁启超本人也并非毫无责任。概括地说,第一,袁段之流作为前清官僚与民主政治家梁启超有本质不同,他们只认权力,笃信武力,是没有民主宪政理想可言的传统政客,早在戊戌变法中,维新事业就因袁的背叛而失败,面对政治品质如此恶劣的袁世凯,梁启超在根本无力挟制他的情况下,将“开明专制”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无疑属根本性的策略错误,其结果必然是南辕北辙。第二,理论上讲,辛亥革命后到“二次革命”前,孙中山的国民党和梁启超的进步党是共匡民主宪政的同道,梁启超本应把国民党当成维护“临时约法”和第一届国会权威的伙伴,但梁启超汤化龙却落井下石,这种作法导致唇亡齿寒,实在是自掘坟墓,尽管梁启超汤化龙后来有所省悟,彼时却大势已去于事无补了。此外,孙中山也缺乏民主政治家的度量,从而把梁启超及其追随者当作民主政治建设的同道,并不顾国会中国民党议员的反对,无视第一届国会的存在,毅然发动“二次革命”,则属梁启超处理两党关系失误的重要外因。
从追求民主宪政理想的角度说,梁启超政治实践的败笔还有不少,他未能在袁世凯拿国会中国民党议员开刀时挺身而出,大力维护议员的权利和国会的声誉,就不仅缺乏政治家的风度,而且造成了袁世凯把包括他在内的国会乃至“临时约法”均看得一文不值的局面。粉碎张勋复辟后,他忘记了不久前护国战争中只有恢复民元约法,并根据约法第54条之规定产生宪法并传诸无穷才是唯一正确道路的主张,竟然拥护段祺瑞召集所谓“临时参议院”代替旧国会,则不仅是一个重大原则错误,而且成为孙中山号令天下发动“护法战争”的口实,致使中国从此走向长时期的全面内战。
此外,就是世人视为梁启超政治活动中闪光点的“护国战争”,其历史价值也属可疑,事实上,“护国战争”使1911年到1917年正好两年一大战,成为使中国陷入全面内战的重要环节,而护国军本身,也成为日后淆乱中华的重要军阀势力,因此,若以梁启超本人避免革命流血以引发乱机的观点衡量,梁启超不用组织游行示威之类的非暴力手段迫哀下台,也同样是南辕北辙之举。
梁启超的改良主义虽随着拥袁拥段搞“开明专制”的错误抉择宣告彻底失败,但就其理论而言却并不错,因为革命复革命、流血复流血、外族入侵等现象的发生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他所做的一切总的来说正是为了避免这些恶果,至于这一切终于还是接踵而至,对他来说,只能是“尽人事而听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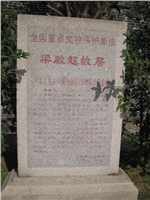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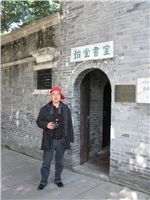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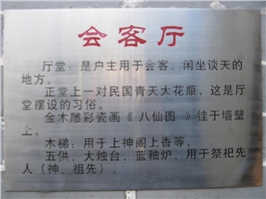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