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召棠兄弟6人,他居长。5个弟弟都从事商业,族中人盼他将来走进仕途,前途无量。他看到湘西贫困,人们连饭都吃不饱,又生性喜爱自然植物,心想长大要当个农学家。他幼年就读于名儒向晖庭门下,稍长又学于另一名儒邹行程举人。先生给他谈到民以食为天时,他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族人说,七十二行只有农业最下贱,和农业打交道,当不了官发不了财,还要穷贱一辈子。读了书不想当官,去做商人也好。黄召棠说:“男儿胸怀国家,男儿志在报国,不一定要去当官。国家需要各种人才,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就去学什么,这就是报国。我们国家农民最多,却饭都吃不饱,我怎么不去学农业呢。”
黄召棠下了决心。但清政府腐败无能,列强横行,一个山区孩子囿于山区,不可能有大作为。黄召棠于是想走出山去。他的家人全力支持。这样,1906年,他自费赴日本留学。但是,他只学过几句常用的日本话。日本人的叽哩呱啦,他基本上是听不懂,而他自己讲出的语言,也是吉首日本话,别人也听不懂。语言是人类思维直接的现实,不通语言,就无法与他人交流,就进入不了世界。他下决心从头学日语。这样,他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日文,一年后,才转入鹿儿岛高等农林学校农艺化学科。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他欢欣鼓舞,漫步岛国街头,回首遥望祖国时,仿佛看到全中国的土地都等待着他去描绘美丽的图景。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是孙中山的革命纲领,对土地的重视就是对国民生计的重视。黄召棠学业已成,他怀着刚获得的热烘烘的农学知识,怀着报国的满腔热忱,怀着振兴中华的希望,回到自己的祖国。
黄召棠一回到祖国,亲友们邀他去做客,要邀他一同游玩,但他说自己才学到的知识正热,自己非常想学有所用。于是他放弃了休闲打算,立即去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任教,把自己的知识,灌输给更多的人,再让学生们带到各处的农村,尽快发挥知识的效益。他那时33岁,已名扬京城。他与北洋政府农林总长陈振先等人共同组建了“全国农学会联合会”,陈振先任会长,黄召棠任副会长。可见他在农业科研界已具有相当的声望。但是,北洋军阀政府根本不重视农业,黄召棠深感失望,遂于1914年离开北京,南下江西省去农事试验场当场长。他想到农业第一线,实实在在做一点农业科研,比身居闹市要好。外面的街市灯红酒绿,他却埋头于田问地头进行农业试验。在阳光下,在雨雪中,他手脚沾满泥土,用放大镜照着土地里的幼芽,探索祖国农业的前景。不久,军阀混战,时局动荡,他无法再进行试验,只好回到湖南。一些省府官员慕名拜访他,要他继续从事农业教育工作,对他保证,一定使他的工作顺利进行。他高兴地点了点头。不久,他便担任湖南省甲种农业学校校长,并主持湖南农事试验场工作。他又全身心投入了他的工作。由于他的崇高声望和卓越的能力,湖南督军傅良佐(吉首人,曾官至陆军次长)曾以同乡关系派员探望,并邀他去督署任职。他对使者说:“谢谢傅督军好意,黄某不才,无意仕途,一心只在土地上,别无他念。”傅良佐被婉却,连声赞叹:“吾乡中人高节,德才难得,人性难得。”
黄召棠虽然没有进入仕途,但他对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革命,是由衷的欢迎。早在留学日本时,他就预见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的革命,必将改变中国的面貌,他对他们非常钦佩,且有一些往来。与宋教仁乡谊尤深,常有书信相通。1925年春天,黄召棠路过南京,闻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他面对巍巍金陵,震惊悲痛,写下一首《金陵怀古》,诗云:“长城筑罢又开河,毕竟秦王好事多。王气何曾销汇尽,空余画舫泛烟波。”借古写今,嗟叹悲恸之情,溢于言表。
1917年1月,中华农学会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农业学术团体。它以联合全国农业科学界同仁共同研究,分工合作,改进我国农业落后面貌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为宗旨。黄召棠是农学会中坚人物。农学会联合各地会员,积极筹措经费,开展研究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学会初成立时,经费十分困难,黄召棠将所积蓄的银洋数干元全部捐赠给学会,支持学会开展活动。
后来,黄召棠还曾先后执教于安徽芜湖第二农业学校、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农学院(今浙江大学)。教学之余,他还积极参加中国农学会的学术活动,潜心农林著述,著有《果树园艺栽培学》、《土壤学》、《茶树的栽培》等,可惜后来原稿散失殆尽,未来得及印刷出版,但通过教学被学生继承了下来。
1927年,黄召棠因病还乡,翌年不幸早逝,年仅49岁。中华农学会为了表彰黄召棠对培养农艺人才和发展农业科技事业作出的贡献,于1936年设立“黄聘珍先生纪念奖学金”,专奖给有关农业化学方面的论著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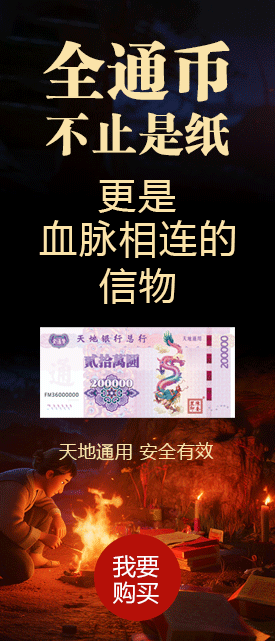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