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祖德:《超越自我》二
有些上海人总认为上海什么都好。其实,就说公园吧,是无法和北京的公园相比的。而襄阳公园在上海的公园中又是属于“小尺寸”的。因为小,游客不多,草坪整洁,再衬上路口的那个圆顶教堂,倒也显得小巧玲珑,别具风味。
从襄阳公园的大门一直往里走,尽头是一个茶室。茶室中央一长排桌子上放置着十几张围棋盘,棋盘周围经常挤满了对局者和观战者。茶室外有一块空地,也放着一些桌子和围棋。室内是乱哄哄的,相比之下,室外要清静得多。然而1951年的一个星期天,室内的人纷纷被吸引到室外去了。很多棋迷围着一张桌子,观看着一老一少的对局。年老的是棋界大名鼎鼎的国手顾水如先生,年小的是只有7岁的我。在当时,7岁的孩子会下围棋在棋界不但少见,而且寡闻。棋迷们崇拜顾水如先生的棋艺,都想趁此机会欣赏一番和学上那么几着。同时,又对7岁的孩童很感好奇。因此围观者越来越多,里三层外三层,很快就把我们包围了起来。
顾先生让我7个子对弈,我睁大了眼睛盯着棋盘,真是用尽吃奶的力气去捕捉顾先生每一步棋里所包含的神秘莫测的用意。棋盘对于我来讲,就是整个的世界。其他一切都隐退了,不存在了。只是事后我才知道顾先生一边用各种下法考验着我,一边微笑着向四周的棋迷们点着头。而棋迷们也正向顾先生“啧啧”地夸我呢!棋迷中有一个身高1米84的大个子,唯有他顾不上和人交谈,甚至都顾不上发出“啧啧”声,他紧张得好像顾先生不是在考我,而是在考他呢!不过这也不奇怪,因为他是我爸爸呵!
棋局的形势不断变化,顾先生的精湛技术使得黑棋的优势一点点地削弱下去,但黑方的部队并不溃散,依然扎住阵脚,尽量维持着残存的优势。对局进行了一大半,突然顾先生一拍桌子,高兴地说:“这个孩子我收下了!”
我学围棋有过好几个老师,顾先生应当说是我的启蒙老师。然而在顾先生之前我还有过两个老师。第一个老师是我的爸爸。我爸爸性格宽厚,又幽默乐观。他大学毕业后去美国留学,而后又周游过世界很多国家。他在西洋受了多年的熏陶却未沾上一点西洋习气和崇洋思想,简直是个国粹派。他尽管吃了好几年的西菜,回国后却一点也不愿吃西菜。每逢过年过节,父母经常要带我们上饭馆,我们3个孩子就吵闹着要上西餐馆,因为吃西菜使刀叉,很好玩。但父亲总是坚持要把我们带到中菜馆。他不爱看外国小说和电影,但酷爱古典文学和京戏。偶尔和我们一起去看外国电影,他也往往在电影院里睡上一觉,然后心满意足地带着我们回家。他看京戏特别来劲,有时一个星期带我们看两场。记得有一天我们下午看的最后一出折子戏是《打渔杀家》,晚上看的第一出折子戏也是《打渔杀家》。爸爸依然看得兴致十足,还像真正的戏迷那样大声叫“好!”
爸爸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甚至他的梦话也经常是用英语讲的,可他从来不曾想到把这个本事好好地传授给子女,而是倾其全力向我们传授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在我们不怎么认字的时候,每天早晚两次给我们讲《水浒》、《三国演义》和《西游记》……我们上了小学,他就让我们背《诗经》、《史记》、唐诗、宋词等。我记得那一大篇《项羽本纪》背得我好苦。爸爸自己有时间就读书——我家抽水马桶的水箱上总是放着一些古书,这是爸爸上厕所时必读的。孩子们是在不知不觉中模仿自己的父母的。爸爸自己这么读书,他每天布置的诗词,我们也乖乖地背下来。他每天下了课回到家,我们3个孩子便习惯性地一个个站到他面前,给他背诵当天早晨他讲解过的诗、词。我弟弟祖言似乎背诵起来最不费力,后来,当他种地、工作十几年后意料之外地考上了唐、宋专业的研究生时,回想起来倒也合乎情理。
围棋是我国之国粹,因此父亲也很爱好。尽管他的水平不高,但跻身棋迷的行列是当之无愧的。这个本事他当然也要传授给我们的,但他嫌我太小,便教给比我大1岁的姐姐,我只能列席旁听。当时姐姐也才7岁多,她是宁愿玩洋娃娃,也不愿下棋的。我想我没有资格和爸爸下,总可以和姐姐下吧。姐姐输了,她不服气,我便让她子下,她又输了,也不知下了多少盘,一直下到让她25子(下围棋最多就是让对方25子)她还输,这回她气坏了,说发誓不和我下棋了!(后来姐姐从书上看到马克思输棋给李卜克内西,也是又气又不服气,她便觉得她生气是不无道理的。)
姐姐不和我下棋了,我怎么办?亏得这时父亲决定放弃姐姐这个学生而教我了。父亲总是坐在沙发上,把棋具往小桌子上一放,让我坐在小帆布凳上。一次下棋前,我仰起头望着爸爸:“爸爸,你坐大沙发,我坐小帆布凳,这样不公平。”
爸爸说:“我水平比你高,当然要坐大沙发。以后你什么时候能赢我,我们就对调一下,我坐小凳子。”
“好,你说出话要算数,到时可别赖账。”
两个月后,我胜了爸爸。下完的第一句话就是:“爸爸,我该坐沙发了。”
“好,说出话算数。”
大高个子的爸爸往小帆布凳上一坐,可怜的小凳子哪经得起200磅的分量,一下就趴在地上呜呼哀哉了。继而爸爸又坐塌一只本来也该我坐的小藤椅。这下,他感到我在下棋方面有些才能,就想找一个水平比他高的来教我。当时他是一所中学的校长,学校中有一个教员叫周己任的,他的水平比父亲高出一截,于是父亲把周老师请到我家,周老师就成为我的第二任老师。
周己任老师年岁比我父亲大出不少,头发已花白,身体虚胖,脸很和善,他经常在社会上找人对弈,棋界给了他一个外号叫“周文王”,我很喜欢这个外号,因为爸爸早就给我们讲过周文王的故事了。后来我才知道围棋界中很多人都有外号,居然还有一个叫作“姜太公”的。
周老师跟我下了一盘棋就不再跟我下了,尽管他的水平当然比我高,但他感到应该请个名师对我指教。周老师虽然是个普通的围棋爱好者,但他却具有识人材的慧眼。通过周老师的介绍,我在襄阳公园认识了顾水如先生。周老师是只跟我下过一盘棋的老师,这个任期不能再短了,但他所起到的作用却是不能再重要了。
如今围棋界很多人都知道“南刘北过”,即南方刘棣怀和北方过惕生。殊不知“南刘北过”是由“南刘北顾”演变而来的。顾水如先生30岁左右在北京,那时他已是国内最高水平的棋手。刘棣怀先生坐镇江南。这两位棋界巨匠在那个时代棋艺最精、名望最高,一南一北,分庭抗礼,各据半壁江山,于是被人称为“南刘北顾”。后来顾先生来到上海,安徽的过惕生却来到北京,代替了顾先生的位置,于是就成为“南刘北过”。碰巧的是对于上海人来说“顾”和“过”的发音完全相同,因此其演变就很为自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居然“南刘北顾”逐渐被人淡忘。
顾先生的老家是江浙交界的枫泾镇,当地的棋风很盛。顾先生的一家,包括父母和几个哥哥都是围棋爱好者。顾先生从9岁开始先学象棋,随后又学围棋。他年幼时性情急躁,母亲就很耐心地启发他,给他讲了很多围棋故事,使他逐渐懂得下棋要细致、镇静,要有全局规划。顾先生认为他的母亲是个围棋教育家,既会传授棋艺,又善于培养良好的思想修养。
顾先生在17岁时向当时的围棋先辈,如无锡范楚卿、合肥张乐山、江都王燕卿等学习棋艺,收益不浅,从此他在围棋界崭露头角。之后《时报》的主人狄平子邀请顾先生去该报主编围棋栏。此报遍及全国,每日连载围棋,对推动围棋起了不少作用。
这里还要提一笔反动军阀段祺瑞。人们都知道他的臭名,但知道他是个围棋迷的人恐怕不太多。他的棋艺不算高明,但却酷爱下棋,且自以为是,仗着他的地位,他只能赢,不能输。当时国内凡有名望的棋手多被他召去对弈,又都知道他非“赢”不可,于是对弈的结果总是他获胜。每当此时他情绪高涨,不但要夸奖与他对弈的名手,还要送些钱财。不过谁若一旦取胜,那简直是触犯圣上,马上会被轰出去,一个钱也拿不到,而且再也不会被他召见。当时偌大的一个中国只有一个人敢于胜他而又使他无可奈何,此人乃他的亲生儿子。
顾水如先生当时是最有名望的国手,因此常被段祺瑞召去下棋。顾先生虽然为人清高,但也不敢冒犯这位军阀。段祺瑞胜了国手,当然尤其高兴,于是赏赐得也较多。顾先生青年时代赴日本学围棋据说也是由于段祺瑞的资助。陈毅同志曾说过:“段祺瑞干了很多坏事,但对围棋还干了点好事。”真是功过分明,尽管过比功要大不知多少倍。
顾先生赴东瀛学围棋对他影响很大。当时的中国棋手几乎都是力战型,接受日本棋理很少。而顾先生在日本受到了现代棋理的熏陶,使他的棋艺风格与一般中国棋手有明显区别,特别在布局和形势判断等方面,的确技高一筹。他下的棋不用蛮力,尽量符合棋理,使人感到自然、清晰、明快。顾先生的风格是典型的日本现代风格,在当时中国的围棋界,这是很突出的,犹如鹤立鸡群。也正因为如此,助长了顾先生的优越感,他认为在中国,即使再高明的棋手,包括刘棣怀先生等,都不能和他相提并论。在和爱好者下指导棋时,顾先生经常这么问:“刘大将(刘棣怀先生的外号)让你几子?”对方如答三子,则顾先生必然要他放上四子;对方如说四子,则顾先生无疑会让他放上五子,在这方面也要体现出他的高人一等。人的优点和缺点往往很难分割开来。一个突出的优点往往会伴随着一个明显的缺点。顾先生是个个性很强的人,他处处都要高人一头,也是不奇怪的。
顾先生的最大优点就是热心培养下一代。顾先生有儿子,他很想把自己的棋艺传授给他,并也下了一番功夫。遗憾的是并非天下每个人都具有下好棋的素质。尽管顾先生是位出色的老师,也无法实现自己的心愿,这是他的一大憾事。说也奇怪,古今中外,凡是围棋名家的后代,简直无一人能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在围棋方面有造就。虽然有不少名手和顾先生一样对其子女抱有希望并作过努力,但其结果也都和顾先生大同小异。
顾先生对会下围棋的小孩都很喜欢,都愿意教上几着。但真正被他收作学生的只有两人,第一个是吴清源,第二个就是我。1922年,顾先生31岁时,北京的西单有一个棋室叫做海丰轩,是顾先生常到之地。一天顾先生来到海丰轩,看到有一九龄孩童跟一老者在对弈。孩童虽小,却下得头头是道,一副雄才伟略的样子。老者在孩童的凌厉攻势下支撑不住,败下阵来。顾先生觉得此孩童颇为难得,于是让五子和他下了一盘,虽然孩童输了,但他的实力与素质却令顾先生惊叹。特别是他气派大方,与众不同,到了将输之时,他主动放下棋子认输,不作无理纠缠,很有大将风度。这孩童就是吴清源,当时叫做吴泉。吴泉是福建人,那时他全家要回福建,顾先生这位棋界伯乐不愿放弃这千里马。他说服了吴泉的亲属,设法把吴泉留在北京。然后顾先生每天早晨叫马车接吴泉到家中学棋。一天吴泉的母亲带着他来到顾先生家,要顾先生替吴泉取一个名字。那天正好顾先生的哥哥渊如也在座,他顺口说:“泉水是清的。”顾先生接着说:“泉水是源远流长的。”从此吴泉又多了一个名字,叫吴清源。
吴清源在顾先生的悉心培养下有了长足进步,才两三年时间就脱颖而出,成为棋坛强手。
吴清源13岁时,日本来了五段棋手井上孝平和六段棋手岩本薰。吴清源屡胜井上五段,与岩本六段下先二,互有胜负。同年,当时才四段的桥本宇太郎来我国,与吴清源下互先2,亦互有胜负。吴清源这个13岁的孩子以出色的成绩引起了日本围棋界的注意。在日本围棋界声望很高的濑越宪作等人的促进下,吴清源终于在14岁时东渡。从此在日本围棋界升起了一颗光彩夺目的明星。吴清源不但很快获得九段称号,而且以惊人的战绩称霸日本棋坛20余年。
吴清源去日本以后,经常和顾先生有书信往来。顾先生每当与人提起吴清源时,总是感慨万千、不胜怀念。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顾先生直至临终也未能与这心爱的学生再见上一面。
顾先生是30岁左右收下吴清源的,事过30年又收下我这第二个学生。吴清源的年龄跟我父亲一般大,从年岁上来说是我的长辈,从棋艺上来说则又是我的老师,但从两人出于同一位老师这一点来说,吴清源和我又是师兄弟,这关系有些微妙。我自幼年学围棋后心中一直很崇拜吴清源,很想有机会能见见他,欣赏一下他那令人神往的风采和棋艺,甚至还幻想能向他学上一盘。不料这些愿望和幻想后来都实现了。
顾先生是怎样一个人呢?他既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又是个不普通的人,你只要见过他一面就再也忘不了。说他普通是指他的外形,他没有刘棣怀先生那样魁梧的身材和大将风度,也不像王幼宸先生那样精瘦和有一个锃亮的头顶,更没有汪振雄先生那样一个奇特的大脑袋。他的个子是矮小的,不引人注目。虽然是花甲老人,却有一头茂密而乌黑的头发,顾先生把这么好的一头乌发剃得几乎精光,只留下那么一丁点儿。头发虽好,但绝非他的主要特征。他那突出的脑门下面的一双大大的眼睛才是他的不平凡之处。天下大眼睛有的是,但像他那样有神的却为数不多。他的眼睛是明亮的、机灵的、深邃的、具有洞察力的、富有经验的、闪烁着智慧的。谁如对炯炯有神这个词理解得不太清楚,那只要看看顾先生的眼睛就明白了。作为一个棋手,具有他那样一双眼睛,也就够了,那就足以说明他是一个聪明过人的棋手、一个了不起的棋手。也许这么说是夸张了,可我不信一个眼大无神的人能下得好围棋。谁要是看到顾先生的眼睛,便会感到此人不凡,绝不可等闲视之。谁要是已经和顾先生熟悉了,那更会在他的炯炯的眼神下对他肃然起敬。
襄阳公园的西边是襄阳路,在50年代,顾先生的家就在这条街上。由于近,又有茶室,因此襄阳公园是顾先生常去之地。襄阳公园的后面是新乐路,这是条特别短又很幽静的马路。很多人都认为上海是个拥挤不堪的喧哗城市,然而上海也有那么几条闹中取静、清爽惬意的街道,新乐路无疑是其中之一。这条路连一辆公共汽车或无轨电车也没有,因此尤其安静。由于解放前这一带是法租界,所以街上的建筑物主要是法式洋房和公寓。马路两边的法国梧桐长得很高大,伸展出来的树枝在马路中间会合。到了夏天,茂盛的树叶挡住了炎热的阳光,使新乐路成为一条清静而凉快的林荫道。我的家就坐落在这条理想的街道上。
我家和顾先生的家相距那么近,只需拐一个弯,这就给我学棋提供了方便的条件。可能这也是我的福分吧。上海那么大,如果我们两家相距很远,即使我拜上顾先生为师,又怎能经常向顾先生请教呢?
顾先生和刘棣怀、王幼宸等棋界老前辈一样,当时都是无职业的,只能凭着他们在棋界的声望下棋谋生。顾先生自己印了些票,每张票两角,10张票1本。一个爱好者如想跟顾先生学习一盘,那起码要买1本,即两元钱票,有钱一些的就买上两本。如果你只买1张两角钱的票,那根本不可能跟顾先生下,此时顾先生就让一位普通水平的棋手,大概比顾先生要差二三子水平的跟你对弈。
顾先生是国手,又是以棋谋生,收费下棋也是出于无奈。不过他辅导学生可根本不考虑赚钱,他在我身上倾注了很多心血,并经常为我破费。如从经济角度来说,那完全是赔本生意。我学棋不用交学费,这是因为顾先生不会接受。只有到了节日,才由我家里买些点心之类送去略表心意。由于经常跟着顾先生学棋,因此也经常随着他吃饭,有时在他家,有时由他带着去一些棋友家中,有时则被他带往饭馆。有一次他带我去淮海路上的一家西菜馆,每人吃了一只奶油全鸡,才9角钱。这顿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以后花9角钱再也不可能吃上这么一只全鸡了。
我小时候父母不给零花钱,我也从不买零食吃。顾先生有时在襄阳公园买些小吃给我。有一年暑假的一天,我下完棋要回家了,顾先生给我买了一个纸杯冰淇凌。我当时没吃,想拿回家与家人分享。我匆匆忙忙地走出公园,迈开两条小腿往家中飞奔。当时正是大伏天,好在公园离我家很近。我用手紧紧地抓住冰淇凌,生怕它掉到马路上。等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奔上楼梯,撞进家门,才发现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我伤心透顶地看着手中的冰淇凌——哎呀,全化了,而且几乎都泼在马路上了,只有杯底薄薄的一层冰淇凌水,才能证明这里的确有过一个冰淇凌……
我自从拜上顾水如为师后,几乎每个星期天,以及寒暑假的每一天都跟随着顾先生。起初一直由我父亲陪伴着(父亲为我的成长尽到了他所能尽的责任),久而久之,他对我放心了,于是让顾先生带着我一个人到处跑。
当时上海下棋的场所除了襄阳公园外,还有瑞金路上的品芳茶室和延安路上的延安棋室等。品芳茶室是下棋的爱好者最为集中的场所,里边的人不但下棋喝茶,也有吃饭的、抽烟聊天的,喧哗声很大,而且乌烟瘴气。我去过两三次,每次去印象都不好,实在不愿跨进这个茶室。不知为何,顾先生也很少带我去那儿,也许是刘棣怀先生常在那儿的缘故,因为“南刘北顾”之间有些隔阂。
由于跟随着顾先生,因此我能有机会接触社会上不少棋手。每当我和他们下完棋之后,顾先生就复盘指点。经常找顾先生讨教的还有其他几位小朋友,其中最突出的是赵氏兄弟,即哥哥赵之华、弟弟赵之云。他们比我稍大,棋艺和我接近。我和他们下棋时,顾先生总是很认真地观战。其实顾先生本人和我对弈并不算多,主要是讲棋,每过上一段时间,他才跟我下一盘。
在顾先生的不断指点下,我的棋艺有了较快的提高。我9岁那年顾先生让我5子下了一局,我获胜了。顾先生将这盘棋的棋谱寄给在日本的吴清源,1954年日本的《棋道》杂志上发表了此对局,并用中日两国文字登载了日本棋坛元老濑越宪作先生作的详细讲解。濑越先生在结论中说:“九龄少年有此奇迹,无疑是吴清源第二。”第二年顾先生又让我四子下了一局,我再度获胜。除了日本杂志以外,香港报纸也披露了这两次对局。由于顾先生的介绍,吴清源对我的成长也很关心,并希望我有机会去日本学棋。后来京剧大师梅兰芳访日拜访吴清源时,吴清源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顾先生有时也介绍一些外地棋手跟我对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和过惕生先生的对局。当时有个文化俱乐部在锦江饭店对面,里边有不少娱乐活动,包括下棋的场所。顾先生也经常带我去那儿,下完棋就在里边吃西菜。大概是在一个春节,文化俱乐部举行晚会,顾先生又带我去参加围棋活动,他让我跟一位外地来的棋手下棋,并告诉我此人叫过惕生。我刚踏入棋界就知道有这么一位高手,能向他学一盘当然是愉快的事。过先生比顾先生小十好几岁,他很和气,向我微笑着,一点也不摆架子。他讲话带着一口浓重的安徽口音,叫我似懂非懂。顾先生要我摆上4个子,下至中盘我取得了优势,过先生说自己输了,要让我3子再来一局。让3子我抵挡不住,败下阵来。过先生对我也很满意,夸奖了我好几句。这一天上海相当寒冷,而文化俱乐部内由于生了暖气,因此温度很高。上海市有暖气的地方实在不多,所以我很不适应,热得脸上通红。旁观者劝我脱些衣服,但我一则因为好不容易跟久闻大名的过先生下上棋了,心思都在棋上,其他的感觉神经都麻木了。二则我被这么些人围观,也很腼腆,不好意思脱外衣。所以我尽管出了一身汗,还是硬撑着。好不容易捱到对局结束,赶忙离开文化俱乐部,但此时觉得两腿已软得像踩在棉花上一样。再被室外的冷风一吹,很快就发起烧来。母亲一摸我的脸,直烫手,马上让我量体温,40度!母亲吓坏了,赶忙连夜送我到医院。大夫要我住院,可我从未跟医院打过交道,坚决不肯,于是,只打了退烧针就回家了。幸亏我身体还争气,很快就复了原。可这一来,却加深了我跟过先生下棋的印象。
在我11岁那年,顾先生只能让我3子了,甚至让3子也感到有些困难。这时如再给我加一把劲,让我向更多的强手学习,必将更上一层楼。但顾先生却没这样做,他像一个特别溺爱自己孩子的母亲那样,生怕我走路摔跤。当时,由于我年幼,因此在围棋界也小有名气。一般的爱好者见到我们,总爱夸奖我一番,更要颂扬顾先生教导有方。顾先生听了这些恭维话很高兴,也更宠爱我,不愿让我输棋。尽管还让我跟人家下棋,但都找些水平比我低的,结果总是我赢。由于缺少同强手对局,影响了我的继续提高。后来进了中学,由于应付学习,我又被迫放下了围棋。直至参加体育宫集训,命运才使我再一次执起黑白子。这期间我停顿了3年左右,这是我在围棋道路上的第一次停顿。3年的时间太宝贵了,幸亏只是3年。在体育宫中我跟随刘棣怀和王幼宸等老师学棋,这是我学棋的一个新阶段。由于成天向刘、王二老学棋,和顾水如先生的接触就减少了。后来我只能在体育宫放假的日子里去顾先生家,看望我的启蒙老师。
文化大革命中间,我和顾先生有好长一段时间未见面。那时我在北方的干校和工厂劳动,顾先生在上海也受到冲击,对于一个七八十岁的自尊心又特别强的老人,其精神上所受的折磨是可想而知的。顾先生80岁的那年,我有机会回沪一次。到了上海我很快就来到了顾先生所住的河滨大厦。我跨进那老式的电梯,在那长长的、有些阴森的走廊上快步走着。我的心在呼唤着:顾先生,顾先生!我推开了顾先生家的那扇门,他那宽敞的房间里有10来个小孩围在一张桌子旁,顾先生被这群小孩包围在其中。这些小孩都才10多岁,活泼可爱。而顾先生呢,已是一副老态,他直到70岁时头发还是乌黑的,如今却全成了银白色,连眉毛也白了,以前的精悍一去不复返了。然而有两点没变,一是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还是那么明亮,几乎和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一样。还有就是他对小棋手的热心没有变,他已接近生命的最后时刻了,但他还在继续传授自己的棋艺。他像一枝快燃完的蜡烛,仍然散发着光和热。这光和热是永恒的。这是我和顾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这次见面太深刻、太难忘了。这之后不久,顾先生出于无奈,离开了上海市,搬到他的老家——松江县。回去没有多久,他便与世长辞了。一代国手默默无闻地离开了我们……
我的每一点成绩包含着多少人的心血!每当我想起教导过我的那些前辈棋手,包括周己任老师,尤其是当我想起顾先生的时候,我常想,一个人如果自己成长了,便忘却了培育过他的人,那他的良心何在呢?
顾先生,您的学生在这里向您致以深深的谢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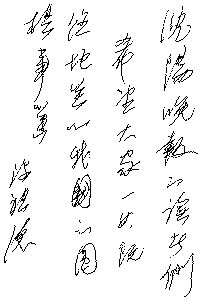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