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祖德:《超越自我》四
1959年是新中国诞生的第10个年头。这是体育事业兴旺发达的一年。这一年的秋天将要举行第一届全国体育运动会,这当然地成了体育界的头等大事。各地体委都在积极准备,凡属于全运会的比赛项目都抽调了人员进行集中训练。棋类也被列入全运会的比赛项目,于是不少省市体委从1958年底或1959年初开始搞这个项目的集训。其实棋类并非一个项目,而应当是围棋、国际象棋和象棋3个项目,正如足球、篮球和排球是3个项目而不能统称为球类1个项目。但是我们不少人认为棋类不如球类重要。这,作为棋手当然是不敢苟同的。不过一个
项目、一个事物,在它真正显示出它的意义和价值之前,往往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搞这个项目的人也不必光是感叹自己的不被重视,这是无济于事的。唯一的办法是全力揭示你们从事的事业的全部意义,然后才能赢得这个事业应有的社会地位。
正因为上面提到的原因,棋就三合一地成为棋类了。而且多少年来这已形成习惯,习惯也就成为自然了。不过我深信,随着棋的越来越被人们理解和重视,总有一天,棋类会一分为三的。
上海市体育宫集中了不少项目的运动员,除棋类外,有乒乓、举重、击剑、摔跤、武术和拳击等项目,真是热闹非凡。我是个中学生,以前很少接触体育,进了体育宫真是大开眼界。我好奇地观察着色彩纷呈的体育项目和朝气蓬勃、体格健美的运动员。棋手们都文质彬彬,处在这么多龙腾虎跃的运动员之中很是不协调。
一月份的气候是寒冷的,加上上海特有的潮湿使人的皮肤感到刺痛。我们棋队要和其他运动队一样出早操、练长跑。尽管我在工厂里有所锻炼,但其锻炼的性质完全不一样。如今要跑上1500米以至3000米,可真够呛。然而这对于正在发育的少年来说是不无好处的。
1959年是出体育人材的一年,各个项目都涌现出一批有前途的运动员。就拿棋类来说,象棋的胡荣华、国际象棋的徐天利、许宏顺和黄鑫斋、围棋的吴淞笙和我均在这一年得到培养和成长。在以后的多少年中,这批人都是棋坛的骨干。其他项目在这里不提了,但我不能不提一笔乒乓球。这年集训的乒乓球队伍规模较其他项目都庞大,从这批队伍中出了林慧卿、郑敏之和李赫男等不少有名的女运动员,她们都为我国的乒乓球事业作出了出色的成绩。只是我所以要特别提一下乒乓球,并非因为他们成绩出色,而是因为其中的女选手郑敏之在10多年后成了我的妻子。只是我们当时并没有什么青梅竹马的故事。在十三四岁这个似懂非懂的年龄上,男孩子和女孩子互相见了大都视为陌路人,不苟言笑。这也是人生的一个颇有特色的时期。
当时有两个项目引起我较多的注意,一个是武术队,另一个是拳击队。武术队和棋类队住得最近,因此我们经掌看到武术队员们训练。我对武术队所以感兴趣,一方面是由于刀、枪、剑、戟这些兵器吸引人,更重要的是武术和围棋尽管一个是武,一个是文,一个是动,一个是静,但都有数千年的历史,都是祖国的传统项目,都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精华。所以我对武术的感情从一开始就不一般。
另一个项目是拳击。这个项目的对抗性特别强,比赛起来较其他项目都更激烈、刺激,简直是惊心动魄,不能不使人感到有些残酷。我经常看到运动员在台上被打得鼻青眼肿、鲜血直流。当两个水平不成为对手的运动员在台上较量时,弱者只有招架之功。有时绕着那小小的场地来回躲闪、逃避,显得十分可怜。然而这个项目偏有它独具的吸引人的魅力。拳击运动充分显示出技巧和灵活、意志和毅力,更重要的是力量和强大。看到了拳击运动使我感到在运动场上必须当个强者,必须有压倒一切的力量和气魄。拳击是如此,下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人应当成为强者,即使今天是弱者,也要有志在明天成为强者,这才是有出息的人。可是拳击运动不久被取消了,其理由是:残酷。的确,看起来,拳击运动较之其他体育项目是残酷了一点。但依我看,或者说,从实质上看,任何体育项目,一旦比赛起来,哪项不是残酷的?因为在比赛中往往要你的肌肉和精神去承受那几乎无法承受的负荷。任何一个好的运动员在比赛中都会不顾一切地搏命,都会拚全力以击败对方,此时谁都不会顾及身体或精神的损伤,甚至把胜负看得比生死还重要。一个运动员苦练多少年,却只在一天之内、一小时之内或几分钟之内甚至在一刹那间决定成败,其心灵受到的震撼,精神受到的冲击,不亚于肉体受到的痛苦和损伤。因此拳击较其他体育项目残酷不过是表现形式的不同。可以说,只是量的不同,而无质的区别。
拳击被取消了,拳击手们失声痛哭,悲恸之极,这情景谁看了都会感到心灵的颤栗。是的,搞事业的人都应该具有这样的事业心——自己的痛苦或欢乐,紧紧地维系在事业上。不管所从事的事业怎样被他人不理解或遇到怎样的逆境,他偏能坚贞地爱自己所从事的这个事业。爱事业甚于自己的生命!拳击运动员的事业心震撼了我那还稚嫩的心灵。10年后,围棋也一次次地遭受到和拳击同样的命运。不过我这个围棋手已经知道为了事业该怎样像拳击手那样去拚上一个回合。我即使给打倒在地,也定要在10秒种之内站起来1,去拚下一个回合。即使不能光荣地获胜,也要光荣地失败。我唯独没有想到,当围棋事业终于能理直气壮地发展的时候,我却得了癌症。我过早地结束了运动员的生涯。我是一个胜利的失败者,还是一个失败的胜利者?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恐怕不用为了围棋事业的存亡再去拚搏了……
1959年,上海棋队参加围棋集训的除我之外还有两老一少,两老是刘棣怀和王幼宸,一少是吴淞笙。刘和王二老均已60多岁了,刘老是棋界著名的“南刘北过”中的南刘。人们平时称刘老为刘大将,之所以如此称呼,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形象和仪表具有大将风度。我总觉得他特别像扑克牌中的老K,魁梧的身材,方方正正的脸煞是威严,不过威严中又含有柔和。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是刘老的棋风战斗力强,魄力大,我国古代棋手好勇善斗的传统特点在他的风格上特别突出。他好攻击,更不愿被对方围歼,有时他由于舍不得一两个子而冒了较大的风险,耍起“大龙”来1。于是有人称他为“一子不舍刘大将”。这样说尽管有些艺术夸张,但还是较形象化的。虽然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刘大将的棋风的确带有无理之处,但从当时的围棋水平来说,要在棋盘上歼灭刘大将的“部队”也确实要有血战一场的勇气。恐怕也正因为如此,在刘大将的思想中增长了自负的因素,他在下棋时经常铤而走险。也许这是艺高人胆大的缘故吧。
另一位老先生王幼宸比刘大将还要大几岁。和刘大将胖胖的身躯相反,王老的体形就像一个惊叹号,干瘦而相当挺拔。刘大将是一头浓密的白发,王老的头顶则光亮可鉴。刘老是健壮的,王老是精悍的。他俩都精神饱满,但从体形来说,王老属于更长寿的类型。王老在青年时代身体很不好,吐过血,以后他以顽强的毅力锻炼身体,终于使体质日趋强健。他的生活极为规律,用雷打不动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的。如果到了他应该休息的时候,那么不管在干什么事情或者在开什么会议,他都会拂袖而去。谁如影响或干扰他那严格的生活规律,就有可能发生一场轩然大波。如此规律化的生活至少我还没见到过第二人。王老除了每天打太极拳外,还养成了长距离散步的习惯,只要两条腿能走到的他就绝不乘车。这些养身之道都是他能够长寿的诀窍吧。王老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他那一口顽固的北京话虽然在上海生活了几十年也未得到改造。偶尔在讲话中也掺上一句上海话,却完全是北京调的上海话。王老的棋风也和刘老截然相反。刘大将大刀阔斧、勇往直前,而王老则精雕细刻、老练持重。他虽然魄力不及刘老,但他的功力也相当深。他的棋稳健中带刚劲,尤其是他的水平发挥稳定,一般水平不如他的很难在和他的对局中得到侥幸的胜利。有的棋手或许能在刘老这儿捞到一盘,但在王老这里就没门儿。
王老是大器晚成的典型。年轻时他的棋艺平平,挤不进棋界一流,可越老越厉害,真所谓姜是老的辣了。年过60,王老被公认为是棋界的高手。他的顶峰时期就在体育宫集训的那个年代,不少血气方刚的年轻棋手遇到王老就胆战心惊。在我国棋界他的确是个少见的人物,有人称他是棋界的老黄忠,他是当之无愧的。王老之所以大器晚成,主要还是由于他自身的刻苦钻研。解放前他是个小职员,经济不宽裕,无法致力于棋艺的提高。解放后,尤其是1959年集训后,他除了对局外,一直手捧棋书,孜孜不倦,这才是他所以大器晚成的关键。一个咳血者和棋艺平平者,到了老年却成为精力过人者和棋界佼佼者。他从不感伤自己青年时代的境遇不佳或身体不行,而只知道每走一步便向目的地接近了一步。一个人到60高龄才杀出来,恐怕不能说他有多少天才了,但是他有的是意志力!人的成功自然包括了机会、天赋等因素,但是,使成功成为必然的,却只有一个因素——人的意志力。
王老由于棋谱钻研多,因此棋理清晰,他看到刘大将有时自恃气盛,着法不那么合乎情理,很不以为然,往往对人用那种纯粹的北京口音说着;“那个刘……”听他这么讲话我总是感到很有趣。可是王老在力量方面稍逊于刘老,因此两人一交手,经常是王老败下阵来。明知对手无理,却又拿不下来,王老颇为懊恼。
小将吴淞笙比我小1岁,我们是在1957年上海市比赛中相识的。那次我俩碰巧在一个小组
里,我原以为自己是参加比赛的选手中年龄最小的,不料遇到一位比我更小的,感到很惊讶。那时从棋力来说,淞笙显然不如我,但他一看就是个聪明的孩子,浓浓的眉毛下一双大大的眼睛,不时朝我望一下,使我感到很好玩。他的神情有些淘气,性格也的确活泼好动。他的棋也恰似他的性格,很有锋芒。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性格发生了变化,变得稳重、含蓄,棋风也随之而变化。说棋如其人,真是一点也不错。他对武术特别入迷,特别愿意听武术队员神聊,在体育宫中他就拜上名师,学起太极拳。也许,打太极拳是他改变性格的一个因素。
刚到体育宫时淞笙的水平比我差一先以上,后来我的水平提高了,他也相应在提高,但由于他的基点比我低,因此提高得比我还要快些。淞笙和我都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围棋手,我们一起成长、共同战斗。在以后的多少年中我俩一起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无数次棋战,随着围棋命运的变化又共同经历了曲折的生活。我俩曾一起达到中国围棋界的高峰,成为围棋史上的“陈吴时代”。
1959年的集训基本上是两老带两小。我的水平尽管比淞笙要高出一块,但比起二老则差距甚大,恐怕要差三个子。集训初期二老让我两子,我屡战屡败,毫无还手之力。在集训之前由于我缺乏实战锻炼因而棋力较弱,被人称为“书房棋”。集训后我看到自己成绩这么糟糕,缺陷又如此严重,不免有些灰心。回想起来,二老对我的培养可真不容易,他们为了激励我,就主动提出不让子下。尽管实力相差悬殊,但这样刺激一下,果真把我的积极性又调动了起来。在平时,高手与低手弈棋,总是让足了子才显得有风度,有的棋手甚至明明已经让后辈赶上了,还是迟迟不愿对下,还要让对方一先,以示“棋高一着”。人往高处走,一个人眼看着自己要被人家打败了,自然不好受。一个人能鼓励别人超过他,帮助别人超过他,这得有多高的境界!刘、王二老故意拉平距离,以提高我的自信心;二老故意造成这种“既定事实”:我的水平已经提高到可以和他们对下了。二老是想让我提前超过他们!
是呵,人就是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这样的境界。
是的,我们在学下棋的同时,也在学做人。
二老训练我们的方法说来也简单,就是下,下完作一番简单复盘1。日复一日,天天如此。这样的训练方法最单调,但也最有效。水平低的年轻棋手要想快速提高,最好就是有条件向高手讨教,通过实践来学习。因为对局中能够学到布局、中盘、官子2及形势判断等各方面的知识,又能不断增加实战经验,还能迫使高手认真思索,拿出看家本领。当然研究棋谱也有利于水平的提高,不过比起和高手对局总是第二位的,是辅助性的。如今我国的年轻棋手多了,这是个好现象,但从向高手学习的这个条件来说,他们却不如我和淞笙在1959年的那个时候。从这一点来说,我和淞笙是有福气的。
回想起来,刘、王二老可真是不容易,要在以往,你不进贡一笔钱、一顿好饭,岂能有机会下上一局。即便我们每天相处在一起,如果老先生有较多保守思想,那又岂能热心辅导晚辈。当然这主要是新社会给我们创造了条件,使老棋手们不用担心教了后代,丢了饭碗。但我们不能不看到老前辈的胸怀和境界。多少年来每每别人讲起我的些许成绩,我便想起老前辈们花在我身上的心血,想起这些六七十岁的老人,天天陪着我们对弈,天天如此呵……
老前辈们扶着年轻一代在棋艺的道路上前进,使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一些老棋手花了几十年走的路,我们只花了一两年时间。我们完全不用像资本主义国家的运动员那样花费昂贵的金钱到处拜师,国家给我们安排好了一切:吃饭、穿衣、上文化课、请名手教棋。我们唯一的事就是努力钻研,我们的生活是单纯而充实的。
在集训期间,有时还请社会上的一些高手和我们一起训练。经常和我们对局的有汪振雄和魏海鸿两位老先生。他俩也都是国内的一流高手。这两位老先生有不少共同之处,首先在棋风方面都属柔和型。刘棣怀和王幼宸二老虽然棋风上有明显区别,但都刚直。汪老着法轻灵,如蜻蜓点水,思路敏捷,且灵活多变,善于腾挪。魏老富于弹性,擅长收束。他的官子可称一绝,往往在中盘魏老还处于下风,然而不知不觉在收官1中却被他逆转。
在性格上,汪、魏二老也有共同之处。他俩都很随和,从不训人,也从未见过他们生气、发火。他俩都较胖,不过汪比魏更大上一二号。魏老恐怕是缺少牙齿的缘故,因此有些瘪嘴,像个善心老太太。汪老的脑袋奇大,虽然我和淞笙的脑袋也显然是大号的,但比起汪老则是小巫见大巫。他脑门大、后脑勺也大,整个脸盘也大,看上去沉甸甸的,像个大冬瓜。我想除了汪老的那个身躯和脖子外,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能承受住这个大脑袋。大家平时都称汪老为汪公,也给了他一个外号叫“汪大头”。汪公总是笑呵呵的,神情像个菩萨,加上一个兔子嘴巴,看起来很有趣。他一点架子也没有,下手找他对局他总不拒绝,至于怎么下法往往是听下手的,哪怕是差二三子的下手要跟他分先他就分先,甚至要执白,他也无所谓,真是个好好先生。像汪老这样随和、谦逊的好脾气在棋界可谓独一无二。
汪、魏二老还有个共同的爱好,即嗜好喝酒,不过表现形式不同。每当吃晚饭时,汪公手持酒壶,蹒跚地走向运动员食堂。在挤满年轻人的食堂中,他把酒壶往桌子上一放,犹如鲁智深一般,旁若无人地喝了起来。魏老则不同,衣兜里总有个小酒瓶,边下棋边喝。走上那么几步棋,拿出酒瓶往喉咙里灌一口,然后心满意足地叹口气,又继续下。
和汪、魏二老对局也使我得益不浅。由于我经常跟刘、王二老对局,因此自己的风格也较刚硬。初次遇上汪、魏二老很不适应,力气总使不上去。他俩像打太极拳似的,很巧妙地把我的力化掉。尤其是汪老,他的棋好似泥鳅,怎么也抓不住。当我有时已能取胜刘、王二老时,见了汪老还是没门儿。在经过较长时间的磨炼后,我的棋路才开阔起来,棋力也随之得到加强。我可以肯定地说,后来我的棋不但比较有力,而且较灵活多变,是和上述这些老先生的帮助分不开的。可以说,在我的棋艺风格中包含着刘老、王老、汪老、魏老等老前辈的风格。从围棋这个角度来说,没有老一辈就没有我。
我在体育宫集训时,瘦瘦的、白白的,戴了副眼镜,像个文弱书生。又由于怕陌生,一说话往往要脸红,所以显得腼腆而拘谨。然而我的内心和外表却不尽相同,我有着较强的自尊心和抱负。从小我讲起话来口气就较大,家里人经常说我说大话。但我心里的确感到没有什么事高不可攀,人家能做到,为何自己就做不到?在体育宫集训不久我心中就有个目标,认为自己一定能把围棋下好。一天临睡时,大家随便聊天谈到水平问题,不知谁问到我:“祖德,你感到自己水平怎么样?”
“我感到自己一定能下好的。”我躺在床上脱口而出。
由于我的口气很大而且漫不经心,一个象棋队员开玩笑地说:“你这臭棋还要吹。”
我蓦地从床上坐起来,使劲说:“我一定能得到冠军。”
“你这水平能当冠军?嘻嘻!”
“你看不起人!”我刷地站了起来,平时文质彬彬,此时却要动武了。
那个队员一看我认真了,马上语气缓和下来:“不要当真么。”
我也有些后悔,干吗动火呵!虽然如此,心中仍一直不能平静,就这样,我一夜未眠。在这个不眠之夜,我多少次在心中发誓:一定要拿到冠军。
我从小爱看小说,在小学时就已看了很多我国古典文学作品,这当然和我父亲教古典文学有关。我、姐姐和弟弟三人,在刚认识字时就由父亲教我们背诵唐诗和宋词,我对背诗实在不感兴趣,非常勉强,只是慑于父亲的威势,无可奈何。我尽管讨厌背诗,但看书的习惯却从小养成了,即使到了体育宫集训也不例外,体育宫隔壁的上海图书馆给我提供了方便,我每天中午吃了饭就直奔图书馆,利用他人午睡的时间阅读各国名著。我特别喜欢有气魄、有分量的作品,比如像维克多·雨果和杰克·伦敦的作品。我也爱看有关大人物的著作,譬如拿破仑的传记。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句话使我很有感触。我就想,一个运动员如果不想当个冠军那怎么能是个好运动员呢?而我如果不想夺取全国冠军又有什么出息呢?
前文我说过,在提高棋艺的效果方面,看棋谱比起对局来说是第二位的。但这绝非说研究棋谱无关紧要,相反,是很必要的。因为在棋谱中总是有很多东西在自己对局时遇不着。在体育宫的集训中我不但学习了很多日本棋书和各种围棋杂志,还花费了不少精力研究我国古谱。我国古代棋手虽然不注重理论,没有现代围棋这么多布局和定式的变化,但仍有很多可取之处。古谱中看不出消极保守,处处闪烁着古代刀枪相见、短兵相接的那种拚搏精神;古谱中也看不到花拳绣腿,每一着都对准了对方的要害并回避着对方的“火力点”,就像古
代那些足智多谋的军师那样显示着智慧和胆识。这是我们先辈的气质,是敢于战斗、善于战斗的好汉气质。这种气质在现代棋谱上是不易看到的,所以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看了很多中国古棋谱,其中印象最深和受益最大的是清代的围棋巨著《寄清霞馆弈选》,一套16本,包含了清代几乎所有围棋名手的精彩对局。这本棋书无疑对我的棋力提高起了作用。
近几百年,日本棋手在围棋的理论方面作了很多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他们对围棋的重大贡献。的确,日本把围棋技术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把“座子”1取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我们学习日本的围棋技术也不能盲从,不能认为他们的技术都那么完善。我认为现代的日本棋手也存在一些缺点,从总的来说,他们的战斗力不够强,因而较讨厌和害怕白刃战。正因为如此,中国去了个吴清源就能击败所有强手,称霸棋坛。也无怪乎他们称中国的围棋手都力量强,尽管现在很多中国棋手天天研究日本棋谱,有的几乎没看过一盘中国古棋谱,但在日本棋手看来,还是中国式的力战型。可见如今我国的围棋手多少还保留着祖先的气质。此外,日本棋手的思想是偏保守的,这恐怕是太重视胜负的缘故,因而就缺乏创造性,容易产生教条主义,一旦有人下出一种较成功的布局或定式,很多人就盲目跟随,以至很多棋谱显得清一色,缺乏生气。当然,日本也有些优秀棋手具有独创性并显示出广阔的艺术境界,但就总体而言,日本棋手是偏保守的。
我年轻时学习棋艺有个优点,就是不盲从。我始终有这么一个信条:你要超过水平比你高的棋手,就必须不跟着他,必须具有他所没有的特点,必须形成自己的风格。上海有个二流棋手叫章照原的,他喜好研究古怪的冷门定式,一心一意想让人中圈套。在一次比赛中,王老、魏老等几个名手居然都中了他设下的圈套,很为有趣。我感到像刘老、王老这些有名望的棋手虽然水平很高,但也有明显的不足,尤其是在接受新事物方面。
在我的心目中也崇拜一些中外名手,如我国的施襄夏、范西屏以及日本的很多高手,但我在学习他们的棋谱时也不完全是学习他们的好着,同时总要找他们的问题、挑他们的毛病,事实上他们的确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正因为这样,我越看棋谱越能增强自己的信心。
上海是围棋高手最多的城市,因此经常有各地的围棋强手前来交流、学习。那时到上海来交流的著名棋手有四川黄乐忱、广西袁兆骥、河南陈岱等,他们在省里都是棋坛权威,有着很高的威望,在棋艺上也都有独到之处。这些强手到了上海往往是先跟上海社会上的一些棋手对弈,尽管这些上海棋手也都有一定实力,但外地这些名将每人都有几下杀手锏,尤其是气势很壮,因此很少有人能抵挡住。这时,他们就来到了体育宫。
刘老和王老当然是全国最强的棋手,但他们也清楚,外地这些高手不可等闲视之。因此二老经常让我先上阵,一来让我得到锻炼,二来也可摸摸这些人的底。我陈祖德的名字当时虽已在棋界被人知晓,究竟一无战绩、二无资历,因此还不足以被人重视。外地强手由于二老让我下,也无可奈何,可劲头总不是很大。反之,我士气旺盛,因此这些强手都一一败于我的手下。刘、王二老看到我获胜,于是让淞笙上,淞笙不仅年岁比我还小,而且在棋界更无名气,这些强手就不痛快了,但鉴于已败给我,只能再屈就一下。淞笙当然很认真,但有的对手就沉不住气了,边下棋边嘀咕,老大不满意。最有趣的是淞笙跟陈岱一战,陈岱是中原棋王,来到上海一心想跟刘、王二老下上几盘,较量较量。不料如今坐在棋盘对过的是个毛头孩子,实在懊恼,怎么也控制不住失望和埋怨的情绪,一直在唠叨:“我这个河南冠军,中原无对手,想不到来到上海只能跟小孩对局,多没意思。”谁料到淞笙也有很强的自尊心,他因年岁小,在名手前不敢还嘴,一肚子的气使劲憋住。对方嘀咕个没完,淞笙的火气越来越大,尽管脸上还平静,但已是爆发前的火山了。对局进行了一大半,火山终于爆发了,只见淞笙猛地把整个棋盘掀起,满盘的黑子白子飞腾起来,又哗啦啦地撒了一地,好似天女散花。中原棋王就此惊呆。事情突然闹大,但也不能责怪谁,陈岱的心情可以理解,而淞笙呢?如换个别人也完全可能爆发,只是形式可能不同。一个围棋手没有很强的自尊心也是成不了气候的。后来陈岱对淞笙的棋艺还是相当赞赏,而淞笙对陈岱仍很尊重。这次对局成了一个棋界趣事。
体育宫是棋手的摇篮,也是冠军的摇篮。我在这个摇篮中成长了。我睁开的眼睛看到了五彩缤纷的美妙世界。我感谢新中国给我提供了这么好的条件,也感谢哺育教导我的老一辈,他们都是受人尊敬的长者,都是永远值得我怀念的老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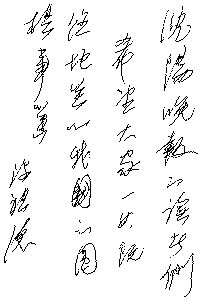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