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容妈妈日记:给父亲的一封信《中》
你和同事朋友们
你的同事和朋友很多,因白天有大量的教学任务,大家聚在一起主要是傍晚那几个小时。我印象最深刻的好象是下午五点半钟吃晚饭,到八点钟才各自回来备课。在这段时间里大家在一起是你们最快乐的时光。
这中间有近三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同事中女教师不多,只有五六个,大部份都是仁寿师范学校毕业后分来不久的年青人,有的弹琴,有的打乒乓球,大家都没有成家,几乎没有看到一个忙于家务事的,尽情的玩耍。
男教师也是年青人多,一个星期学校组织一次兰球赛,还要求社会上的人参加,也是彰加场镇上最热闹的一个下午,那必竟是小地方,五十年代又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所有休闲的人都来看热闹,还包括周边的农民,那场面很热闹的的。
其余的几天的时间都是自由安排,大家比较集中的地方主要还是学校后面那小山上,要说是小山也不是,它和学校的最高教学楼是平行的,那里也是周围的最高点,站在小山上周围望去,所有的景色尽收眼底。
夕阳西下,天空中五光十色,太阳的余辉和云彩变换无穹,使人留念忘返,下面,劳动一天的农夫有的收工回家,有的还在加紧耕作,只见远处近处的农舍中炊烟缠绕,鸡招呼同伴回茏的叫声,鸭子结伴回家的欢呼声,组成了一副美丽的田园风光,这时,也是你们几个教师谈笑风生最佳的时候。
这一群同事中数你的年龄最大,他们是十几岁,最多二十几岁,最喜欢听你讲的所见所闻,我当时发觉你的口才极好,讲得那些同事专专心心的听,有的同事还听得捧腹大笑,当然也说些奇谈怪论,不三不四的话,大家笑过了还故意看看我,心想,也不知这个小家伙听懂了没有?我长大了细想起来,只是说说笑而已,实际上没有一点科学根据,
我记得有次一个老乡寄放了一付“滑竽”在学校,你们几个老师心血来潮,说要坐坐“滑竽”,享受一下坐“滑竽”的资味。那个抬呢?没有人抬,只好轮流坐,轮流抬,大家抬上同事在周围学校不停的转呀转,有时还故意晃动“滑竽”造成“要出事”的假象,弄得得大家笑声不断,最可笑的还是外面玩够了,大家要抬上“滑竽”爬石梯,这个石梯是校内的一个分界线,下面是一小部份教室,和校门及广场,上面才是礼堂和办公室及教学楼。石梯有三十米长,坡度是五十度以上,不管是抬的坐的都是一种冒险行为,这下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两个人抬上还必须要两个人扶上,坐“滑竽”的人必须牢牢抓紧竹竽,在这种情况下也是不停的抬上抬下的,年青人就是好玩,引来周围一遍大笑声。
学校组织的剧团和歌舞班子
当年除县城外,区乡基本没有专业演出人员,要拿上台面的更是少之又少,学校成了文艺演出的中心,只要各乡有庆祝活动都有要请学校派出教师搞演出,教师中也成立了各种临时演出班子,在我的记忆中主要是以歌舞,小品,话剧居多,有时忙不过来,再找场镇上喜爱文艺娱乐的年青人助阵。
演话剧时台词较多,就在幕布边摆上一张小桌,找人念台词,这样才能和演员含接得上。从当年的情况看,只有在教师中才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只有从那里才能找出人材来。
不过我记得,你是演话剧和小品的,可惜我一次也没有看过你的演出,演出往往是晚上,我还小,我等不到深夜,而且人多也杂,怕丢失掉,事后有些老师有评论,我是断断续续听到一些,我听他们说你是弹长吹笛和洞箫,我好象记忆不起了,大哥继承你的优点,他在吹、拉、弹、上还真有一套,我不行,只会听,表演不来。
另两个老师就是万玉蓉和汪国勋,他们夫妇的演出是轰动了当地的。在五十年代是常成盛不衰的。他们的歌唱得好,人材也好,是一对最佳夫妇。很多年过去了,大家只要提起他们还是赞不绝口的。
这里还闹出过一次大笑话,有次女演员在演出时相当投入,跳呀跳,不小心还把裤子跳掉了,闹成了十几年的笑话。
总之在五十年代的前五年,社会是安定的。人民是幸福的。自从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斗争后,社会空气突然紧张,各种不幸的事都降临我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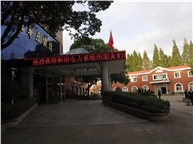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