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雅意 秋水文章——追忆沈培新同志的人品官品
原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省文联原党组书记、主席,安徽老年大学名誉校长,省老年大学协会顾问沈培新同志因病经抢救无效,于2012年3月28日在合肥逝世,享年77岁。沈培新同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出了毕生精力,为我省老年教育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期我们特约张和敬同志的追思文章,以表示对沈培新同志的深切怀念和崇高敬意。
——编者
沈培新同志走了,悄无声息地走了。
我因去冬今春寓居外地数月,直至四月九日方才听一位老朋友告知此事,震惊之余赶忙在网上查看,果然得到证实。网上公布了他的简历、遗嘱以及一些简短的悼念文章,这使我回忆起与沈培新同志交往的点点滴滴。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中期,我与培新同志在一个单位共事近十年,其后的几十年也一直交往不断。他大我十多岁,是一位我尊敬的长者,他有思想、有才华,工作有能力、有创意,而且由于“出道早”,经验丰富,活动能力强。1982年,他担任省委组织部干部三处副处长,主抓干部教育工作,在他的建议和努力下,我省在干部培训方面拿出不少创造性的举措,取得显著成绩。比如,当时各个地市委及组织部门普遍反映:经过“文革”十年蹉跎,各地党政机关里的文字秘书奇缺,于是他利用在合师院工作过的优势,委托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举办了一期秘书进修班,各地市和省直部分厅局输送了几十名秘书人员,安师大挑选最棒的师资力量对这批同志进行强化培训,效果甚佳,这些同志后来绝大多数都成为了机关搞文字的骨干,其中有一、二十位担任了有关地市党委、政府的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或省直厅局的文秘骨干。我本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
1983年,各地进行机构改革,提倡“四化”,大幅度调整领导班子,这期间有不少年轻、学历高的同志甚至得到越级提拔,当时,沈培新同志是省委组织部机关呼声最高的二、三名中层干部之一,但最终上级批下来的副部长人选却没有他,尽管如此,他的情绪并没受到影响,仍然一如既往地兢兢业业工作。作为干部三处的处长,他除了认真抓好全省的干部培训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之外,还积极联络和筹划在我省绩溪县召开的以华东片为主的八省市干部教育理论研讨会。到1985年秋此次会议召开时,沈培新同志虽然已经调省教育厅担任副厅长,但由于前期筹备工作扎实认真,会议开得很成功,共收到论文108篇,时任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的赵启正同志也来参加了会议,并提供了论文《谈谈干部教育中的党性教育问题》。中央组织部干教局、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与会的各省组织部长,以及专家、学者对这次大会的筹备和安排给予了很高评价。我也亲历了会议筹备、召开的全过程,前来绩溪县参会的不少外省市组织部门的领导同志还纷纷询问沈培新同志的近况。
在此前后,沈培新同志还与安徽日报的金志华及我省社科界的一些同志,针对一大批新近走上领导岗位的年轻干部在新时期遇到和可能遇到的实际问题,筹划写作一本《青年领导者哲学》,以答疑释惑。待到着手撰写的时候,他因担任省教委副主任,领导工作繁忙,就把本应自己直接撰稿的一部分内容委托我与汪世来同志撰写,这是我参与省委组织部编写的《做合格的共产党员》一书之后,第二次参加正式出版物的写作,当我从他爱人周老师那里拿到他写给我的委托信及有关资料时,内心的确非常激动和感激。这本《青年领导者哲学》于1988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王照华同志欣然撰写了《和年轻干部谈成长》一文,作为该书的序言,阅读过此书的年轻领导者,都认为对于他们在新时期开创新局面大有裨益。
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间,我们各自的工作岗位都经历了不少变动,但却一直保持着联系。1991年至1993年我在霍山县挂职先后任副县长、副书记,后期应新华出版社之约(陈桂棣推荐),与郭明英合作出版了反映大别山革命老区脱贫致富的一本长篇纪实文学《走出大山的困厄》,该书正式出版后,我恳请沈培新同志为之写一篇书评,他愉快地应允,不久就满怀深情地写了《革命老区的新赞歌 -- 长篇纪实文学<走出大山的困厄>评介》。到了1999年年底我在黄山市工作的后期,又写作了一本介绍黄山风景名胜的著作《寻梦到徽州》(与程春雷合作),由黄山书社出版。新书付梓之际,我又一次恭请他写一篇书评,而他也又一次欣然命笔,写出《美景造徽州》,发表在《安徽日报》上。1995年和2002年,沈培新同志也先后出版了《岁月流韵》和《岁月流痕》两本著作,为我撰写的上述两篇书评就分别收入在这两本著作中。新书敷一印出,他又郑重地签名赠与我和我爱人(我爱人曾在安徽省委宣传部供职20年,也是沈培新同志的同事和部下),这其间的同志情、朋友情于此可见一斑。
沈培新同志在评介《走出大山的困厄》的文章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在报刊上,经常读到和敬同志的文章。他是一个谦虚好学的人,对事业兢兢业业,对同志热情诚恳。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总给自己的工作,留下点点滴滴的财富,这是十分可贵的。愿作者能经常到主战场上去汲取营养,用自己的手为四化建设添砖加瓦,用自己的笔撰写更多更好的作品。”这是对我的鼓励,更是鞭策。我在以后的诸多岗位上,总是把这番话当做座右铭,一直努力去做、去实践,不敢有丝毫懈怠。
其实,沈培新同志自己就是一个勤奋、刻苦、好学又善于钻研的人,是一个兢兢业业干事,大胆实践,又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直抒胸臆的人。他曾在《岁月流韵》的自序中写道:“我的经历不是学什么干什么,谈不上专业对口,而是干什么学什么,实实在在地工作。”换句话说,就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专一行。沈培新同志干过人事、组织、教育、宣传、文化艺术,每到一处总能钻研出点道道,干出点名堂。所以,他在各级各类报刊上发表过大量文章,主编过一系列的书籍。在一些悼念文章中,有人称他为教育家、理论家、社会活动家,有人称他为平民官员,这些都不为过。我倒认为他的最大长处是两点:无私与宽厚。他廉洁、坦诚、正派;他胸襟博大、有亲和力。他处处为他人着想、为工作着想、为百姓着想。
“春风雅意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用此概括他的一生,概括他的人品官品,应该是十分确当的。
记得沈培新同志还牵头主编过一本《人生百年不是梦》,鼓励老同志愉快生活,健康长寿,你自己怎么就过早离去了呢?真是造化弄人。我将培新同志不幸去世的消息用短信发给在外地的妻子,并且告诉她我正在写一篇悼念文章。她在回复短信中表示遗憾、惋惜,之后却又平静地说,都这个年龄了,今后这类事(指老友们离世)还会很多。是啊,这是自然规律。这倒使我油然想起林黛玉葬花词中的两句词:“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作者系省委统战部原副部长,曾任省政协常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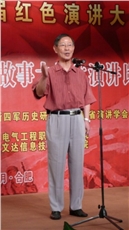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