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分子春天的日子里
1985 年,我从省委组织部重回教育界,时任教育厅副厅长,先后分管过职业教育、师范教育、普通教育和成人教育等,参与了当年的安徽教育改革工作。回顾这段历史,对安徽教育事业的发展或许会有某些启示。
解放初期,安徽教育落后,教育欠债很多。尤其是十年“文革”,“停课闹革命”、“知识越多越反动”,大批教育界知识分子和学校领导被批斗,大学拆迁,中学下放,给安徽教育
带来了空前的灾难。1977 年恢复高考制度后,教育呈现新的生机。1985 年党中央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的同时,作出了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并采取了许多相应措施。同年我参加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参与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一、普及义务教育举步维艰
如何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在1985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展开了一番热烈的讨论。当时国家还拿不出更多的资金来支持教育,于是决定开两个口子:一是收教育费附加,二是可
以集资建房。在“科举制度”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追求学历和文凭这个“指挥棒”,造成了我国教育的畸形发展和教育投资的失衡。从总体说,中国的教育投资偏低,1980年教育经费在公共开支预算中,中国占7.8%,而泰国为20.6%,日本为17.6%,南斯拉夫为32.5%,非洲为16.4%。在教育支出中,我国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重城市教育,轻农村教育。以1986 年为例,国家投入的生均费用大学为2370 元,高中、中师为1012元,初中为103 元,小学仅为56 元,农村小学更低。基于这样的国情,既要普及义务教育,只好走“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的路子(山东的提法),加大人民的负担尤其是农民的负担。这就是1985年教育体制改革,在这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许多省的代表尤其是基层代表,都认为这实际上是国家把“包袱”下放到基层。可是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是我国整个教育事业的基础工程,是国民素质提高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发展的起码人力资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如此。
二、不要棒打基层学校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安庆地区有人民来信到中央,反映怀宁县教育有严重的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片面追求升学率有一定的社会根源,我们的教育尚欠公平,发展不平衡,加上人事、就业、晋升等制度均与文凭学历挂钩,因此追求升学率是满足人们的欲望和谋求生存发展的必然选择,所以我在分管普通教育时“顶风”支持办好重点高中。而事实上,重点高中办得越多,人才外流越严重,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基本上都留在大城市就业,很少回到本地,更去不了农村。可是“跳农门”、“进龙门”是广大农民的愿望,我们只能顺其自然。关于怀宁县的“升学率”问题,我们采取全面调查、深层分析、直面现实、实事求是的态度。调查报告直接寄到国家教委,希望决策机关不要棒打基层,更不要去责怪学校校长和教师,而要从高考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的改革入手,删简课程和教学内容,改进教法、考法和学法,等等。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必然带来教育的不平衡,“一张文凭定终身”是客观存在的。今天,均衡教育正在推进,高考制度正在改革,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更新教育观念,深化教学内容方式、考试招生制度、质量评价制度等改革,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我国的基础教育面貌将发生很大转变。
三、力求增加教育投入争得外援
当时,知识界、教育界、人民群众对我省教育经费不足反映较多,尤其是农村教育困难重重,因此在讨论起草政府工作报告时,我们总想力争多要点教育经费。一天,王郁昭省长对我们说,关于教育经费问题,以后你们不要再提了,安徽人均教育经费比人均财政支出还高一二个百分点,可以了。安徽现在是“吃饭财政”,还不可能有更大的投入,希望教育界能够理解。《人民日报》驻皖记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消息,说安徽省花“血本”支持教育,结果人大代表意见纷纷,说下面教育经费如此困难,还说花了血本。事情是辩证的,有的贫困县当时教育经费支出的确要占到财政支出的50%左右,有的甚至更多,说花血本也未尝不可。即使这样也的确无法满足教育的需求,尤其是在农村学校,有的没有教室,有的没有课桌椅,有的只有一块八寸见方的小黑板,有的老师用的粉笔都是一支一支发的,有的危房更是让人揪心,每逢刮风下雨,校长就担心出危险。农村教师待遇很低,尤其是民办教师更是在艰难维持最基本生活的状态下为社会作贡献。我陪中央讲师团成员(支援教育的中央电视台成员)到利辛县农村,他们在看到学校困境后眼圈都红了,纷纷从自己的衣袋里掏出仅有的钱送给学校。
为推进教育改革和发展,国家教委在京召开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召开十省分管普教的省教委副主任座谈会。我们其中有几位相交较多,一起商量去中南海开会谈什么?大家认为,大政方针已明确,而且高考改革时机还不成熟,我们就当“伸手派”,围绕着增加教育经费而谈,有苦说苦,有难说难,有办法说办法。尽管主持人一再要求我们谈谈学校德育、师资队伍、教育质量等等,我们绕来绕去还是讲投入,并提出三条思路请予考虑:一是学习日本经验,加大教育投入,尤其是基础教育要加强,相对放慢其他方面建设速度;二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面向农村,面向实际,面向落后;三是放宽政策,社会各界支持,赞助放开,允许私人和社团办学,该收费的就收费,不要老是批“乱收费”。主持人当然不同意这三条,参加座谈会的同志问:那教育问题怎么办呢?我们不能把困难转嫁给政府和社会!
据统计,当时全省7~15 岁残疾儿童约为36.6 万人,其中弱智儿童23.74 万人,入学率仅为0.03%。英国驻香港办事处的救助儿童基金会主任巴克尔先生在中国寻找弱智儿童“一体化教育”的合作伙伴。我省南方由于水土和近亲结婚的关系,弱智儿童的出生、教育和提高生存质量等问题急待解决。经过争取,安徽和云南争得了援助。在黄山区甘棠和马鞍山市开办了两所弱智儿童一体化教育试验幼儿园。弱智儿童一体化教育是指轻度和中度智残的儿童和正常儿童一道在一个班同样学习,可以得到正常儿童的帮助和启迪。从幼儿园开始,争取同上小学,直至小学毕业。考虑到弱智儿童上学不便,他们还专门捐赠了一部豪华中巴。为培养一体化教学骨干,他们还邀请两所幼儿园老师去香港培训。
改革开放30 年,人们感慨最多的,也许是那些看得见的方面,如城市发展、道路建设和家庭生活变化等。但实际上,教育发展很快,变化很大。“农业税不收了”,“念书不要钱了”,这是中国农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明亮教室、现代化设备、高水平师资、优质均衡教育正在逐步推进,尤其是以乡镇为主的管理体制回到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人民负担的部分由公共财政承担,这是历史的进步!教育振兴,必然为提高整体国民素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作出更大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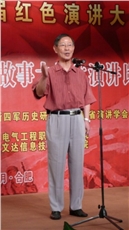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