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五 女 村 历 险 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小故事
贺 明
1942年“五一反扫荡”后,青纱帐凋敝前,上级命令,凡在冀中坚持的团队,都必须转移到平汉路西(今京广路)的山区根据地休整待命。
为了给本团(22团)作顺利越过铁路封锁线的准备,梁达三政委命我带一名侦察员到定县明月店一带的敌占区,通过地下组织了解敌情,选择有利的过路口和隐蔽的宿营地。
领受任务的当天,我便和侦察员陈凤堂到了目的地。经过两天的工作,各项任务都顺利地完成了。但在返回根据地的路上,由于一时的麻痹大意,险些遭到一次致命的损失——不是被敌俘杀,就是在搏斗中战死。
经过是这样:
正是八月的中旬,高杆农作物已形成了绿色的海洋。我俩途中虽然要绕过敌人许多碉堡和沟壕封锁线,但在青纱帐的遮掩下,又都身着便衣,这已不是什么难事了。
那日早饭后,告别了地下组织的负责同志,便向着我团的联络站——定南县的大定村前进。
在三伏天的太阳下行走已经是够热了,而在密不透风的青纱帐里穿插,除热之外,还有个闷,简直像进了蒸笼!汗流浃背,由于出汗过多,喉咙干渴的像火烧似的。
忽然从右面的玉米地里传出嘎吱嘎吱吊杆打水的浇园声。水的声音对于我俩来说,是多么具有吸引力啊!于是,便寻声来到井边,可不是嘛,一位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正赤着膊一上一下地提水浇园。我俩向小伙打过招呼,便蹲到井边掬水喝。好甘甜清凉的水啊!便一气喝了个饱,待喘过气来,向小伙随便问到:
“同志,前面是什么村子?”
意外的是,小伙子用疑虑的目光打量着我俩,冷漠、低沉地答道:
“大——五——女”!
“啊,到了大五女!”我自言自语地说。因为“大五女”是敌人的一个老据点。营盘扎在村东头,营地还筑了四五丈高的大碉堡。这我们都知道。
我又问:
“敌人今天出动了没有?”
这一问不打紧,小伙子竟惊恐地直愣着两只眼睛瞪着我俩,半晌也不开口。小陈等急,又重复了一句,小伙子这才慢慢腾腾地从牙缝里蹦出四个字来:
“我——没——看——到”!
这话可以理解为敌人没有出动,也可以理解为敌人虽然出动,可我并没看到。显然,这是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加上他先是疑虑,继而惊恐的样子,我们应该从中察觉出点什么味道来;但是,由于当时思想麻痹,未去细想,所以什么也没发现。
既然没有发现新情况,当然还按原计划——从大五女村西边穿过公路,直奔大定村。遂沿着田埂儿,向南走去。
哪里知道,一走出玉米地,景物大变——青纱帐消失了,摆在眼前的是一片长着低矮作物的开阔地(这是鬼子为扫清射界严禁在据点周围种高杆作物的景物),这时,要直插过去,少说也有二里地,向东看,就是敌据点“大五女”。村边距我们俩的脚下也不足二百米。就连碉堡上的“膏药旗”也看得一清二楚。我俩边走边看,待目光扫到西边时,哎哟!更严重的情况出现了——有一长溜穿着黄军装带着钢盔的敌人:前面打着太阳旗的是尖兵,接着是骑兵,再是干队。距我俩也就是三百多米远,正沿着我俩拟穿过的公路,朝他们的老巢——大五女村行进。小陈一面保持着行进姿态,一面压低嗓门急促地问道:
“总支书,西边有敌人!看见了吗?怎么办?”
我立即斩钉截铁地说:“看见了,进据点!”
为什么这样办呢?我当时只是这么想的:继续南行横穿公路吧?虽然不至于和敌人碰面交汇,但会在路南侧不足百米的地方给敌人一个背影。如果敌人发现起疑,吆喝站住,这就要硬干,对我们十分不利;如果扭身再返回玉米地吧,敌人也会生疑——这两个人见到 “皇军”,为啥又突然折返?如纵马追来,后果也很是不利。比较起来,还是大大方方上公路,堂堂正正进据点,以迷惑敌人,才有可能化险为夷。至于据点里面嘛,碉堡在村东头,街巷房舍都可以利用,人民群众更是我们的铜墙铁壁。
于是,我俩仍旧照常向南走,约五十来米,缓缓地上了公路,然后折转向东。这样就形成了如下态势:我俩在前,敌队在后,间隔约一百五十多米,都向着大五女据点行进。当时我一边走着,一边叮咛着自己:“要沉着”,“脚步要保持正常”,可实际上,不仅两腿交替得快,而且步度也迈得大,总算万幸,距寨门口将近百米,虽然被敌人紧盯着身背而行进,终于平平稳稳地闯过了!我所耽心的事——敌人吆喝“站住”的事,并没有发生! 是的,被喊住这一险关是过去了,但,整个险情并未摆脱。情况刻不容缓,要继续为最后摆脱险境而努力!
一进寨子,小陈便一头扎进道南居民的大门里,正好,院里有盆泡着待洗的衣服,他蹲下就搓了起来。我想,不能两人都围着一个盆搓衣服,就又出了大门再朝东走。约二十多米,忽然在街南发现了一条窄胡同。啊!是条窄胡同呀;此时,此地对我来说,该是多么求之不得的去处呀!我一扭身就闪了进去。入了胡同可就不一样了,敌人直盯身背的顾虑就消除了,我几乎像竞走比赛那样一直向南驰去。 走了约五十米远,一个更理想的去处出现了——道东有户人家的大门敞着,我大踏步迈进院子,北房檐更立着梯子,便飞身登上了房顶,这时我掏出手枪,监视着敌方。
大街上隐隐约约传来了马蹄声、脚步声。
这是从东屋里走出了一位大嫂,她惊奇地望着我,想说什么,但又没开口。我在房上,便低声地向她说明:
“大嫂,我是八路,差点和鬼子走个碰面……现在鬼子正从街上过。”
大嫂会意地点点头,可仍站在那里未动。
过了约两三分钟,大街上完全沉静了,我就赶忙向大嫂打听寨墙有多高?怎么走离墙近?……每句问话,都得到她圆满地回答:
事不宜迟!
我下了房,向大嫂道了谢,便按照所询问的路线,顺利地从豁口出了寨墙,安全通过了开阔地,又重新沿着大车道走进了多么向往的绿色海洋——青纱帐!至此,我总算摆脱了危境,但小陈现在怎么样呢?我一边朝南走,一边向北探望。
又走了不到十分钟,眼看着小陈气喘吁吁地赶上来了。他人还没有到,而“哈……哈……哈”的大笑声和“好玄哪”的惊叹声,却早已传到了。我迎住他忙问:
“怎么样?敌人有多少,你都看清楚了吧?”
小陈是那样的兴奋!沿着这一话题,就滔滔不绝地说开了。敌人是怎样从大门口通过的,并没有怀疑他,什么日军有多少,伪军有多少,马儿有几匹,过了多长时间。说得又具体,又流利,因为他是个老侦察员呀!
这一话题尚未落点,我又问到:
“小陈,你现在知道了浇园的那小伙子,为啥见了咱俩咋那么惊恐吗?”
小陈张口答到:
“知道,他准是把咱俩当成假装八路的汉奸特务啦!”
我俩的判断是一致的。这个小伙子很可能吃过“假八路”、特务的亏,……以至于表现出对我俩如此的疑惧和惊恐
边走边说,不觉来到了联络站,也很快回到了团机关。见了梁政委。除汇报了有关过路的各项准备情况外,着重地叙述了在大五女村的遇险经过。梁政委一边听一边微笑,听完后除肯定了当时的处置是恰当的外,更说了一句:“记住啊,任何时候都不能麻痹大意啊!”
这桩事虽然已过去了四十多年了,虽然当时的抉择是恰当的。是利用“出敌不意”的法子化险为夷的。但是,这比“西城弄险”还危险,事过之后,仍不免心有余悸。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里的主要教训就是:在任何有利的情况下,都不能麻痹大意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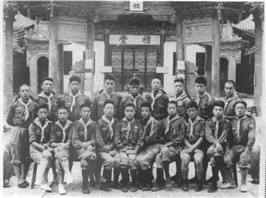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