葱花饼
记忆中的葱花饼
2025年12月10日 11:19
在小说阅读器中沉浸阅读
那葱花饼的香气,是先从记忆里漫出来的。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表哥家做客,午后三四点钟的光景,日头偏西了,把暖烘烘的光懒懒地照进厨房。表嫂系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站在面案前。一只粗陶盆,半瓢温水,几碗雪白的面粉。表嫂并不用量器,全凭着手感,那水与面的交融,像一场静默的仪式。面和好了,团成一个光润、温顺的球,再覆上一块微湿的笼布,让它“醒”着,表嫂说,面也得打个盹儿,醒透了,性子才柔韧,才听话。
醒面的工夫,表嫂从院角掐了一把小葱,青是青,白是白,水灵灵的。刀起刀落,细密的“沙沙”声,像春蚕在食桑叶。转眼间,案板上便堆起莹润翡翠的葱末。这还不够,总还得有一小撮粗盐粒,在石臼里慢慢捣成细粉;或许再舀一勺自家腌的、黄亮亮的猪油。这猪油是关键,冷却时是凝脂,一遇热,便化作勾魂的泉,能将面粉与葱花浸润、交融得天衣无缝。
面醒好了。表嫂将它移到案上,并不狠揉,只轻轻推展,擀成一片浑圆而薄匀的月亮。盐末匀匀地撒上去,猪油薄薄地抹一层,再抓起那把翡翠,天女散花般撒个满怀。这时,她那双布满老茧与皱纹的手,便显出了神通。从饼的圆心向外轻轻划一刀,然后捏着那“切口”,手腕带着一种圆融的韵律,开始一圈圈地卷。面皮便听话地层层叠叠起来,将青白与油香,严严实实地包裹进千层万层的秘密里。最后收口,按扁,再轻轻擀开。饼的形状或许不很圆,边缘带着些憨厚的起伏,那便是“手作”的印记了。
铁锅早已坐在灶上,烧得匀热。锅底只用肥肉膘极快地擦过一遭,滋啦一声,腾起一缕几乎看不见的烟。饼胚子“啪”地贴下去,与热铁接触的瞬间,一股难以形容的、混合着麦香与焦香的雾气便蓬然而起。表嫂微微弯着腰,目光沉静地注视着饼面,看着它从纯白渐渐染上淡淡的金,又生出些动人的焦黄斑点,像秋日的落叶。这时才用锅铲将饼挑起,手腕一翻,那饼在空中划个半弧,另一面便又贴上了热锅。翻动的间隙,她用锅铲的背面,在饼上轻轻按压、转动,那饼便听话地变得更薄、更匀,层次也更分明了。葱花受了热,那霸道的、鲜活的香气再也藏不住,混着炙烤的面香,穿堂过室,能把在院外玩耍的孩童,生生地“勾”回屋里来。
第一张饼总是烫手的。顾不得了,急急地撕下一角。热气“呼”地扑面,带着灼人的诚意。咬下去,先是脆,外层是恰到好处的焦酥,簌簌地落些碎屑;紧接着是软,内里层层叠叠的面皮,因了油与蒸汽的作用,变得绵软而富有弹性;最后,才是那画龙点睛的咸与鲜——葱花的滋味,在这一刻全然释放,不是葱的冲辣,而是一种被热力驯服后的、醇厚的清甜与辛香,熨帖地融在每一丝面絮里。表嫂总是笑着,看着我们狼吞虎咽,自己却不动,只说:“慢些,锅里还有。”
如今,城里也多见葱花饼。电饼铛烙的,规规矩矩,圆如满月,金黄整齐。买来一张,吃着,酥脆是酥脆,香味也浓郁,可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少了那柴火灶间腾起的、带着人间烟火的雾气?少了那铁锅边缘些许不均匀的、带着热力的焦痕?还是少了那等待时,从胃到心都被吊着的那份殷切的期盼?
那饼里,有自家院里的泥土味,有井水的清冽,有猪油历经时日凝成的醇厚,更有一种对于粮食、对于寻常日子近乎虔诚的耐心。民间美食的魂魄,从来不在珍稀的食材与繁复的技法,而在于这“民”与“间”——在于百姓的手,在于家屋的灶间,在于那将最朴素的材料,化作温暖生命力量的、代代相传的生存智慧与脉脉温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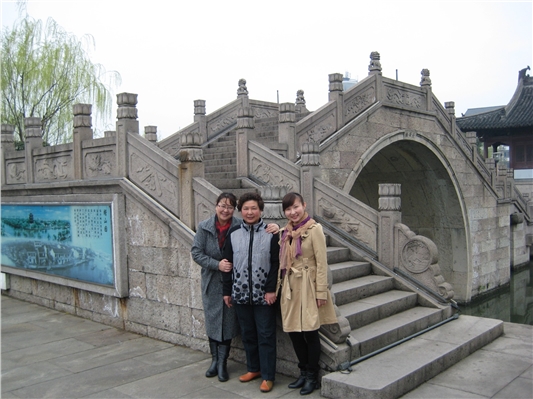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