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湘西“竿军”陈渠珍
“竿军”的形成
不断的移民,不断的战争,逐步形成了近代的苗汉分界线,几百年来不断的苗汉冲突和战争使这里常年拥有一支军队。屯丁分田到户,且耕且守,战丁专事操练,由屯田佃租中拨粮关饷,数以万计的凤凰人就这样被屯田的绳索牵在封建朝廷和旧中国的战车上,以致使当兵吃粮成了世代传统。因此地名镇竿,故称这支军队为“竿军”。乾嘉年间苗民起义后,清政府在已损毁的南方长城沿线修建汛堡、屯卡、碉楼、炮台、关门一千几百座,其中凤凰境内修筑了八百余座,征得屯田六万亩,养屯丁四千,战丁一千,苗兵二千,共计七千人之多,加上朝廷绿营总镇约四千人的兵额,当时凤凰十万左右的人口,就有一万人常年兵役在身,这个比例恐怕在其他地方都难以出现。当凤凰古城还处在边防要塞位置的时候,军旅的粗犷气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湘西人。孩子们从小就习惯了看兵营里的士兵舞枪弄棒,喜欢看大人猎取野猪或豹子宰杀了来分肉,喜欢看杀人割下耳朵挂在墙上,还喜欢看宗族家长把不守妇道的年轻媳妇绑来沉潭,甚至还会看到活剥人皮!他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凤凰人尚武成习就毫不奇怪了。竿军在鸦片战争、辛亥革命、护国护法、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中都有激动人心的表演。大大小小的战争在凤凰这座小山城里,制造了许多的军人世家,制造了凤凰人特殊的地方荣誉感。
古城文脉
抗战期间,1937年11月以凤凰籍官兵为主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128师,赴浙江嘉善狙击侵华日军第六、第八两个师团,及以后的南昌会战、宜昌反攻、荆沙争夺、长沙会战以及洞庭湖南岸的据点争夺等一系列抗日战役中,每一硬仗苦战都有竿军参加。抗战前夕的凤凰,大约不到一万户人家,却拥有三千左右连排下级军官,以及五个师的兵力储备。经过八年殊死征战,到了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的1945年,凤凰二十五岁以下的男丁死伤数目惊人,至少有三千位少妇守了寡,上万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老无所依…… 湘西“竿军”绝不仅仅是只是挥舞着铁血大旗冲锋陷阵的猛夫,他们骨子里涌动着的古城文脉让他们高人一筹。 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清光绪元年(1875年)短短的36年间,就从“竿军”里选拔出20位提督,其中7个成为朝延重臣封疆大吏,21个总兵,43个副将,31个参将,73个游击等三品以上军官。民国时期,“竿军”又诞生了7个中将,17个少将,230个旅团以上军官。而它的最后一位“舵爷”龙云飞自杀,已经是一九五零年的春天了。新中国的军队中,从“竿军”、湘西籍人成长为将军、干部的大有人在,贵为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的朱早观将军,位居中国武装警察部队政委的李振军将军就是杰出代表…… 竿军的第一任大佬田兴恕,道光十六年出生于麻冲乡的一个苗族家庭。16岁参加了竿军,作战勇猛。22岁时当上副将、总兵。24岁任贵州提督,诏赐钦差大臣。25岁兼任贵州巡抚。军权民政集于一身。1861年,因不满传教士在贵州的非法活动,先后将天主教传教士文乃尔及教民四人凌迟处死。在法国大使馆的压力下,1865年,田兴恕被革职发配新疆,“永不赦免”。到了兰州,所幸被陕甘总督左宗棠接收。左宗棠起用田兴恕带兵征剿,屡获全胜。左宗棠奏请光绪帝,请求将田兴恕释放回原籍。1873年,田兴恕回到故乡凤凰,田兴恕的故居门口悬着对联:人杰地灵文经武纬,物华天宝提督军门。四年后,年仅四十一岁的田兴恕英年早逝。四十年后,田兴恕的第三子田应诏因在辛亥革命担任光复南京的敢死队长、护国将军的英勇表现,又成为国民党中将,湘西镇守使。但是他很快厌倦了这种生活,1920年将统领湘西军政大权让给时年38岁的陈渠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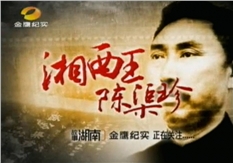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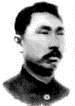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