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教不言,无为而治
大教不言,无为而治
——从教师角度解读贾老师
从师弟周刚告诉我老师猝然离世的那一刻起,与老师之间的点点滴滴就总是萦绕在脑海中,甚至到了彻夜不眠的地步。那些具象的细节,都令我泪流不止。当悲痛逐渐平复,一个核心的问题呈现出来:他对我们每一个悲伤的孩子具有哪些非凡的意义,使得他的去世令那么多人如此深刻的悲伤?也许,从“导师”一词中可以觅得最佳答案:多数人的导师只是起到专业方面的指导作用,而贾老师这样的导师,则是既指导学生专业知识,也指导学生本专业相关的上下游知识、技术与能力,最核心的是他指导学生的心灵。
我和贾老师之间有一个不太舒心的开始。我家境不太好。大概是1999年五月份,班主任岳喜庆老师在一次实验课后跟我说,你跟贾老师做论文吧,他可以资助你。因为盲目的骄傲和自卑,使我很抵触这种无来由的帮助。想来贾老师就只是要帮助我,但是从班主任那里,我却听出来施舍的意味。所以,我直到大三上学期期末才进到实验室里。彼时,康志远和李福鑫已经跟贾老师做了多半年的实验了。因为是这样的开始,我在实验室学技术的心气也不高,所以后来也没有进到冷饮行业中去。这些并不妨碍我学习、领悟老师。
人生三大幸事之一,就是“遇名师”。我这个老师,大教不言,无为而治。老师几乎从不指导我们做试验,哪怕站在旁边看一看,也没有过。以至于毕业之后多年中我常怀疑自己是否上过大学、是否进过他的实验室。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习和思考的深入,逐渐体会到了老师将中国文化的最精髓“无为而治”用到我们身上是怎样的大智慧!
举个例子吧!大约是2000年的夏天,实验室已经从二舍后面搬到科技一条街上。有一天中午一点多,他说“咱们喝酒吧,茅台,你们袁琳师姐跟他爸要来的,53度,好像是1983年的,瓶口还是那种赛璐珞的呢。你们谁去买个鸡架凉拌菜什么的?”于是,尊贵的国酒茅台搭着咸菜就进了肚。
“什么味啊?”
李福鑫说是大酱味,我说是青霉素味。老师听了,只是笑笑。
现在想想,这个事情寓意颇深。老师是通过这个事情来向我们传达一些理念。首先是本质至上。人们赋予茅台如此尊贵的声誉,其实它不过是和老龙口一样是个助兴的东西,能助兴、能给大伙带来快乐的就是好酒。其次,做人要大气,要能共享,不要把什么都自己拿着。第三,尊重,对学生、弟子也给与同样的尊重,不能做居高临下的姿态。第四,作老大就要有老大的样子和作为。第五,用行为来尊重长辈。第六,己敬人,人才能敬己。第七,威信不是由身份中来。第八,人要懂得感恩。等等,等等。这是做人方面的,还有些专业方面的知识。比如酱香型白酒的典型风味就是“酱香” 也就是“大酱味”;只有53度的茅台才是国酒,别的都不是。
这就是老师的“无为而治,大教不言”,他寓大于小,育人于无形。
“无为而治”,正是我们实验室的运行机制。这算是我们实验室的最大特色吧:辈分以进门时间为标准,在学的大师兄们到外面做与行业相关的生意,带回试验用的各种原料小样;大一点的师弟根据客户要求在实验室里做配方试验;初进实验室的小弟,除了看师兄们做试验外还要给师兄们刷移液管、搬东西、做卫生。老师只是坐在椅子上看着我们做事情,偶尔会问问试验做得怎么样,有时候也招呼备饭。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下,从门外徘徊者到稍微摸到点门路,再到基本熟悉专业技术,最后通过市场练兵,从做人、技术、商务等多个方面把学生培养成材。
我从2001年7月开始当老师,因循老师的数路:也是称学生为“孩子”,称女孩为“姑娘”,到他们做论文期间,也是经常一起去饭馆吃饭,当然是我买单,学生毕业后回来看我的第一顿饭,也是我请客,之后都是他们请客;和学生们吃饭时,我一定是坐在上座的,酒桌上言传身教的教给他们一些社交礼仪。效果,就是“老师爱我我爱她”,也像恩师那样收到不少孩子的“供奉”。
老师对我对大的影响,当属在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的影响。人生的省悟有两个突越阶段,第一阶段是四五岁,童蒙初发;第二个阶段是二十岁前后,形成确定的人生观、价值观,灵魂建设完整并逐渐走向成熟,人生的走向基本确定。就是从老师那里开始,我懵懂少年混沌初开,灵魂趋向于完整。事实上,就像他没有手把手教给我们如何做实验一样,他也没有用什么上升到教学手段高度上的具体方法,不过就是一起吃饭、一起玩乐、一起聊天这些日常琐碎。但是,可能你把他某一句话听进心里去了,并且按照他指示的去做了,多半你也就成了。老师说“最好的中国文化在先秦时期”,我工作后通读的第一本书是《庄子》,第二本是《诗经》,后来又读过《论语》、《道德经》等等,再后来又深入学习过一卷佛经。由此,我明白了很多中国人在哲学、美学、文学、社会学等多个方面的特点,成为一个拥有“三十岁的身体、五十岁的文化”的人,老师讲的那种的“中国人”。
大概是做了老师比较有时间想一些形而上的问题。2002年3月我初上讲台时我布置给学生们一道思考题:大学会给你什么?事实上我当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那时的答案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老师交给的书本知识慢慢都老化、淡去,专业以外的教诲则会越来越清晰。现在的答案,还要加上一句:那些教诲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消弭,那不是消失,而是融合进你的日常生活中去了。比如,我用过的每一部手机的问候语都是“热爱生命,享受生活”,我每次给新生上课,开篇也必然是这八个字;和学生们在一起时,也是尽量不讲专业知识而是电影、新闻、商学和市场营销。我的孩子都是大专生,以他们的天资和努力,现在有几个孩子已经算是小有所成了。他们谢我,我都会跟他们说,“当年你们师爷爷也是这么教我的。”
写到这里,我的眼泪又出来了。周刚在QQ上劝我说,“只要老师在我们心里,他就没有走。热爱生命,享受生活,就是要把悲剧的人生当成喜剧来活。在自己领域中做到最好,就是对老师最好的祭奠,不然对不起自己身上的贾氏标签。”周刚是我熟悉的师兄弟中老师最喜欢的一个,也是和老师最像的一个。他的话,余深以为是。
我在实验室的时候,老师常常是隔一段时间就要消失两三天。这一次,他大概是去加拿大或者新西兰了,地方远,时间当然会长一点。不久,他还会同往常一样,弥勒佛似的坐在实验室最尊贵的位置,喝着女孩给泡的酽茶,实验空隙时和男孩子们一起抽个烟,天南海北的胡侃一下,备不住还会数落数落哪个没有把卫生做好的倒霉蛋。
多希望,事实就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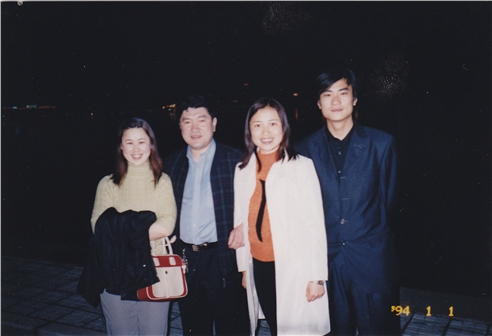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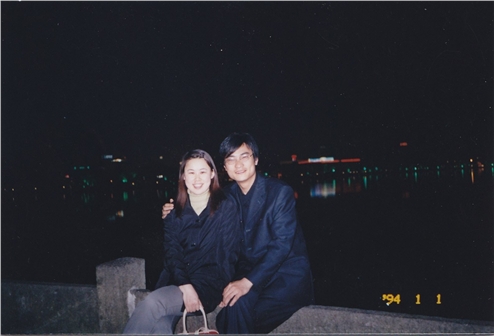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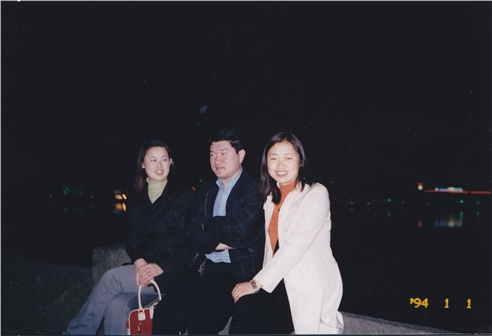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