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靳以
自参加新文学运动起,靳以将自己的一生精力全部投入了编辑与办刊工作。他曾参与编辑《文学季刊》、《水星》、《文季月刊》、《文丛》、《现代文艺》、《中国作家》等多个在文学史上掷地有声的刊物,并在办刊与教学的生涯里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小说、散文与报告文学。在靳以诞辰100周年、逝世50周年之际,上海市作协推出《百年靳以纪念集》。本版首发徐中玉、艾以两位老作家的纪念文章。
回忆靳以在沪江大学
徐中玉
靳以同志比我年长七岁,天津人。1932年就已复旦大学商学院国际贸易系毕业。我因家境清贫高中时期读的是无锡中学师范科,毕业后必须当两年公立小学的教师才许凭证报考国立大学,1934年考进了青岛的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我存心报读中文系,但实际对读中文系究该读些什么,以及怎样学法,根本不了解,不清楚。可在初到山大时,已在图书馆里看到靳以参加编出厚厚一大本的《文学季刊》了。他此后参加和主编的《水星》、《文季月刊》、《文丛》等刊物,以及他自己写出的不少作品不仅知道,也翻过,读了一些。因规定应读的以古典名家、古书为多,兴趣所在毕竟有别了。那时之前我连北平与上海两地都尚未去过,对靳以自然只推想成是一位很能干的新作家了。
沪江大学是所教会大学,在我进入的时候,管理权早已由中国收回,教会色彩已非常淡薄。中文系的一位资深“助教”丁景唐就是共产党员。后来才知全校早已有了“党组织”。上海解放时全校没有受到任何损失。进步教师事前自发组成一个“革新会”,配合具体工作,协助华东教育部领导即来校正式接受,我们的说法是沪江“新生”。
果然,这个大家盼望已久的“接收”、“新生”负责人靳以同志等都来了,明确被华东教育部请来当教务长和中文系教授,同时担任沪江大学工会主席。大学教授也被认为“工人”,有自己的工会,是对大学同人的一大喜讯,即承认脑力劳动者也是工人阶级了。“工人阶级”当时对学校中人乃是求之不得,极为高兴的事情。记得“教育工会”后来曾被取消过,又曾恢复过,现在则大概早已统一称呼了罢。
我和靳以同志实际就是他来沪江成为同事才相识,直接感受到了他的热情、诚恳、正直等种种性格优点。靳以来沪江后不久开始了一段时期的“思想改造”,中文系小组即在他所住的一个较大的客厅里举行。领导怎样计划和要求的,大家不清楚,我只是在北京报纸上先已读到了一些老前辈的表态或检查性文章。我们这个小组参加的除系里六个教授一个助教与两个学生代表,及一位新来的干部外,并无别人。靳以是组长,教授即朱东润、余上沅、施蛰存、朱维之和我。沪江全校有文、理、商、教育、社会、音乐等十多个系,所有包括文学写作“大学语文”课程全是我们分担的,互相理解尽力担任,一向非常融洽。各人经历自然不同,却都历史清楚。讨论中,各自介绍过去经历,教过哪些课,做过哪些研究,到过哪些学校。在各自所专的方面,究应如何批判旧思想,对封建时代包括国外资本主义、各种学派、学说究应如何批判分析,多表示教学、了解、弄清楚还很不够,应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学说。
现在想来,当时大家这些类似的心情都真愿望改进,如何改才对,哪些传统才算必须接受的、批判的、或彻底否定的,却很难有把握。两个多月中,每周举行两三次。更相熟后,各说各的,互相探讨,很有益处。主要因为我们先后都出生大学,从小到大,一直在教育界中工作及各种关系简单,清楚。沪江的其他各组,如政治系、社会系等,就不一样。我们小组有这样的结果,同靳以作为组长是非常重要的。因他热情、和气、诚恳,常常讲自己的疏忽、不足处。他从来没有什么架子,见解总是向前看,向积极有效方面引导。所以大家心情愉快,从来不曾感觉到有什么恐惧或忧虑。
这个学习基本结束后,我们即陆续服从分配,靳以根据上级要求,先去上海作家协会与巴金共同负责会务。事实上却是马不停蹄,随着抗美援朝的大军,跨过鸭绿江大桥,到前线慰问去了。当年一起开会学习的六个同事,分手后就从未再一道会面过。各自在另外的运动中都经历经不少磨难,但后来毕竟都仍在各自岗位上彻底平反后,重新得以尽力辅做了不少工作。最可惜的是靳以同志却在又做了许多重要工作后,积劳成疾,心脏病突然发作,竟于1959年11月7日50岁时离开我们,最早逝去了。靳以在沪江工作这段时期可能文学界朋友们所知极少。当年我们同事六人现只有我一人尚健在,但也95岁了,理应把这段情况写出来留个纪念。在过去的六十年中,我们这些人无一不经受过许多风浪,无奇不有,真假长期难辨。可以告慰50岁就不幸逝去的靳以同志的是,公道毕竟尚有,巴老典型也常在。朋友们都仍牢记着你,安息吧。
和靳以同志朝夕相处的日子
艾以
1950年上海市第一届文代会后,成立了上海市文联,夏衍同志当选为上海市文联主席。紧接着由冯雪峰、巴金、唐弢、靳以、陈白尘、许杰等组成的编委会,决定出版一份文艺刊物,定名为《文艺新地》,由陈毅市长题写了刊名。我于1951年由唐弢先生介绍来到市文联,被安排在《文艺新地》任编辑。在雪峰同志奉命上调北京后,《文艺新地》改由巴金、唐弢任主编。编辑部设在巨鹿路675号三楼的一间小房间内,四张写字台,由唐弢、李金波、陈家骅和我坐班使用。就在这时候,我有幸和靳以同志走到了一起,在他的领导下工作。
由茅盾、巴人、葛琴、孟超、蒋牧良、周而复、以群、楼适夷任编委的《小说》月刊于1948年7月7日在香港创刊,尊重茅盾的意见,刊物不设主编,由楼适夷负责全部编辑工作。《小说》在香港仅出版了两卷,后因国内形势遽变,《小说》月刊匆匆迁来上海,并赶在新中国成立那天在上海出版了第三卷第一期。
追根溯源,当年在香港创办《小说》,提议者是周而复,他当时是香港中共华南分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是他设想要在香港办一份文艺刊物。他的这一创议,得到了叶以群、楼适夷等的支持。但是,《小说》月刊迁来上海后,原来在香港时期主持编务的各位同志因此各奔东西,而此时的周而复,被任命为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和上海市委统战部第一副部长,他已无暇顾及《小说》的编务了,其主要编辑任务就落到了靳以同志肩上。虽然,“在那号称所谓‘民主之窗’的英帝国主义殖民地内,要出版一种严肃的文艺刊物,是非常艰难的。别的不说,首先,那一笔3000港币的登记费就不容易筹措。”(《小说》月刊第三卷第一期《编后记》)但是,当时由于上海刚刚解放,千头万绪。《小说》月刊迁来上海后也碰到诸多困难。而当时靳以同志是沪江大学教务长和工会主席,同时还是平明出版社的特约编辑。当时,《文艺新地》和《小说》月刊两个编辑部除去唐弢和靳以两位主编外,只有李金波、陈家骅和我三位编辑捆在一起应付两个刊物,当时的困难处境可想而知。
《小说》月刊迁沪后,摆在靳以同志面前的还有一个难题时时困扰着他,那就是小说月刊社的挂靠问题一时难以落实。因此,《小说》月刊迁沪后很长时间无家可归,几次易址。直到1950年年底出版第4卷第5期时,小说月刊社总算有了归属,成为中华文学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会刊,社址也随之迁到协会所在地武进路309弄12号。此时此刻,靳以同志总算松了一口气。
但是,到了1952年1月,为了“响应全国文联的号召,遵从华东文联筹委会的领导,也在主持编辑的几位同志交换过意见”,《小说》月刊出满第6卷后决定停刊。《小说》月刊迁沪后共出版了四卷,从《小说》月刊迁沪后的办刊经历,我深切地感受到靳以同志对文学事业的忠诚,对创办刊物的执着。虽然困难重重,但他始终乐此不疲。
1953年年初,靳以同志到华东文联上班。同年11月6日上午,华东作家协会成立大会开幕。大会通过了三天的议程,选举了夏衍、巴金、于伶、靳以等46人为理事,夏衍为华东作家协会主席,巴金、于伶、周而复、许杰、靳以为副主席。至此,靳以辞去了大学教职,作为常驻副主席坐镇在巨鹿路675号。当时,我在《文艺月报》任编辑,从那时开始,我和靳以同志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几乎朝夕相处,天天见面。
由于我在《文艺月报》担任理论编辑,平时就免不了和一些相识和不相识的文艺理论家们有所交往,有时或奉命或自己主动向他们约稿,其中就有胡风、王元化、贾植芳、耿庸、张禹、施昌东、张中晓等。想不到1955年反胡风运动突然平地起风波,我就因此于6月被捕入狱。在铁窗内羁押了一年又一个半月后,实在找不到我和胡风集团有什么牵连和纠葛,结果被“教育释放”,重回《文艺月报》。1957年乍暖还寒时,一场反右斗争又席卷全国。我当时刚刚从拘留所释放出来,惊魂未定,哪敢大鸣大放,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是,在一言未发的情况下,还是被划为极右分子,轮番批判。到了翌年4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正在编辑部伏案写检查,突然接到作协总机转来的电话,叫我马上到主席办公室去,我急忙放下手中的笔,快步走去,推门后一眼就看到靳以正在和陈家骅谈话,孔罗荪则坐在办公室另一张办公桌看文件。大概只有一两分钟,靳以和陈家骅的谈话就结束了,随即陈家骅由一位陌生男子护送走出办公室。这时,只听孔罗荪对靳以说:“傅艾以来了,你和他谈谈。”靳以有点不耐烦的样子说:“傅艾以还是由你和他谈。”说罢,转身走出办公室。罗荪就叫我在他的办公桌前坐下。沉默片刻,罗荪严肃而郑重地向我宣布上级的决定,告诉我已被定为极右分子,决定处以劳动教养的处分。听到这声宣布,我顿时就懵了,只感到天在转,地在沉,不知身在何处。看到我那惊恐异常的样子,罗荪向我解释道,根据中央政策,右派分子虽然是敌我矛盾,但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劳动教养是最高行政处分,以教育为主,最多6个月,以后仍可回单位工作。谈话匆匆结束。
被遣送到皖南白茅岭改造农场之后,我的脑子里日夜记住罗荪同志的话。很快6个月过去了,不但丝毫没有解除劳动教养,回单位工作的迹象,反而遇到了1959年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改造农场的生活更为困苦,真是度日如年。1959年正是新中国诞生十周年,国庆十周年在全民欢腾中度过,11月的某一天,却从上海传来了靳以同志因患心脏病突发去世的噩耗。悲痛之余,我一次次想起一年前在作协办公室和靳以同志的最后诀别。那场合,那情景,真是刻骨铭心,一言难尽,终生不忘……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世纪末,我和友人相约主编过一套“中国著名作家记传”丛书,其中就包括靳以、许杰、陈白尘、孙大雨、耿庸几位在生前都是我所尊重的、过从甚密的良师益友,他们的为人为文深深地影响着我,使我终生受益。
选稿:芦村 来源:文学报 作者:徐中玉;艾以
2009年10月2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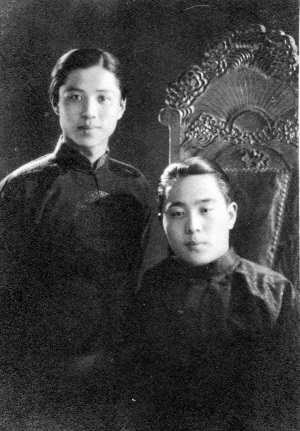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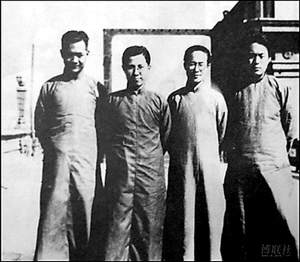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