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新闻观念的开放程度上的差异
弥尔顿要求撤销废除《出版管制法》等一系列压制英国民众宗教信仰、政治思想和言论出版自由的一切法律法规,废除出版许可制,使人们能自由地发表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和意见,让真理在公开而自由的竞争中战胜谬误。弥尔顿所希望的自由、所要求的自由是最大限度的自由,是几乎完全的自由,在备案登记的情况下,只是反对象“旧戏剧集”一样的指名道姓的诽谤。他希望“让我有自由来认识、抒发己见,并根据良心做自由的讨论”[11],并认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12],《出版管制法》“虽然主要想禁止诽谤性的和煽动性的书籍,但达不到目的”[13],压制他人就是压制自己。弥尔顿要求几乎完全的自由,一方面源于他对古希腊雅典人道主义传统的向往,对资本主义自由精神追求,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一方面源于他所看到的禁言所带来的恶性结果和解除言禁后的繁荣景象;还有一方面则源于他对真理的正确认识:“虽然各种学说流派可以随便在大地上传播,然而真理却已经亲自上阵;我们如果怀疑她的力量而实行许可制和查禁制,那就是伤害了她。让她和虚伪交手吧。谁又看见过真理在放胆地交手时吃过败仗呢?她的驳斥就是最好的和最可靠的压制。”[14]
与弥尔顿相反的是,梁启超更希望有限制的自由,他不希望言论出版自由太开放,只要进一小步即可。他先是指出报馆有“无补时艰,徒伤风化”[15]、“荧惑听闻,贻误大局”[16]、“毁誉凭其恩怨”[17]、“义无足取,言之无文”[18]、“歌诗不类”[19](《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等五种弊病以自贬,期望通过降低身份来获取清政府对报馆的支持,实际上则向清廷暗示自己的报业活动会限制在封建专制制度允许的范围之内,而且还有为清政府实行言论控制献策之嫌。梁启超认为“人各有权,权各有限也。权限云者,所以限人不使滥用其自由也。”[20]他倡导用法律来确保自由的范围,用道德来确保自由的理性。但其道德仍具有封建专制主义性质,其法律也是在保皇立宪下的对言论稍有放松的法律,因而才会向袁世凯建议行开明专制之治,“只有制裁之自由,则自由而不乱暴”[21],“窃计治今日之中国,其当操干涉主意者十之七,当操放任主义者十之三”[22]。
对于享有新闻自由的人,两者都将其局限在知识分子与道德模范的双重精英身上,梁启超更是以报馆作为精英的依托,精英必须借助报业才得发言的认识,愈加缩小了权利主体的范围与使用权限。而自由为谁服务,弥尔顿主要希望能释放真理,梁启超则是希望为政治和国家指明出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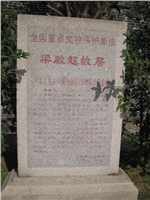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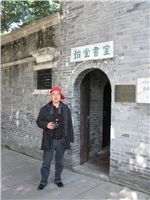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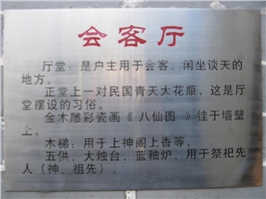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