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宋教仁的道路——宪政中国之道(二)
平心而论,清末立宪派对待革命党大体上还算有绅士风度,温文有礼,讲究分寸,只作理论商榷,不作谩骂攻讦。梁启超虽也有过对革命党咬牙切齿的时候,但他从骨子里就是一个温和敦厚者,对清政府如是,对革命党亦如是。梁先生认为,“天地甚大,前途甚宽,实有容两主义并行不悖之余地”,且两党“其事本非相反,其效乃真相成”,更应该“相扶掖为用,不相妨碍为界”。国内的立宪派更对革命党大表同情之意,经常声援、庇护、营救遭政府迫害的革命党人。
但是,革命党对待立宪派可就有些过分了,得理不让人,不得理亦不让人,往往意气用事,从造谣、谩骂,到挑衅、殴打,但为革命故,无所不敢为。一些革命党人以肢体冲突为能事,1907年在政闻社(梁启超发起的宪政组织)成立大会上冲击会场、大打出手,1910年将立宪派人士白坚打到头破血流。更怪者,干出这类丑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民国初年回到国内之后,仍上演过捣毁立宪派报社《国民公报》、在国会里打架骂人等闹剧(不过,得补充一句:在国会里打架骂人固然不美,却总比数百万人在辽沈、淮海大打内战,比“镇压反革命”、“反右派”、“文化大革命”要文明千百倍)。1910年,由立宪派发动且举国支持的国会请愿运动被清政府拒绝,海外一些革命党人竟然幸灾乐祸、摆酒庆贺,一副“凡是立宪派支持的,革命党都反对”的架势。难道不是有些过分吗?
但宋教仁不同,他是另一种类型的革命党。按梁启超的说法,革命党可分为激烈与非激烈两类。激烈者“纯属感情用事”,“只宜于破坏,不宜于建设”,“终不能结为有秩序之政党”,对其“不可阿顺之”;非激烈者为“旧革命党中之有政治思想者”,革命后可导入民主宪政轨道,造成“健全之大党”,“使为公正之党争”。宋教仁当然属于后者。
在革命群英谱中,宋教仁是聪明好学、才华横溢的一位。文才、学识、思想、政见,都是第一流的。客观地说,宋氏才识超出孙、黄多多,不可同日而语。宋在政治法律、边疆史地、财政管理以及宋明理学(尤其是阳明学)等方面均有深钻精研。恃才傲物、难于相处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瞧得起的人极少,老一辈的康梁、新一辈的陈独秀胡适都不曾放在眼里,却对宋教仁的才学赞许有加,更公开推宋为国务总理的不二人选(但章太炎的颂扬使年轻的宋教仁遭到党内外大人物们的嫉妒和忌讳。在中国政坛,举谁当总理大概是不可以公开讨论的,除非已经在密室里谈妥、十拿九稳,否则多半好心办出坏事)。章士钊、蔡元培、杨度、于右任、徐佛苏、林长民、蒋智由等才学之士与宋教仁政见各异,有的“先进”,有的“落后”,但均与宋惺惺相惜,过从往还十分密切。此中因缘或与革命无关,慕其长才实学,合其学问意趣,信其人品道德是也。
有证据表明,在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对宋教仁颇为欣赏。在当时的留日学生中,宋以文名见长,梁见宋发表在《民报》的文章后曾托徐佛苏致意,表示愿与相见。彼时梁正与革命党在《新民丛报》和《民报》上展开马拉松式大论战,梁亦转达宋教仁、章太炎息战调和之意。宋与章同意梁的调和倡议,但孙中山、胡汉民、黄兴不许,要与梁斗争到底。
到了民国初年,革命党中孙派人物仍全力排斥梁启超(如胡汉民对梁口诛笔伐,称梁对民国“犯罪”。孙的亲信中唯汪精卫曾向梁示好),但党中黄派、尤其是黄派中之宋派,则向梁表达敬慕之意。在国民党欢迎梁启超归国的大会上,胡瑛、孙毓筠称颂梁启超为“全国最崇拜之人”、“当代第一人物”。梁漱溟先生晚年回忆民初往事,说第一届国会竞选期间,宋教仁曾专程跑到天津拜访梁启超,以英美式两党轮替执政相勉励。“梁若执政则他愿在野相助;否则,他出来时请梁善意监督。这原亦是梁的梦想,对此自然感激而且契合。所以其后宋被刺身死,梁真是痛惜不已。”但此事似无其他的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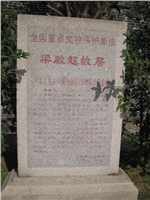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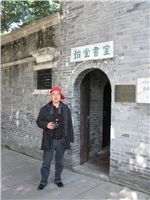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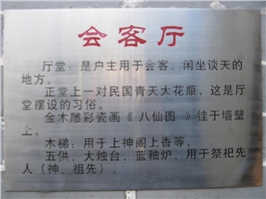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