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七师与门炳岳
骑七师与门炳岳
范辑五
骑七师沿革
骑七师成立时我就在这个部队担任中尉排长,后由排长到副官、副连长、连长、队长等职,历时十一年。现将我所知该师的情况分述于后。
国(民)党骑兵第七师是由三个独立骑兵旅组成的,即骑兵第一旅、第十一旅,第十三旅。第十一旅编为该师第十九团,第一旅编为该师第二十团,第十三旅编为该师第二十一团。我原在第十三旅,对第一旅和第十一旅以前的情况不太了解,仅就我所知的第二十一团的情况谈一下。
第二十一团的老底原是冯玉祥(西北军)的骑兵第四师。一九三〇年阎、冯倒蒋时,在河南豫东参加军阀混战。阎、冯失败后,这个师就在开封以东的东名县被改编为骑兵第一师,一九三三年改编为骑兵第十三旅。我是一九二六年参加这个部队的,那时是西北军第四师,参加后由列兵、下士、中士、上士,准尉司务长、少尉排长、中尉排长,直至骑兵第十三旅改编成骑兵第七师时仍任中尉排长。当时这三个旅分驻在河南归德(商邱),驻马店等地,改编后统一开驻河南陕县结集整训。当时三个旅的人数虽不足额,但缩编成三个团以及师司令部的几个直属部队,人马还是有余的。在旅改团时都是挑选的强兵、壮马。到陕县结集时,又统一了原有口径不一的轻重武器,全部换成七九口径,步qiang为捷克式和中正式的步马qiang,轻机qiang以捷克式为最多,重机qiang以马克沁为主,迫击炮以八二为主。另外还配有qiang榴弹、掷弹筒等轻便武器。编成后全师官兵约有六千余名,乘马七千余匹。
门炳岳的身世和生活习性
门炳岳原籍河北省河间县,据说其家是当地富豪。本人自幼上学,天资聪颖。据他本人说,他从八岁开始念书直至高中毕业,年年总是考第一,高中毕业后又连续上了十三年的军事学校(究竟是哪些学校不详),同样每次考试也未落过前三名,最后在保定军官学校(不知第几期)毕业,考试时仍是第一名。由于他的成绩好,就留校当教官,后来直至当了军长(不知是哪一军)。由于门主张抗日,与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相抵触,不能见容于蒋,而由军长调国(民)党中央工作。由于门炳岳自恃学习成绩优良,官运亨通,在待人接物上不时表现出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久之影响他和同事之间的关系,逐渐脱离了群众。因而调职中央多年,一直没给他带兵的机会。与他前后期的同学都早已有权有势,有官有钱,唯独他一直坐着冷板凳。后来他参加了庐山训练团,换了换脑筋,攘外思想有些转变,恰好一九三五年改编骑兵第七师时,原来的三个旅长让谁当师长,其他两个旅长都有意见,经国(民)党中央再三斟酌决定另派师长,由于门在庐山的表现和白崇禧的保荐,门炳岳就这样当了骑兵第七师师长。多年的冷板凳使门懂得了手中无兵一切空的道理,因而门就将骑七师视为他立足的政治资本了。
他接师长不久,部队就开到西安附近归属张学良的骑兵军军长何柱国指挥。当时骑兵军所辖骑三、骑五、骑六三个师都是原东北军过来的,纪律不好,兵员不足,武器又差。门便从思想上看不起何柱国,更不愿与他所谓的土匪队伍为伍。记得有一次门硬是把军部发下的东北军统一着用的蓝色、布底、三角头军鞋给退了回去。他说我骑七师宁可打赤脚也不能穿东北军的军鞋,不然就良萎不分、好坏不清了。正由于他存在这样的思想,下边的团、连受他的影响经常与东北军闹纠纷。门对此也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九三六年春,骑七师驻防陕北耀县时,张学良的总部派一班宪兵驻耀县维持军风纪,门炳岳知道后认为这是对骑七师不放心,是看不起他门炳岳。于是便暗示师司令部特务连把这班宪兵打跑,打时自己不能吃亏,不能让他们抓住人,不能打死他们的人。结果这班宪兵到耀县不到一星期果然被打跑了。
两个部队经常闹纠纷的消息逐渐反映到上边,门炳岳也早就想脱离东北军,于是便给中央军事委员会打报告要求北上抗日。经批准后于一九三六年十月,由西安开往绥东的平地泉、丰镇、卓姿山沿京包铁路线一带驻防。
门炳岳作为一个旧军队的高级指挥官,和当时一般军阀、官僚相比,他在生活上一贯是比较朴素的,私生活也比较正派、严肃,他烟酒不沾,更不寻花问柳。他个性强,好胜心强,上进心更强,对工作认真负责,肯吃苦耐劳。在钱财上廉洁奉公。这些在当时腐败的国(民)党军政要人中是难能可贵的。
门炳岳对骑七师的整训
骑七师是在三个旅缩编成三个团的基础上组成的。所辖第十九团团长叫胡竞先(系原十一旅旅长),第二十团和二十一团团长都姓张。这三个团长的情况各有不同。十九团胡团长是中央军校(不知第几期)毕业生,又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有靠山、根子硬,素日练兵方法完全是学日本法西期那一套,对下级压制,打骂士兵,要求全团官兵对他绝对服从。记得有一次部队出操乘马行进在平凉的大街上,有一个士兵稍微偏离队列,团长上来就是一顿马鞭子。胡团长对门炳岳也不买账,而门对胡也感棘手,于是两人在思想上就产生了矛盾。
第二十团团长虽然根子不硬,但在二十团官兵中有一定的威信。他带兵的方法使用的是江湖上的那一套,嗜好多端,吃、喝嫖,du,抽大烟一应俱全,团内官兵磕头拜把子成风。平时训练要求不严,不过是摆摆架子应付差事而已,全团上下都是大哥二哥麻子哥。门炳岳对张团长的行为和全团的风纪很看不惯。
第二十一团团长无硬根子,团内威信也不高。其人既吸大烟又嗜du如命,但在战场上指挥骑兵却颇有经验。他对门炳岳是唯命是从。该团无论在平时,还是在战时,对全团官兵的纪律一向抓得较紧,因此军风纪较其它两个团都要好一些。
另外还有刘凤岐副师长(原系十三旅旅长),此人是行伍出身,文化水平低,但他在战场上的作战经验却很丰富。他和门炳岳的关系开始时还不坏,由于门炳岳不时流露出看不起刘的意思,天长日久二人在思想上就有了隔阂。
门炳岳为了进一步整顿骑七师的纪律,先后将三个团长、一个副师长撤换了。十九团由朱钜林任团长;二十团由吕纪化任团
长,二十一团由胡逢泰任团长,后来在刘副师长离职后,又提朱钜林为副师长,另派刘旭东为十九团团长。
经过人事调整,门炳岳身体力行深入下层,抓紧整训。他亲自给下级军官讲骑兵战术课程,白(天)工作一天,夜间还下连队抽查岗哨。有一次部队驻在陕北耀县,我那时担任骑七师司令部装甲汽车排排长,耀县南门的城防由我排负责。一天夜间十二点左右,门炳岳带着两名卫士前来我排抽查。按规定给他配备有汽车、乘马,但他轻易不用。再如在西安参加会议时,他总是跟一个勤务兵徒步赴会。此外,他还经常到司令部直属连队的马号查看马匹的饲养状况,并随时向饲养员了解每日马干的定量与用量。当初门炳岳到骑七师上任时,只带勤务兵一名。这在当时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风气中,实属少见。后来虽曾有老部下、同乡来投奔他,也录用了一些,但都是从事一般工作。
该师经过人事调整和加强整训,全师的团结和风纪逐渐有所好转。就拿逃兵一项来说,我带的装甲兵汽车排共有官兵六十余人,过去每月总是逃亡现象不断,自从整训以后,这个排有一年的时间未发现逃兵。其他团、连也大有好转。
门炳岳及骑七师在抗日战争中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门炳岳的骑七师于十月间在商都与日本侵略军打了第一仗。开始是与伪蒙军的骑兵接火,当时士气高昂,官兵个个奋不顾身,冲锋陷阵,英勇杀敌。此役伪蒙骑兵师长几乎被擒,并将商都城打开。伪蒙骑兵败退后,随后上来了日军的正规军,双方激战了一天,由于我军孤军作战,如不转移将受重大损失。于是就边打边撤,沿京包线南侧经归绥、包头,北侧经大青山以北的陶林,武川、固阳,逐步向西撤退。特别是由包头沿前山大道往后套撤退时,沿途所见确为一幅国破家亡的流民图。一路同往西撤的部队有马占山的骑兵,石玉山的骑兵,安华亭的步兵旅,地方团队武驼皋以及绥,包地方行政人员及其家属,绥、包二市的商人和市民。沿途人流如潮,汽车、马车、乘马、骆驼、毛驴争先恐后,公路为塞;军民穿插,贫富混迹,扶老携幼,人喊马叫,哭天喊地;人马杂踏,不少人倒毙途中。此情此景令人惨不忍睹。
当时西撤各路队伍,除骑七师尚有军容队列以外,其他队伍都已溃不成军。而且一些杂牌队伍中的不肖之徒还趁火打劫,明刁暗抢,杀人越货。这些平日吃军粮、拿军饷的队伍在敌人面前一qiang不发便望风披靡,而对被迫背井离乡流浪逃难的百姓却凶残狠毒,无所不用其极。骑七师的官兵目睹此种情景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请求门炳岳下令停止西撤,就地阻击,以灭敌寇猖狂气焰,显中国军队威风,就百姓于水火。因此,当骑七师退到西山嘴时,门炳岳依据当地地形,下令停止后撤,在此阻击日寇。经过各部队长会议研究,下达如下命令:
1.二十一团守住卧羊台的一、二、三号碉堡;
2.十九团暂时停在退水渠下游红柳林中待命出击;
3.二十团和司令部的直属小部队过退水渠待命,通信连及各团的通信排即刻架设电话,各部队马上进入阵地。
不到半天功夫,敌人果然追上来了。先头部队是伪蒙古骑兵。当它接近二十一团第四连据守的第一号碉堡时,四连便以轻、重机qiang,步qiang猛烈射击,当场击毙敌军三人,其余的拨马而逃。时已天晚,再未发生大的战斗。次日敌人结集了一团之众,向三个碉堡猛扑,连续数次都被击退。随后敌人又增援了一个团(两个团总共不到一千人)准备联合进攻。这次敌人来势凶猛,激战两小时,敌散兵已接近了碉堡,向碉堡内投掷手留弹,有五次都在爆(炸)之前被中士班长张兴林掷还出去,将敌人炸死不少。正在双方激战之际,隐蔽在红柳林中的第十九团由敌左侧快速插到赵家油房一带,切断了敌后方补给线和援兵。十九团的出现,动摇了前边的敌人,就在这一刹那,二十一团乘隙出击,敌人只好全线撤退。敌在骑七师前后夹击之下,伤亡惨重,一口气由西山嘴后撤二百余里,到离包头只有百十里的三顶帐篷一带,由于包头援兵出来接应才停止后退。敌我双方就在此地相峙起来。这一役大灭了敌人的威风,大长了我军民的志气,为绥远抗日史写下了光辉的一笔。
门炳岳到五原后,就地qiang毙了卖国投敌的唐兆明和康三元。由此振奋了士气,安定了民心。正如民谣所说:"西山嘴有了一座门,不怕抵挡不住日本人。"
日寇进攻后套时是兵分数路齐头并进的。敌步兵以乘汽车为主,伪蒙古军以骑兵为主。当时骑七师二十团防守的阵地是在河西一带,最前线二圪旦南至高地脑包上,北至黄河,共约二公里。沿公路两侧及脑包高地上约五百公尺的一段是第二连的防守地。该连为了增强火力,将全连的轻机qiang大部集中在脑包附近的高地上。敌人先头部队有装甲车三辆,行进到二连阵地前约二百公尺处,立即遭到步qiang、机qiang的猛烈射击,敌不支退回原地。随后就以步兵炮兵集中火力向脑包高地轰击,但二连冒着敌人的炮火坚守阵地毫不动摇。以后敌人又以炮兵作掩护组织步兵向高地进攻,每次出动一个连,连攻三次均未得逞。最后敌以密集的炮火向我发射毒气弹,致使该连多人中毒。经过一昼夜的顽强固守,毙敌五百余名,我二连官兵大部中毒,连长负伤,连附阵亡,官兵共伤亡二十余人。次日拂晓前我二连才向后转移。
门炳岳进套后,为了维持地方治安,相继收容了石玉山、安华亭,邬四儿等杂牌队伍。当时在后套的游式军的警备旅和地方团队武驼皋、盟旗的保安司令部、乌拉特前旗的司令奇俊峰、乌拉特后旗的司令巴云英,都纷纷前来投奔门炳岳,并请其统一指挥。这些杂牌队伍所以要来投靠门炳岳,一是为了保自身的地位;二是看门炳岳的骑七师是人强马壮的中央正规军,势力雄厚;三是看门炳岳的作风比较正派。而门炳岳也有自己的打算:笼络住这些队伍的头子,再通过他们去约束各自的队伍,总比放任不管为害地方要好一些。抓住这些队伍,对于扩充自己的势力和影响有益。于是门炳岳向国(民)党中央请拨军费以维持这部分队伍,中央在批拨军费的同时,准将其收容的石玉山部编为骑四师,石玉山,任师长;安华亭部编为步兵第五旅,安华亭任旅长;门炳岳也因而被擢升为骑兵第六军军长。就在这种互相利用的情况下,总算把当时的混乱局势稳定下来了。而这也就触发了门炳岳想当绥远省主席的野心。门为了给自己登上省主席宝座打基础,还从当地吸收乔学曾委为安北县县长,吸收梁子才任其少校副官,拉拢临河县大地主李干臣(记不得委他当了什么司令),并且在五原成立了"政务处",实际上这个处就是省政府的雏型。由于骑七师进套以后在军风纪方面比其他队伍为好,受到可姓的好评,门炳岳在一片赞扬声中也自认为绥远省主席舍我其谁?
门炳岳与傅作义的矛盾
太原失守后,傅作义备受阎锡山排挤率部到绥西河套重振队伍继续抗日,蒋介石任命傅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仍兼绥远省主席。这样一来,门炳岳的绥远省主席也就好梦难成了。门炳岳对此心怀不满。
一九三七年冬黄河封冻后,骑七师派二十一团的三个骑兵连带一部电台进驻河西二圪旦湾以西地区。当时黄河西岸老乡因避战乱都已逃走,土地无人耕种,致使驻防河西队伍的马草、马料无法就地解决,必须由套内供应。为此骑七师就在河西吉星滩设一草料供应站,草料是从一百多里外用骆驼运来,途中还要渡过黄河,其困难情况可想而知,驻地官兵对这批草料非常珍惜。门炳岳专派我(当时是副官)带兵一个班严加守护。约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间,傅作义的部队由山西开进后套,路经七星滩时要用骑七师供应站的草料喂马。当时我以不经上级许可不敢擅自作主为由向傅部三十五军一位营长说明原委,而该营长坚持非喂不可,并动手抢喂了一部分。我无奈只好骑马回师请示报告。门炳岳听后火冒三丈,骂傅部简直是一群土匪!从此以后,门、傅矛盾日益加深。三十五军进套以后,驻在五原南牛犋附近一部分,与骑七师二十团驻地相距不远。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两部分打起群架来,后来整连的队伍都拉出来摆开阵势准备火并,幸被制止才未酿成流血事件。自此傅作义一到五原,门炳岳就到乡下去避而不见,而那些杂牌队伍的头头,一见傅作义到来,个个趋之若鹜,傅也有意识地拉拢这些人,于是这些人便逐渐地疏门而亲傅了。门炳岳对这些杂牌队伍早已不感兴趣,认为骑七师与这些军纪败坏,土匪成性的队伍为伍,有玷骑七师的声誉,现在他们投靠傅作义正是去了自己的一块心病。
门、傅矛盾上下皆知。尽管两人见面点头哈腰,实际上是勾心斗角,矛盾重重。那时门炳岳除非是参加机密的军事会议从不去长官部见傅作义。门炳岳当时所以敢于对傅作义如此大不敬,主要自恃是中央军,兵强马壮,战斗力强,有群众威信,傅作义离开骑七师就塌了半边天;而傅作义对门的作为和用心,心如明镜,但考虑到大敌当前,一时还不能离开骑七师,对门尽可能以迁就求和解,等待时机再说。那时骑七师虽归傅作义节制,但每月的经费,门宁可派队伍沿途护送由河套到宁夏去领,也不让长官部代领代发。由此一事即可见门、傅关系之一斑了。
一九三九年冬,傅作义以副司令长官的名义指挥绥西所有部队全力进攻包头,当时给骑七师的任务是:由河套出发经伊盟佯攻萨县,破坏萨县以东的铁路桥梁,以阻止归绥及二十四顷地两方面敌人向包头增援。骑七师奉命由河套出发经伊盟达拉特旗及新民堡,渡过冰桥后以一个团的兵力进攻萨县,一个团留在师部作预备队,同时监视二十四顷地方向的敌人。骑七师当夜完成破坏铁路桥梁的任务后,拂晓前同时将佯攻萨县的部队全部撤到萨县以南七民胡芦头一带:次日上午九时左右,二十四顷地的敌人果然出动,当即与二十团接触。激战一天,日落前全师队伍转移到那令沟一带渡过黄河,又从那令沟转移新民堡。此时由傅作义指挥的攻包部队受挫后撤,途中骑七师与傅的电台失掉联络,骑七师只好沿黄河南岸西撤。事后门、傅二人互相埋怨,各说其理,相持不下,最后将官司打到蒋介石那里,终于将门炳岳调职,由该师副师长朱钜林代理师长。
门炳岳行前对全师官兵讲话时说:此次攻打包头,根据长官部的部署,本师所承担的任务已经完成,是无可责难的。至于自己在包头受挫而委过于人,那是故意找我的毛病。我们两人(指门、傅)的问题在这里是解决不了的,必须到中央去打这场官司。我这次离开大家就不回来了,你们要在朱副师长的领导下,听从傅长官的指示……等等。门炳岳这番话实是暗示官兵继续与傅作对。后来门炳岳调任骑兵监,许多官兵都认为这是被傅排挤所致。傅听到这些议论之后,就带着攻打包头前后的一沓电报到骑七师驻地蛮会,召集连长以上的军官讲话,意思是想说明攻打包头失利究竟谁是谁非,以消除骑七师官兵的误解。与会的军官一听傅是算老帐来了,有的便离开会场不听了;有的在下边乱哄哄地议论纷纷。傅作义见此情势,知道继续开下去也不会有什么效果,便由朱钜林打个圆场陪同傅作义离开了会场。
朱钜林为人忠厚老实,接任师长后,对傅恭而敬之,唯命是从;傅作义向来城府很深,但对蛮会之事未加深究,而对朱钜林却倍加信任。如此一来,门炳岳任期内遗留下的与傅的矛盾,也就逐渐由淡薄而消除了。
骑七师的军风纪
骑七师自一九三七年冬进套以后,经过逐渐整顿,其纪律较之杂牌军是要好得多。特别是门炳岳治军甚严,平时不许扰民,战时更为注意军风纪。按当时的供给制度,行军中部队的人吃马喂,除自带一部分以备不时之需而外,一般都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然后按实际用量照价付款。并规定,如遇主人不在而动用粮草时,必须公平折款作价,将现款留在容易被主人发现的地方,并留下清单然后才能离去。然而具体到各个连队就不一定都能遵照执行了。常常是主人在就付钱,无人时也就白吃白喂了,省下的钱便归连队所有了。门炳岳为了堵塞这个漏洞,每逢行军作战过后,便组织一个军风纪检查团,沿行军路线进行调查,只要有老乡反映少了粮草未见留钱的,检查团取得当地证明,回来查明联队番号,除责令给老乡补送价款外,还要给连队长以处分。因此老乡编成歌谣赞颂骑七师:"一出门,往正东,从天掉下铁帽兵。铁帽军,甚讲理,公平买卖不刁东西。"(铁帽兵系指骑七师)当然,老乡对骑七师的赞扬是与那些土匪成性的杂牌军相比而言的,也是一个标准不高的评价。
从表面上看,骑七师的纪律确忱其他队伍好一些,但其内部也是乌七八糟的。他们当时所以能够维持一个好纪律的门面,最主要的是这个部队粮饷充足。来钱的门道多,因此扰民之事就少一些。
抗战期间驻河套的部队大都不能按时给官兵发饷,即使发也只发个半饷,叫做"国难饷";而骑七师每月都能发八成饷,比如那时一个少校每月可发八十元、上尉五十元、中尉四十元,一个列兵每月也能发八至十元。当时的生活费用每人每月吃三元的伙食,三天两头还能吃上肉;每匹马每月发马干费九元,当地的马料(莞豆)每石(三百斤)才三元,草价就更便宜了。此外,骑七师每个连队既有办公费,还有副杂费,官兵一切生活必需品以及马匹装具等等都是发给的。这样骑七师的官兵由于手头不太拮据,一般情况下为非作歹之事也就少了。
但骑七师官兵的来钱之道主要不是靠那有限的几个薪饷,而是靠走私做买卖。每逢冬季黄河封冻之后,骑七师就把人马放到河西一带去了,东至包头南大树湾,西至马七渡口,东西二百多华里的黄河沿线都是骑七师的防区。在这里有时也和从包头及中滩来的敌人打一打,十天二十天也不准碰上一回,其余的时间都是想方设法"捞外快"。骑七师防区对面的敌占区盛种大烟,黄河封冻之后来往行人多以倒换皮毛、大烟为主。这些人都得事先与河防部队联系好,从这边买上皮毛到中滩去换大烟。骑七师的官兵也趁此机会有的直接拿钱去买;有的拿钱买上皮毛和当地老乡各伙去换大烟;还有的专门护送走私商人吃护送费。这样一个冬季下来,骑七师到河西去的官兵都程度不同地搞回些大烟,多者千八百两岁一般的五六百两,最少的也得闹个十两八两。次年黄河解冻后,这些大烟就随大部队带回后套来了,渡口虽设有宪兵、警察稽查毒品,但对渡河的大部队,尤其是骑七师,明知挟带有大烟土,也不敢检查。这些大烟一到后套便获利几倍,官兵们便吃喝嫖du尽情挥霍。再就是这些人自恃有钱,利用后套百姓的穷困和烟毒流行,以及青壮年被拉夫抓兵的机会,以金钱、大烟为诱耳,通过认千亲、串门子等手段,到处"打伙计'',影响甚坏。
另外,这个部队里江湖习气很重,在"家理" (即青红帮)、磕头拜把子、换贴等等很是普遍。一经拜了把子,这一伙人就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吃吃喝喝不分彼此。到了战场上也能互相照顾,有的还真能做到生死与共,即在平时也能一人有难大家来帮。如果在这个部队没有几个磕头相好的,一旦遇事就吃亏。
这个部队的du风也很严重,打麻将、推牌九、掷骰子一应俱全,du注有大有小,人数可多可少,上场不分官兵,du本不分公私(有的连长一夜将全连薪饷全部输光)。那时可以说除门炳岳以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官兵都du。
更为奇特的是这个师相当一部分官兵笃信神佛,每日在家焚香跪拜。骑七师有一位张副师长,一九三七年率部驻防伊盟时,师司令部的谍报队长带着几名士兵给投机商人武装护送走私,中途与缉私队交火,打死缉私队一人。傅作义得悉此事后指示严究。师里只好将谍报长张云峰和另一名樊永富的扣押起来。报经傅作义批示,为首者qiang决,胁从者判刑,张副师长对谁主谁从拿不定主意,几经八大处长集体研究也无结果。于是张副师长便求助神明,焚香求拜佛爷托梦定生死。经过精于此道的一位军法官为之圆梦,结果将张云峰执行qiang决,樊永福判了徒刑,这简直是以人命为儿戏。
门炳岳和骑七师的结局
门炳岳由骑七师调骑兵监后,虽然离开了八战区,但和傅作义的芥蒂并没消除,遇机免不了要参傅一本。胡宗南也不甘心将骑七师拱手送给傅作义,于是便在中央鼓捣。正巧伊盟发生"三·二六"事变,朱钜林调离骑七师,胡宗南便利用机会派七分校骑兵科长张绍武接任骑七师师长,终于一九四四年将骑七师调离傅作义的势力范围。据说日本投降后骑七师调到山东投入内战,曹州一役被解放军击溃,伤亡惨重,后转移到许昌一带,终于全军
覆没。
至于门炳岳的结局也很惨。在他任骑兵监时,有一年夏天到庐山去参加军事会议,会场设在山上,他住在山下,每次开会都是一人徒步上下山。门炳岳一向严格遵守时间,有一天开会时间已过仍不见门炳岳到来,工作人员便打电话询问住地,对方说早已上山,与会人中也有人证明曾在路上遇见门一人徒步上山(其他人都是坐滑竿轿子)。散会后仍不见门,于是派人四处寻找。原来门炳岳身体肥胖,患有高血压,加之天气炎热,行至半路晕倒在地,当时路上没有行人及时发现和抢救,便倒毙在山路上。这时正好有两个讨吃的见门穿着不一般,身旁并有黑色公文包一个,以为里面有钱,便打开想发洋财,结果里面除文件外并无分文。两个讨吃的便将门的尸体拖至树林之内,将门的衣服剥得精光便逃之夭天。因此寻见门炳岳时只是一具赤身裸ti的僵尸。曾经在抗日战场上叱咤风云、立下战功的一员战将,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
(一九六二年九月于集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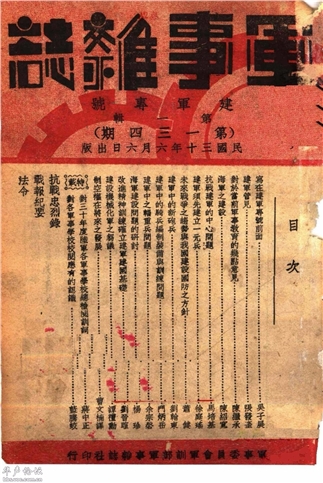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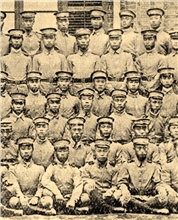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