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5-08-25 11:43:38
发布人:
天府霞影
风云日月八千里(5)
二十六、李相云这样教育小儿子
她家有个小闹钟,走走停停很不准时,出于好奇心,没经母亲允许,才十岁的小儿子把它拆卸开摆了一桌子。李相云见到后非常惋惜地问他:“为什么把钟拆了?一个还可以用的东西破坏了很可惜的”。而她没想到小儿子忽然脱口而出:“没有破坏,就没有发明”。母亲大吃一惊,看着年仅十岁的小儿子,继而笑了,摸摸他的脸说:“妈妈要你好好读书,以后成为发明家”。
有一次,为了买一本作业本,小儿子偷偷从商店装钱的抽屉里拿了五百元(相当人民币改制后的五分钱),晚上,李相云清账时发现少了五百元钱(当时,一天的营业额只有一两万元),她知道一定是我拿的,就自己坐在那里出神,而后就伤伤心心地抽泣起来。儿子吓得赶紧向妈妈承认错误。她止住哭泣,把儿子搂进她的怀里,痛苦地嘱咐他: “妈妈不是心痛这几个钱,妈妈是担心你学坏了,妈妈就没法活了”。从此儿子再没有私自拿过一分钱。母亲的话虽然很轻,却让儿子一辈子不能忘。
李相云节衣缩食勤劳俭朴一生,但对孩子从不扣,只要是有利孩子学习和健康成长的合理要求,她都尽可能满足。她的小儿子从读小学就喜欢踢皮球,进入中学后就更加酷爱,一九五三年的儿童节前,她花去了四元钱,给儿子买了一个儿童足球,而当时学校伙食费一个月大约才四元五角钱。有了足球让儿子的课余活动和假期生活更加丰富,使他成了街坊邻居孩子们的核心,也使他以后成为学校足球队的队员奠定了基础。
为了鼓励儿子热爱科学,李相云还给儿子五元钱,去成都的会府旧货市场,买了一个矿石收音机,让他对学习物理的兴趣更加浓厚。
由于儿子从小就喜爱下河游泳,在一次丢失衣裤等到天黑才敢光着屁股回家的教训之后,再每次下河游泳就不脱裤子跳下水,上岸拧干后再穿上回家,从城外回到家时,湿裤子就被穿干了。久而久之,儿子得了关节炎。整个中学时期,每到秋末冬初,下肢关节肿痛,蹲不下去,蹲下去后又站不起来,连晚上了睡觉翻身都很困难。但李相云从不娇惯儿子,鼓励他勇敢战胜病痛,不请病假,坚持学习,坚持体育锻炼。支持儿子参加体育比赛,从不阻拦,不拖后腿,让儿子学会坚强。她带儿子去看医生,一瓶接一瓶地买回鱼肝油叫儿子服用。又四处寻找偏方,把黑豆、黑芝、糯米等炒熟,磨成面,将熬好的牛骨髓油和在一起,制成甜食店里三合泥一样的食品,让儿子每天吃一小碗。又嘱咐儿子多晒太阳。从初中直到高中毕业,一直如此,终于让关节炎远离儿子而去。
二十七、李相云累得病倒了
住在李相云家的那位先生去参加土改工作队,完成任务后己返回家,他热心群众工作,被选为居委会主任。虽然他在李相云家住,并参股为商店的股东,与李相云都在商店拿工资,但是,许多时候他是在办理街道群众的事。李相云要养活她的儿子和女儿,供她们读书,很想把生意做大,于是更加拼命地劳作。很快她就累倒了,被诊断为伤寒病。没有钱去住院,只能躺在家的床上听天由命。这时女儿己考上大学去东北读书,小儿子己是成都县中学的初中学生。小儿子从进初中起就住校,每星期六回家一次。李相云怕耽误儿子的功课,不让他请假在家照料她。在她生病期间,商店无人经管只得停业关门。儿子向学校请求改为走读生,他每天把母亲锁在家里去上学,放学回家给母亲热饭、送水。基督教会的教友是一家私人医院的护士,自学掌握了一些医疗知识,出于仁慈和友谊,她一天或两天去李相云家一次,给她量体温,送来治病的药。半个月后李相云的病奇迹般地好了,这位护士谦逊地说这是上帝创造的奇迹。为了感谢仁慈的主,李相云病好以后,更把她的爱布向人间。
二十八、帮助贫困军属,把爱布向人间
人民政府号召有困难的军烈属组织互助组生产自救。李相云自己的生活并不富裕,还很拮据,但她认为要响应政府号召,军属更应该帮助军属,他通过军烈属互助会,请求安排一位军属大嫂到她的商店来工作。于是一位面容清瘦、肤色蜡黄的中年妇女经介绍来到李相云家。李相云了解到她的家世和身体有病,就安排她干些力所能及的轻活,对她视同姐妹,相敬如宾,每月工资只比自己的工资少几元钱。对李相云的善意,她再三感谢。李相云告诉她: “我们都是军属,互相帮助是应该的”。几个月后,这位军属因病辞职回家。几个月相处的交情,李相云和这位军属成为朋友,还几次带领着她的小儿子去她家看她,逢年过节给她送些食品去。她的家住在城墙边一条低洼窄小的巷内,几乎每下雨就被淹,小屋又湿又黑,常年不进阳光。这真是一位苦命的女性,几年后,她就在家病逝了。
二十九、一九五七年的喜与悲
李相云的二儿子是一九四七年离开家的,三儿子是一九五零年离开家的,为了革命工作,这许多年他们都没有回过家,而且也一直都是单身汉。
一九五七年春节前他们相约一同回家看望母亲,也顺便解决个人问题。李相云得知两个大儿子要回成都家里过年,高兴得忙着收拾屋子,整理床铺,备下丰盛的食品,竭尽所能迎接离家多年在外的两个儿子归来。
这年她的两个儿子,一个二十八岁,一个二十五岁。他俩风华正茂,虽然已转业到地方,仍有一股军人的神韵,让街坊邻居们赞不绝口,李相云的家实实在在地红火了十多天。她每天从合作社下班回家,就忙着调理一家人的生活,每天不论他们多晚回家,她都要等到他们回来,说说话,关心嘱咐,问长问短,方才休息。她讲得最多的就是,要两个儿子好好工作,听党的话,听领导的话,一定不能犯错误。这也是小儿子参加工作之后,她在口头,在通信中对儿子嘱咐得最多的话。可是,谁也想不到,听了党的话,听了领导的话,努力地好好工作,最终仍难免不犯“错误”。怎样做才是听了党的话,听领导的话?什么是错误?错与对的标准为何?几十年过去了,在中国有多少人弄明白了这个人生难题?
李相云的小儿子高中快毕业了,学校让填写学生登记表,经过一九五七年的政治运动后,他对于两个哥哥的情况不清楚。就回家问母亲,李相云沉默无语,一脸愁苦,在儿子的一再要求下,她强忍悲痛告诉他,在司法部门工作的二儿子和在大学当教师的三儿子都成了反革命“右派”。这个家庭从过去的光荣军属一下变成了右派家属,从刚刚才过了几年安稳踏实的好日子,一下又堕入了人鬼皆非的境地 。
其实,数日之前李相云就被通知了此情,可她一直没有告诉身边的小儿子,怕对他造成负面影响。她悄悄地饮下这两坛苦水,当然也没告诉远在长春工作的女儿。但是,己经长大了的小儿子,早己从派出所的户藉警的眼神和口气中,隐隐约约感觉到了什么。一生善良的李相云,不得不再一次为自己的儿子背起了沉重的十字架。小儿子还去信指责这两个不争气的右派哥哥,要他们好好接受改造,重新做人。自以为听党的话立场坚定的他,已经与右派分子的哥哥划清了界线,到高中毕业时才知道,他仍难免受到株连,也被打入另册。但他还幼稚而倔强地去问班主任老师,这是为什么?班主任似笑非笑地对他说:“这不是看你的考试成绩”。再没有多余的回答。刚过十七岁的他,当时只觉得天昏地暗,认为是被两个右派哥哥害了,被跑去台湾的父亲害了。
不仅仅李相云,她们家的每一个人都得受于浣非的株连,都必须为他赎罪。这个深重的莫须有罪孽,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得以偿清?
从此,在共和国灿烂的阳光下,他们全家的每一个人都自觉地走上了赎罪之旅。当然,在这赎罪之途,何止千军万马。从开国元勋,元帅将校,仁人志士,科学家、作家、文艺家,教育工作者、大学生,甚至中学生,都在一夜间变成罪人,成其为赎罪大军的一员。他们中许多人甚至为这莫须有之罪,付出了一生甚至自己的性命。与这些逝去的人相比,李相云一家真算得上不幸中之大幸了。
当然,这也是在被蒙蔽了许多年之后,在中国进入新时期之后,才逐渐清醒,逐渐明白过来的。
三十、博大宽厚崇高伟大的母爱支撑起这个破碎的家
抗日爱国的丈夫已成为历史反革命,响应号召参加整风的两个儿子已变成右派,李相云和他最小的儿子变成了反动派的家属,女儿在东北,她的境况如何不得而知。仅管还有于浣非的小弟和小妹这样的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党员,但那个时代谁也保不了谁,他们受不受牵连也很难说。所以李相云不让小儿子把家里的境况告诉他们,要说一切都好,报喜不报忧。
一九五七年秋天,李相云被合作社劝退了。合作化运动入社时领导美好的许诺没有了(一切生产资料全部交给了生产合作社,全心全意地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社干部许诺说,生、养、死、葬,都由合作社包了),一心一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她,只给发了一个月的工资就让其回家了。她感到很失落。没有了收入(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有三十元,她和小儿子两母子觉得日子过得很知足了),小儿子即将中学毕业,女儿己经结婚且远在东北。
为了生活,为了支起这个破碎的家,已经年满五十五岁的李相云决定重操旧业,自谋出路。可全部生产资料早就入了社,两手空空,政策又限制单干(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最终被迫放弃打算。
为了弥补空虚,在老朋友的劝导下,李相云将家迁往老朋友的空屋子。这位朋友也是从同一个合作社被劝退的。她的丈夫是一位国民党军队的起义军官,早己病逝,留有几间空房出租。她的独子远在内蒙工作,她独居一人,就邀约母亲为伴。就这样,李相云变卖了家产,将家从居住十几年的老房子,搬到只有一间屋子的居所。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将肖军去延安前寄放的物品全部处理掉的缘由。靠过去的积蓄和女儿每月寄来的生活费,让小儿子顺利地从中学毕业。
这期间,李相云心里也一直惦念着那两个被划为右派分子远在西北劳动改造的孩子。她常常告诉小儿子:“手心手背都是肉,十个指头咬咬哪个都疼,你二哥三哥虽然犯了错误,还要关心他们,多去信开导他们,要他们好好接受改造,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李相云说出的话看似平静,可内心所受的煎熬与痛楚,只有作母亲的自己知道。所以,几乎每个月,小儿子都要遵照母亲的嘱咐,以母亲的口吻给他们写信。每封信的内容都主要是鼓励他们好好接受改造,努力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那时候,成为“牧马人”的两位儿子,是否能感知他们母亲的良苦用心呢?他们能坚强地活下去吗?
三十一、高考被意外被录取
被打入另册后,李相云的小儿子已失去升大学的信心。他在学校宿舍悄悄地痛哭了一场,他不明白地责问自己:我有什么错?这么多年,我应该算是一个听话的乖孩子,对党对祖国真心不二,可是为什么父辈的过错要我们来赎罪?不是讲“有成份而不唯成份,重在表现吗”?(在那个时代,像他这样幼稚的人太多太多)。痛定之后,他决心好好接受党的教育,认真努力改造自己,脱胎换骨。(那时一条很流行的口号是:听毛主席的话,活一辈子,改造一辈子。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于是,争取当一名自食其力的,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普通工人,就成为他人生的唯一理想。在相好的同学的鼓励开导下,心里流着泪水,他一边复习功课,一边思考着参加完高考之后的劳动就业。
高考一结束,同学们组织勤工俭学,到省图书馆清理被尘封多年的外文图书,编辑图书目录,以便让这些书籍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他有了参加社会劳动的机会。发榜开始,每天都有同学接到录取通知书,参加劳动的同学逐日减少,他们回家作进入大学的准备了。剩下来的同学,又转到一家木材加工厂去劳动。在又热又臭的胶合板车间里,每天劳作八个小时,日工资三角八分,在工厂食堂进餐,每日三餐最省也得四角钱。劳动强度比正式工人的劳动强度大,而工资不足他们工资的一半,就因为他们是学生。美其名曰勤工俭学,待遇和劳动强度,犹如现今的农民工。仅管劳动条件很差,工资如此少,他们仍准备如果考不上大学,好好表现,争取就这样参加正式工作也好。没有接到录取通知就剩下两三个同学了,李相云的小儿子是其中一个。其他几个同学出于友谊和同情,仍陪伴着他继续在工厂劳动。
一天,李相云在她的老朋友陪同下,找到儿子劳动的工厂,给他送去一封信,是入学录取通知书,他被录取到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学校。另一个同学家人也为他送来一封录取通知书,他们是被同一所学校录取的。他们都十分意外,(那位同学的父亲是一位国民党军队起义的高级军官,在农村当农民);所有同学都为我们高兴,但还有一个同学没被录取,(他的爷爷是清末四川保路风潮的组织者之一,他的父亲在成都解放前夕失踪了),我们三人都是被打入另册的,我们决定陪他继续劳动下去。直到有一天,工厂安排我们做装卸工,搬运一整辆大货车的胶合板,在卸货地点,受到货车司机的刁难和污辱,我们愤而向厂方辞去工作,结算了一个多月的打工劳动所得,除了吃饭,没余下一分钱。但让我们对将来进入和认识社会有了一次难忘的经历。
- 上一篇:风云日月八千里(4)
- 下一篇:风云日月八千里(6)
到过这里的访客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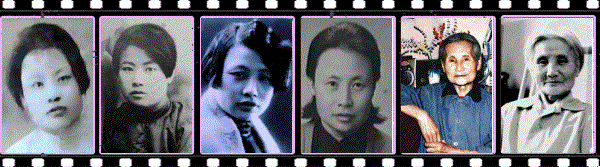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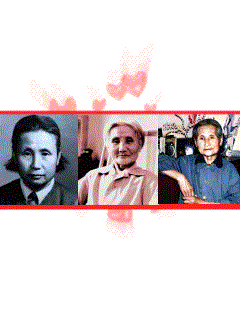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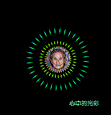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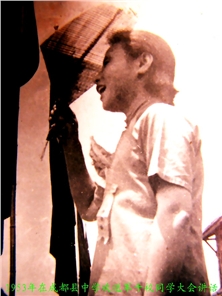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