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宪:我与他人——胡塞尔的《笛卡尔式的沉思》
| 作者:张宪 文章来源:中山大学哲学系 | |
|
胡塞尔生前发表过三部重要的现象学导论性的著作,分别是1913年的《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简称“大观念”)、1931年的《笛卡尔式的沉思》(简称“沉思”)和1936年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简称“危机”)。如果说,《大观念》首先系统地表述了现象学基本问题,《危机》用“生活世界”为所有这些问题的研究来个收场,那么,《沉思》的贡献则在于通过对他人经验或他人构造这一棘手哲学问题的集中审视,连起了胡塞尔自己一生的哲学化活动。 《沉思》是由胡塞尔当时的学生、助教,后来成了法国一位非常有影响的哲学家勒维纳斯(M. E. Levinas),把胡塞尔写的德文手稿翻译成法文,于1931年发表的。德文版的《沉思》则是在19年后即1950年,由奥地利现象学家斯特拉塞(S. Strasser)编入《胡塞尔全集》的第一卷,才得以问世。令人遗憾的是,最先用法文出版的《沉思》译本多有断章取义之处,不是一个好译本。1960年《沉思》英译本出版,译者是有名的现象学家D. 凯恩斯(D. Cairns)。英译本根据德文手稿本、亦参照法译本译出,基本上忠实原稿。现在《沉思》已经有了两个中译本,第一个中译本1992年在台湾出版,依据凯恩斯的英译本;第二个中译本于2002年在国内发行,直接从德文原书译出。 实际上,《沉思》(主要是第五沉思)的产生有一个历史的铺垫。胡塞尔对他人经验的思考,最早的可以追溯到1901年发表的《逻辑研究》。此书在论述语言表达的功能时,已经多少触及到我与他人这样一个交互主体性的问题了。从1905年至1909年,胡塞尔开始着手从方法论上系统地探讨他人经验问题,把现象学还原看成“所有方法中最主要的方法”,并由此给予自己的先验哲学一个立足点。1910年冬季,胡塞尔以“现象学的根本问题”为题开讲,提出再当下化(Vergegenwärtigung)的所谓“双重还原”思想。由此,他一方面把这种“现象学的经验”延伸到在“同感”(Einfühlung)中被当下化的他人体验,另一方面把自然看作已经由现象学处理和整合过的一种“样标”(Index)。显然,这个自然包括了一切在同感的联系中相互交织的“意识流”或者“我—单子”。胡塞尔这时候孕育的这个思想,在后来的《沉思》中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 这里,有一个哲学家不能不提及。他就是被称为“慕尼黑现象学之父”的利普斯(T. Lipps)。同感作为《沉思)讨论交互主体性的一个重要概念,正是从他那里来的。胡塞尔接过了利普斯的同感术语,但是在与他的争论中赋予它完全不同的含义。也就是说,胡塞尔不认为同感是对他人经验的一种类比推演的逻辑结论。或者说,同感并非他人经验在我的本有经验的一种插入。这个看法非常重要,胡塞尔由此才发展了一种真正称之为关于他人经验的现象学理论。摆在胡塞尔面前的问题,不再是关于来自对他人外部躯体(Körper)的感觉域(Empfindungsfeld)的同感,而是一种外在的呈现如何被“解释”为内在的呈现系统,即一种新的、在本有的零位点(Nullpunkt)上定位的、被中心化的对他人以及世界的观照。换句话说,另一个亦如此处于中心而指向世界的观照点(Gesichtspunkt)如何可能。 对于这个棘手的哲学问题,胡塞尔的考虑是,我绝不可以在自己的感觉域内对一个外在被感知的他者躯体直接发生同感。换言之,我并不可以直接地看到他人内在的感受、体验和经验。相反,我只有在我自己的意识里,对他的“观照点”再进行当下化的处理,才可能对他产生同感。引起我的再当下化意识的根据是,我已经不再把他的躯体单纯作为外在的躯体来感知,而是看成像我的本有身体(der eigene Leib)那样的另一个本有的身体。这种所谓的“配对”(Paarung)理论,无疑是胡塞尔处理他人构造问题的基本思路。 事实上,“第五沉思”的形成也与胡塞尔在二十年代给学生开的一系列讲座关系密切。从1921年5、6月至1922年初的讲座中,胡塞尔继续发挥他1910年冬季讲座所形成的见解,试图在一个系统的框架内,解决同感关系中相互并存的诸单子(意识主体)的现象学多样性,即把先验自我学加以扩大的现象学单子论问题。自然,这种单子论的结论,是通过各种意识联系作现象学的先验反思而获得的。值得注意的是,胡塞尔在这段时间里,还研究了其他社会学家如齐美尔(G. Simmel)、韦伯(M. Weber)等人的思想,试图从他人的“观照点”出发,为社会学奠定一个先验哲学的基础。胡塞尔的研究包括:区分不同社会行为的概念,如单纯的同感行为概念、单纯的理解行为概念、在每个个体之上的“更高秩序上的个性统一体”概念等等。胡塞尔还探讨了,通过联结诸单子的我主体,从而联结诸单子的各种可能性。 在1926年至1927年的冬季学期,胡塞尔以“现象学导论”为题开设讲座,对交互主体性的研究又作了新的发展。这时候,他研究现象学的着眼点,不是寻找那种确然认识的观念(die Idee apodiktischer Erkenntnis),也不是还原到确然的自我的我思活动,而是建立作为哲学知识出发点的普遍科学的观念。在他看来,鉴于科学基本概念的不明确性,有必要对此来一次彻底的沉思,从而找到在一切科学中所共有的东西——那个在人的纯粹经验中呈现的世界。不难理解,这就是后来在《危机》着重处理的“生活世界”。 这个作为普遍经验的基础,将在对一切科学进行现象学悬隔(die phänomenologische Epoché),然后在对一种普遍的意识结构的分析中加以奠定。也许,胡塞尔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在先验意识范围内,消除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对立,把先验现象学作为实现普遍科学——这就是哲学的观念——的一条必然途径。总之,可以肯定的是,他这时候试图解决心理——物理的经验问题,寻找回到“原本经验”(die originale Erfahrung)的途径,也就是先验现象学还原的途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详细分析他人的经验。这种分析是直接从他人经验这个事实出发,对他人的意识所作的一种构造意向分析(eine konstitutive Intentional-Analyse)。毋庸赘言,这就是胡塞尔整个《沉思》特别是第五沉思的思想内容。 刚刚谈及,《沉思》是胡塞尔生前发表的三部现象学导论式著作中的一部,对于研究他的先验现象学哲学,特别是交互主体性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部著作中,胡塞尔把他以前主要是二十年代对交互主体性的研究加以系统化,从而使交互主体性,特别是关于他人经验,在先验现象学的基础上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形式。在这部著作的前四个沉思中,胡塞尔分别论述了作为普遍科学的哲学基础的明证性原则问题,讨论了作为普遍方法论的现象学还原,探讨了那种从先验自我出发,构造科学知识的意向性的构造问题,还再次涉及有关内在时间意识的构造问题,等等。这一系列的现象学哲学问题,当然都是分别在其他著作中都程度不同地讨论过的。《沉思》的新贡献在于,从前四个沉思的基础上,着力解决交互主体性的问题。 我认为,关于交互主体性的沉思,显然是前四个沉思的必然展开,胡塞尔不能不写。一方面,他要反驳把先验现象学指责为唯我论的批评,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任何一个哲学分析特别是哲学体系的建立,都会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涉及到我与他人的问题,这是绕不开的。但是,有必要指出,胡塞尔的第五个笛卡儿式的沉思,并非要扩展先验领域,也就是说,并非要跨过一开始就已经被接受的“自我学”立场,而是要更好地阐明已建立的先验领域,从而表明,先验自我学不过是先验领域的一个外观而已。在他看来,作为先验交互主体性的先验主体性的确立,更能确切地规定自我学的还原(die egologische Reduktion)。所以,他在第五沉思中明确指出,基于先验现象学立场的意向分析方法,也能解决交互主体性的问题。同时,交互主体性的构造,提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构造问题,使得整个现象学的构造理论,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只有在这个层面上,现象学哲学才得以最终完成。 尽管胡塞尔在《沉思》中对交互主体性问题作了相当详尽的论述,但他对自己的研究并不感到十分满意。在三十年代前后直到1938年去世为止的那些日子里,胡塞尔一再地重新思考一些涉及交互主体性的哲学问题。例如,本己的和非本己的同感,作为单纯同感的社会行为和作为与他人发生交往的社会行为问题,等等。他对这些思考以及对原来那些研究所写的手稿,都收进了由瑞士现象学家耿宁(Iso Kern)编纂的《胡塞尔全集》十三至十五卷中。另外,胡塞尔的助教,波兰现象学家英伽登(R. Ingarden)写了长篇有关《沉思》的评注,其中不乏批评性的意见,一少部分被收进了《胡塞尔全集》第一卷。胡塞尔的另一位助教,德国现象学家芬克(E. Fink)曾写了《第六沉思》。该书虽然对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理论多有根本性的批评,却为胡塞尔大为赏识。胡塞尔当时曾希望此书与自己的《沉思》合在一起出版,芬克没有接受老师的建议,后来独立成书发表。要想全面了解胡塞尔现象学交互主体性理论的人,这本著作连同胡塞尔自己的手稿都是不能不读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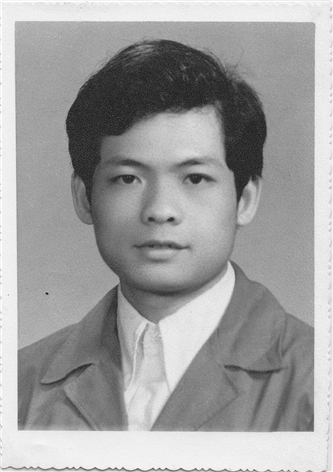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