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逝世百日纪念
——父亲逝世百日纪念
王建中
2011年8月13日凌晨,我亲爱的父亲走完了他85年人生之路,安详地离开了我们。
在父亲去世的100天里,我脑海里时常浮现出他老人家还如平常那样倔强而慈祥的面孔;坐在家中沙发上读书看报的专注神情;在院子里种菜浇水的劳动身影······待回过神来,方知这是梦境虚幻世界,这时,我已泪满眼眶。
追求真理 投身革命
我的父亲王占昌,1927年4月出生在甘肃省合水县一个苦难深重的中国农民家庭。1944年1月,不到17岁的他,与那个年代千千万万向往光明、追求真理的进步青年一样,在陕甘宁边区合水县罗家畔乡政府参加了革命,同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到了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工作和大生产运动。从此,父亲就把自己的个人使命与党的事业、国家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
经过两年的锻炼,1946年7月,父亲担任了合水县二区区委副书记。面对国民党全面发动内战的严酷现实,父亲忠于党、忠于人民,坚信革命一定成功,积极协助党委主要领导,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并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懈的斗争。在敌人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情况十分危急的形势下,父亲勇敢地参加了著名的西华池战役。国民党占领延安后,父亲即同县武装大队一起转移到子午岭山区一带,继续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同时,还在一些地方发动群众搞土改。1948年4月,受党的派遣,担任了宁县工委西区地下工作组组长,改名为赫德福,进入敌占区进行地下工作。在极其危险和艰苦的环境中,父亲和全组同志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期间,一天夜里,父亲在宁县新庄附近和敌人遭遇,战斗中右胸不幸被敌人的子弹打穿,身负重伤。1949年7月,父亲挎着带伤的右臂,随甘肃工委,踏着兰州解放的隆隆炮火,进驻兰州,开始了他和平年代的工作。
心系百姓 造福敦煌
1965年9月,父亲被组织调往敦煌担任县委书记。此前至解放后的10多年间,父亲一直担任党委组织部门领导干部,担任县委书记一职,使他的领导角色发生了转变,成了为百姓服务的“父母官”,也使父亲的领导才能和优秀品德得到了充分展现。
父亲上任后,为了向百姓表达扎根敦煌工作的决心,10月我们就举家从酒泉迁往敦煌。初到敦煌,我们全家都傻了眼,住的是土坯房,还要烧土炕,做饭用的燃料是红柳根,县城街道全是沙土路,车一驶过尘土飞扬,和农村并无差别。当时的我只有九岁,从第二年开始,放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挎起粪筐,外出拾粪(牲畜粪),用来填补烧炕用的燃料以节省家庭开支。
当时敦煌的经济只有农业,由于受“大跃进”浮夸风的影响,1960年冬至1961年春,敦煌大批牲畜死亡,人口大量外流,饥饿死亡蔓延。据统计记载,敦煌全县总人口由1959年的91257人,下降为1960年的84843人,1961年下降为65668人,两年期间,全县人口减少了25000多人,到1965年,全县人口也仅有7万多人。情况虽然有所好转,但“元气”伤的太重,农业生产和百姓生活尚未发生根本转变。
然而就在父亲正准备和县委“一班人”,带领全县人民大干、苦干,打农业翻身仗、为百姓谋利益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从而使敦煌正在恢复的各项工作又跌入深渊。父亲也被造反派强加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徒”、“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牛棚”。那时,造反派在县城经常召开批斗会,每次都要把父亲押出来,“架飞机”进行游行,然后在县城盘旋路搭起的台子上,由两人架着胳膊,一人在身后拽着头发进行批斗。有一次,一名造反派拽父亲的头发,由于时间长太累了,改抓到后衣领,结果造成父亲窒息,在台上昏死了过去,经过抢救苏醒后,造反派仍不罢休,又继续进行批斗,真是惨无人道!那段时间,母亲和我们一看到张贴在大街上批斗父亲的“海报”,恐惧的心都在“颤抖”。由于造反派对父亲的人身摧残,全身两处肋骨被打骨折,颈部神经被打伤,落下了头部摇摆的后遗症。
父亲虽然身陷囹圄,身心受得了极大伤害,但他对党和革命事业始终抱着坚定信念,不说假话,不损害同志和国家利益,无怨无悔,相信是非总会清楚,真理终将会战胜邪恶。以后他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说,“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是深刻的,我们都要汲取,至于我个人的遭遇,则无须萦怀的。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和情怀。
1969年12月,“文革”形势开始好转,父亲也从“牛棚”里被解放出来,先后被任命为敦煌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县委副书记、书记。重新工作后的父亲,不计前嫌,一切向前看,克服种种困难,带领全县人民重新实现他心中的宏伟蓝图。做得第一件大事,就是动员全县人民,兴修水利,建成了党河水库,保证了全县农业灌溉用水;第二件事,就是推行科学种田,提高了粮、棉、油的单产,从而使全县农业生产上了一个新台阶,也为敦煌经济大发展、人民过上富裕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期间,父亲经常徒步走村串乡,一出去就是一、二个月,吃住在农民家,深入群众,访贫问苦,进行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解决实际问题。同时,他还结交了很多农民朋友,父亲下乡曾经住过的转渠口乡和杨家桥乡的2户农民,过一段时间,就进城来家中看望父亲,还要带上他们自家产的农副产品。后来父亲当了省级领导,他们还来兰州家中进行探望,与父亲结下深厚的友谊。
父亲的艰辛付出,造福了敦煌人民,也得到了组织的肯定。1973年5月,他被调任酒泉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地委副书记,1975年10月,又调任兰州市委书记,1977年8月,由于工作需要,又被调任酒泉地委书记。在这短短几年时间里,父亲无论在哪里工作,都能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能紧密结合当地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振兴当地经济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也体现了他对工作的驾驭能力。
端正党风的“卫士” 维护党风的“斗士”
1980年9月,父亲走上了省级领导岗位。一开始担任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第一副部长,一年后,中央决定成立省一级纪律检查筹备委员会,父亲被任命为中共甘肃省纪律检查筹备委员会第一书记,并在1983年12月甘肃省第六次党代会上当选为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父亲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10年。
父亲走上新的领导岗位,面对的是党风遭到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的种种现实,他边筹建边工作,为维护党纪党规,端正党风,严肃党纪,为贯彻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贯彻中纪委的各项具体指示,依靠全省纪检干部的共同努力,坚持原则,敢于碰硬,克服困难,排除阻力,查处违纪案件,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特别是中央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整党决定,开始全面整党以来,父亲参与领导了全省的整党工作,并主持日常工作,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关于整党工作的精神和省委的安排部署,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全面完成了整党工作要求的“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的四项任务,为我省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
1990年,父亲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主动向组织提出了退居二线,不再担任纪委书记一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时刻将党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高尚品德。
两袖清风 爱心永存
父亲一生爱憎分明,坚持原则,淡泊名利,对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嫉恶如仇,横眉冷对。不仅自己始终保持着勤劳节俭、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对家人、亲属,也是严格要求,从不搞特殊化。母亲到退休一直是一名普通干部,我们姊妹三人也在平凡的岗位上工作,父亲从来没有在工作安排、职务提拔等方面打过招呼。他的专车,除了上班、开会等公事外,很少用车,家里人更不能用。1985年3月10日傍晚,我妻子身体不舒服,感觉有临产征兆,此种情况下,都没用父亲的专车,而是由我推着自行车送到公交车站,转乘公交车去的医院,当晚就生下了我的女儿。
1973年,庆阳地区连续三年特大干旱,农民都饿着肚子外出讨饭,奶奶领着父亲的亲侄儿,要让父亲给找个工作,父亲耐心地解释道:我是领导干部,如果带头违反政策,还怎么管别人。后来,侄儿又返回老家继续务农,在一次上山砍柴当中不幸失足,掉下山崖被摔身亡。父亲得知后悲痛不已,只能给我大伯寄了些钱,以示安慰。
父亲对工作认真负责,不徇私情,对生活却是充满爱心,善待他人。在单位如此,在家里也是一样。他和母亲共同生活了近60年,两人相濡以沫、白头到老,互相爱护、彼此关心。母亲平时身体不好,需要经常打针吃药,为了方便以及不麻烦护士,父亲年轻时便学会了打针,能不去医院的,就在家里亲自给母亲打针。有时,我们病了也能“享受”到父亲的这种关爱。1965年,二姐得了脑膜炎,由于当时酒泉医院的医疗水平有限,病情没有得到控制,发展到了生命垂危的程度,父亲急忙从外地赶回,亲自找大夫,和母亲彻夜守护,终于从死神边上把二姐救了回来。1970年,父亲恢复工作后第一次去兰州开会,特意带了一箱敦煌特产“李广杏”,下了公交车,又背着箱子步行近一个小时,看望在焦家湾兵工厂工作的大姐。
由于父亲在老家人们的眼中是“大官”,家乡经常来人找父亲办事、解决问题,父亲每次都以好言相劝,给他们一些生活费,让他们回去好好生活。父亲离休后,在我们工作繁忙没有时间接送女儿时,父亲就推着自行车,亲自去学校门口接送孙女。此时的他,完全没有“官架子”,在我们眼中,只是一位和蔼可亲、疼爱晚辈的老人。总之,父亲的慈爱与心血,渗透在全家的每一处角落、每一个人心中。
父亲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在各级领导岗位上,献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得到了组织的认可、百姓的拥护;父亲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在工作和生活中,清正廉洁、刚直不阿、实事求是、勤政为民,为党和人民奉献出了一切。
父亲走了,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他没有留下多少财物,但他留给我们的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儿孙永远享用!
今天,写下父亲一生经历中的一、二,祈愿宽厚、倔强、慈祥的父亲知道,您的美德,我们会继承,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亲爱的父亲,您听到了吗?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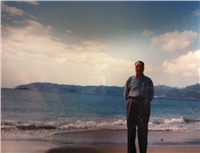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