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省文联工作期间
按:2010年是沈培新同志父亲沈兰村100年诞辰,受沈培新同志委托,我编写了十余万字的《百年缘》,记载他与父兄的百年缘分。他父兄皆为抗战时期的新四军,父亲生前为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副厅长、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兄沈柏青为浙江省最高人民法院主持工作的副院长。沈培新同志不幸前年辞世。此为《百年缘》中他在安徽省文联工作的一段文字,《百年缘》皆经他仔细审阅。
谨以此文深切怀念沈培新同志,
作者 乔延凤
在省文联工作期间
处理“89遗案”
沈一直从事人事工作,包括在大学的人才培养工作、在人事厅的大学管理工作、在省委组织部的知识分子工作。
大概由于经历了89风波的历史阶段,沈在政治上表现得还比较成熟,所以省委决定调他到安徽省文联工作。
沈去的时候,这时省文联没有正式的党政组织,只有一个有职无权的临时领导小组。
89年,省文联有许多干部和党员,都上街游行或贴了大字报。根据当时的政策,都要经过一定的程序,或者是说清楚,或者是受处理,或者是受处分。
因为经过了甄别平反的锻炼,又受到过胡耀邦同志关于历史地看人和宽以待人的教育,所以,沈在处理89问题时,暗下决心,一个都不处分。
为此,他找了几个一时想不通的文人谈心,建议他们作出检讨,以求早日解脱。
他先找了一位诗人.
这位诗人在全国的诗歌界有一定的影响。
在互相叙谈中,沈劝他:“89年的事,已成了历史,但上了街,写了大字报的党员,总得有个检查,不然整党时不好说、不好办。”
这位诗人说:“我想不通,国防军的任务,主要是对付外来侵略,哪能镇压学生呢?”
沈说:“我们现在还是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既有对外的国防任务,也有对内的护卫人民的任务。再说,当时天安门的具体状况我们也不知道。还是相信中央吧!”
这位诗人又说: “那事情我没有弄明白以前,我不能检讨。”
沈说: “这样吧,也不等你把事情弄明白,这不是一时可以清楚的,整党是有时间要求的,你也不必做全面检查,中心就写;我是党员,服从中央的决定。这还是应该的,也是可以的。”
这位诗人终于表态:“那好吧。”
省文联同类的事件太多,省委和社会都很关注进展的情况和处理的结果。
省里一位领导同志劝告沈培新:“该怎么处理,你就怎么处理吧,没有必要去保那么多人,你自己的政治生命也很重要啊!”
沈培新听了以后,也做了认真思考,他还是觉得,做官要先做人,党性和良心,通常是一致的。能不处理还是尽量不处理吧。
他对人说:“文人又不是政治家,他们往往好冲动,好感情发泄。89年那场风波,我们也都是过来人,那时候,我的爱人每天吃饭都要看新闻,一听到汽笛声,她就说,坏了,又有学生中暑了!全国都在关心着学生们,他们年轻,大多数也并没有什么政治背景,怀着一颗单纯的心,安徽也没有发现有里通外国的人。能保还是保吧!”
最后,这个单位还是处理了一个处级干部。
沈找这位处级干部谈了半天话,讲了许多政策性、情感性的话。
这位处级干部就是死不开口。说来说去,只有这样几句话:“谢谢书记的关心,我没有认识到,我不能检讨,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我不会怪你们的。”
结果,党支部决定给予警告处分,党总支决定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单位党组意见是留党察看,而上级批复是:开除党籍。
党籍是保不住了,可是行政上,尤其是工资待遇上,我们还是尽力地给予他帮助。
事隔几年以后,沈培新在一次会上说:“从政治角度说,他不检讨是不对的,但从人格上说,他还是一个讲人格的人。”
现在,社会显得十分浮躁,有不少的领导同志、党员同志,已经忘记了党员的宗旨和公仆的身份,把自己看成是官僚,说什么“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自己打扮成了救世主。
封建社会里,做官还要讲忠心,还要讲人格,还要有骨气,现在,在有些人身上,连这些也都被统统抛弃了。
“一江春水向东流”
文艺界的人,大半都有些真实本领,各有各的风格,各有各的风采,也各有各的成就。加上他们长期地在一个单位里工作、生活,恩恩怨怨,你一团我一群,今天我俩好,明天他俩亲,以至该开的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三十二年年都没有能够开成。
沈培新到任以后,首先要解决两大任务:一是妥善处理89遗留问题,二就是开成安徽省文联的文代会,还要争取开好。以求得安徽省文艺界的大团结、大繁荣、大发展。
经过将近一年的筹备,安徽省文联第三次代表大会总算如期召开了,可是,哪里知道,谁当文联主席,又成了难题。
处理89遗留问题时,省文联的鲁彦周同志,因为支持学生运动,在当时中央、地方的报纸上登的支持信上都签过名,在社会上影响大,省里还是一直想让他当新一届文联主席,处理89遗留问题中,他已做了检查,就通过了。
文联的一些老同志对鲁彦周政治上不作处理,是赞成的,可是他们不知道,不处理就可以在新一届省文代会上当选省文联主席。
结果,当省里研究安排鲁彦周当省文联主席时,分歧就发生了。
省文联两位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领导、老作家陈登科、那沙,都认为不论从年龄上讲,还是从政治上讲,省里选定的当文联主席的人选鲁彦周,他们都不能认可,而且表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他们要保留向中央反映的权利。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省里面感到很为难,如果他们真的到中央去反映情况,中央可能会批评安徽:30年都不开文代会,现在开了,难道非得选一个有问题的人来当省文联的主席不可吗?
最后,省委只好作出决定,采用别的省份的做法:要沈培新兼任这个难产的安徽省文联主席。
公正对待文艺界老领导
沈培新做了省文联主席以后,为了做好文联的工作,十分注意处理好这几位老领导的关系。他对他们都非常尊重,不偏不倚。
省文联的一些老同志,长期以来,结怨太深,谁都不肯主动出来和解。
沈认为,先不谈让他们坐到一起吃饭,首先要做到能够和平相处。沈就分别和他们交心、谈心。
他对他们说:“我作为省文联的书记,对你们都一样尊敬,能关照的都关照,能帮忙的都帮忙,能出力的都出力。我有时请鲁老,有时请陈老,有时请那老,你们不能坐在一起,都不要见怪。是谁的朋友来,我就请谁出来。”
在他的公正的原则之下,这些老同志都没有什么意见。
他为这些老同志做了许多工作,解决了他们的实际困难。
有一位老同志的儿子是残疾人,沈考虑到残疾人是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应当予以照顾的,就主动向省里打了报告,要了一个照顾的名额,解决了这位老同志多年来没有解决的残疾儿子的就业问题。
这位老同志的心里感觉十分温暖,后来向人说起沈培新同志,总是说,作为一位党的领导,能做到这样关心同志,很不容易。
他帮助陈登科组织了一次作品讨论会。那一次讨论会,从北京和外地邀请了不少文艺界的领导、评论家、文艺家来参加。
那沙先生的文集出版,他也给予了支持和帮助。
他想为鲁彦周同志组织一次他的文学道路的研讨会,他说等一等,结果他的《梨花似雪》出版后,为他举办了《梨花似雪》作品研讨会。
对待鲁彦周同志,还要提一提沈初来省文联工作时遇到的一件事:
前一届党组留下一份材料,是对鲁彦周小说《天云山传奇》的,当时,省里党的组织、纪律检查部门对这部作品有看法,认为是为右派翻案的。
当时,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因为当时对右派的问题,中央并没有说要平反。
组织检查部门对小说有看法,也很正常,但这就是个政治问题了。
沈培新就和省文联的同志广泛接触,听取大家的意见,没有把它当作严重的政治问题来对待。
他和胡耀邦同志接触过,聆听过胡耀邦同志的谈话,所以使他对待历史遗留问题有了正确认识。
《天云山传奇》属于伤痕文学,是对过去“左”的政策的反思,是有历史价值的。
坦诚关心青年作家
陈源斌是安徽省文联的一位青年作家,以写小说知名文坛。
他创作的小说《万家诉讼》,后来被改编为《秋菊打官司》,由张艺谋执导、巩俐主演,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他是安徽省文联一个有争议的作家,其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他在天长县入党的问题。
1992年的夏季,安徽省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其时,陈源斌在自己要求下乡体验生活、进行锻炼的安徽省天长县的一个村当副村长。
那里的乡党委,向安徽省文联党组发过一封公函,说陈在他们那里的表现较好,要发展他入党,征求省文联的意见。
这封信,省文联机关党委书记没有收到,省文联党组也没有收到。
当时,沈培新正带领安徽省抗洪救灾巡回报告团,在北京做报告活动,不在合肥。
后来,陈源斌在天长县那边入了党,手续办完,并且由上级党委批准了。这时,陈源斌正式对省文联党组讲,他在那边入党了。
在和平的环境里,按照常规,他应该在省文联入党,在天长县挂职期间的表现,可以提供给安徽省文联的党组织。
但他在那边已经履行过入党手续了,怎么办?
沈培新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没有表态。他叫省文联的机关党委书记胡震同志,去向省直工委请示一下:像此情况怎么处理?
省直工委的同志听了情况以后说,按常理,他应当由文联的党组织发展,但那边已经发展了,属于个例。
胡震同志问:“那怎么处理呢?”
他们回答说,这是抗洪救灾阶段发生的事,情况比较特殊,省文联里的情况也比较复杂,就口头答复说,也可以吧。
说同意吧,也没有正式的文字批复。这件事,就这样不清不楚的。
后来,陈源斌从天长县挂职结束,回省文联来了,把党的组织关系也带回来了。
省直工委也默认了,省文联的机关党委书记胡震说:“陈源斌回来了,就跟省作协党支部的贾梦雷同志商量一下,把他的组织关系放在省作协吧。”
贾梦雷同志当时也感到为难:他已经是党员了,又不能开除。贾也就就接收了。
当时党的支部生活也还没有正常起来。
这期间,安徽省文联的二里街宿舍区发生过一次火灾,一座小红楼被烧。
陈源斌家当时正好住在那里,也是受灾的文联同志之一,当时的省委宣传部牛小梅部长,获知受灾,还去看望过他;他的小说《万家诉讼》也是在这时被改编成《秋菊打官司》的。可以说,当时大家对他的创作成绩都感到高兴。
沈培新看他创作势头不错,就对他说:“你就乘势而上,好好写作,不要考虑别的问题。”
沈培新也知道陈源斌在省文联有对立面,作家相互之间的关系不好处。
沈培新对青年作家,总希望能尽量发挥他们的专长。
在主持省文联党组工作时,一直考虑安排陈一个合适的位子,后来就安排他在省文联的文学院当副院长。
沈培新离开文联以后,由刘景龙来当省文联的党组书记。刘想把陈由副院长磨正,另一位副院长刘祖慈不为磨正,把刘调到作协,叫陈当院长。
党组决定了以后,才打电话来告诉沈培新(此时沈当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分管省文联的工作):让刘祖慈去当省作协的秘书长,由陈源斌当文学院院长。
沈培新问刘景龙:“你和省作协通过气么?”刘说马上通气。
后来,出现了省作协刘先平、贾梦雷同志抵制,省作协宣布,让李亚平同志当省作协的副秘书长。
当时,沈培新就和省委宣传部部长杜诚,把省文联党组的同志们找到省委宣传部来。
沈对党组的白龙驹同志说:“你知道刘祖慈是自己宣布退出省作协的,现在叫他去当省作协的秘书长,省作协当然不会同意。”
出现了僵局以后,拖了很长时间,最后又把刘柤慈退回文学院,叫陈源斌离开文学院,让他进省文联党组,当党组成员。
后来,又发生了陈源斌和省文联一些青年作家公开打官司的事情。
2002年,陈源斌感到自己的工作环境不好,经过全面考虑以后,他提出要到浙江省作协去工作。
当陈向沈培新谈这件事的时候,沈对陈的选择表示同意。沈培新对他说:“你只要感到自己心情愉快,能把工作做好就行!”
“约法三章”
文艺界是美女成群的地方,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场合很多,加上西方“性自由”思潮的影响,稍有不慎,就会卷入情网、情敌、情仇之中。
所以文代会闭幕不久,沈就给自己约法三章:
不和女演员单独约见,晚上各种应酬只到八点左右,九点以前一定回家,不打听不了解女演员的私人生活。
沈培新果然就这样严格要求自己,即使事务再多、再紧张,他都在九点之前回到家中。有些必要的谈话、会见,他都安排在公开的场合。
他和文艺界的文艺家们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帮助文艺家们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深得文艺家们的信赖。
大家都乐于把心里的话说给他听,请求他的分析、帮助,所以这期间,只要你到沈培新家中去,常常可以看到安徽文艺界的作家、艺术家们在他家作客、谈心。
他也有带文艺家们出去采风、演出的机会,他和作家、艺术家在一起,谈笑风生,是那样的自然、和谐、仿佛就是一家人一样。
在他担任省文联主席的那些年,安徽文艺界不仅团结活泼,而且成果也是非常显著的。许多文艺家都心情舒畅,创作出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
文艺界的好领导
沈培新是从安徽省教委副主任位子上调到安徽省文联任党组书记的。
沈培新说:“我不靠权利去领导,而是靠决策的科学、同志与朋友的相处,靠实在有效和可行的措施来保障任务的完成。”他有自己的领导艺术。
他对自己要求严格。1989年6月9日,他就写过一幅自勉的条幅:
当官一要清廉,二要公正,三要干事,四要平等。
他在安徽省文联主持工作期间,正是用自己的领导艺术,按照这四条做的,所以深得文艺家信赖,很快使文联工作开展起来。
他乐于为大家办事,解决别人的困难。到省文联后,他常和文艺家们推心置腹地谈心。有时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获知单位、个人有什么困难,他就设法去解决。
在经费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解决安徽省文联职工住房困难,他和党组同志共同研究,筹措了资金建造了二里街6号楼住宅楼;又考虑到老干部们的晚年生活,还同时专门建造了一幢老干部活动楼;在安徽省委常委会上,他为省文联的几位老领导要了一部专车。
这些,省文联的文艺家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沈培新对几位有名望的省文联老领导、老文艺家,同样尊重,不偏不倚,他善于倾听他们的意见,所以避免了产生新的矛盾,使文联工作平稳发展,顺利完成了解决遗留问题和文联换届的任务。
他平易近人,作风民主,真心地关心文艺界的同志们,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所以,在文艺界,他有许多新老朋友。
前几年,他不幸患重病住了一次医院。
2004年10月,他去亳州市参加彭雪枫将军纪念活动,发现自己身体不大好,当时也没有放在心上。他平时喜欢买些医疗方面的书籍来读。就自己对症治疗,进行调理,觉得身体又好了。可是到了2005年春节,家里儿女、亲戚对他说,身体不好,不要小视,还是去医院看看吧。春节过后,沈就到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直肠发现了非典型性息肉,实际是直肠癌。
就住院进一步检查、开刀。
沈当时对医生提了个要求:我一生生活得很愉快。要求直肠保留住,不插管,如果不能保留,开刀后就再缝起来。活一天算一天。
后来还好,虽然保留很困难,还是保留下来了。
沈培新对生死问题看得很透彻,早啊晚啊,人总有一死的。战争年代那么多年轻人都牺牲了,抗震中7、8万人都死了,他觉得癌症也就是一种慢性病,不要把它看得那么可怕。他坦然对待癌症,抱着乐观的态度,现在开刀以后,已经过去四年了,身体仍然很好。
那次,为了治疗直肠癌住院开刀,前往医院去探望他的,多达一百四十多人。
他的安危牵动着省内外许多朋友们的心。这情景连医院的医生们,也深受感动。
八十多岁的老文艺家郭因还专门写了一幅条幅给他:
人是好人,管是好官,善缘广结,海阔天空。
遒劲而娴熟的笔墨,饱含着安徽省的文艺家们对沈培新的一片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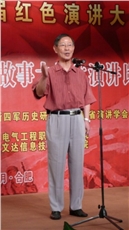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