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责任」两难之战——王度庐
诚然,爱是一种不同的生命体验,其价值观因人而异。但若涉及到责任关系,原本单纯的「爱」就会变得极端复杂;再进而将两者对立起来,非此即彼,积不兼容,便终不免一战。而这种隐藏在心灵中的战斗,往往是自毁性的「善」与「善」之争。其惨烈、痛苦程度,即当事人亦无法形容。
《鹤惊昆仑》正是「爱与责任」两难周全的一大悲剧典型。它以一般江湖仇杀、冤冤相报的故事套子为外部架构;内则致力营造一个逼使英雄儿女面对「命运的悲剧」而又无可逃避、摆脱的极限情境——对于江小鹤来说,父仇不共戴天!他是非报不可;而鲍阿鸾为救乃祖之命,亦非全力阻挡不可!于是「报仇」与「反报仇」遂各自形成某种在伦理道德上的至大至高「责任」。他们互怜互爱,但分别又与其不可逃避的「责任」相冲突!怎么办?作者只有教阿鸾以自杀殉情的方式来解决这两难之局——虽然在事实上此一「死结」并未打开,它成为小鹤心中永远的「痛」!
相信作者写阿鸾悲情而短命的一生是噙着泪下笔的。其所述阿鸾种种内心挣扎、分裂、交战以至感情崩溃、爆发;最后且引「情人剑」自杀相殉,可谓字字濡泪,血染桃花!当这一痴心少女垂危之际,犹呻吟着说:
「你甘心了吧?……这你还不出气吗?快再刺我一剑,别教我受罪……小鹤,你这狠心的人……我等了你十年……我虽嫁了纪广杰,可并没跟他好!……十年前我小的时候答应你,我……我并没忘呀!」(见原书第十七回)
此情此景,何等动人!也许唐人李商隐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便是阿鸾最佳写照吧!
提到「爱与责任」这个在西方歌剧中常出现的对立性主题,就不能不谈造成鸾、鹤命运悲剧的鲍昆仑。由于他刚愎自用,又受到群小包围蒙蔽;进而残害门人,纵容凶徒,且硬逼孙女阿鸾嫁给纪广杰;一直固执到底,犹自以为代表「正义」!因而种种悖乱皆由其本身性格的悲剧导出,并成为本书一切悲剧的根源。
书中说老鲍「最得意的爱徒」龙志起无恶不作,人尽皆知;偏偏它却曲予包庇,言听计从。老鲍之「护短」是基于其牢不可破的错误观念,认为龙某忠于师门,决非歹人!同时为保全自己的江湖令誉,乃无视于客观存在的事实;反而偏听信龙某一面之辞,力加庇护,死不改悔!这与其说鲍昆仑是「老糊涂」,不如说是他过于「自私」——系由本身刚愎性格所决定——这正是他倒行逆施、执迷不悟的主因。作者写鲍昆仑所作所为,全用「反跌法」;特别是本书第十五至十七回,刻画鲍、龙师徒二人明暗对比的心理变化,入木三分,令人叫绝!
固然《鹤惊昆仑》一书大巧若拙,美不胜收;且布局严密,情节动人,足以哀感顽艳,但在故事结构上的败笔亦有所不免。笔者认为,本书在写到江小鹤扶鸾柩返乡,「又见柳树,又见柳树」而此恨绵绵无绝期之际,就应戛然打住——让读者置身于那四面八方扑上来的愁云惨雾之中,咀嚼回味,黯然神伤——当可将这部「悲剧侠情」杰作升华至更高层次的文学意境中去。
怎奈当时作者无米下炊,「为稻粱谋」而著书,只有往下「拖」!致使全书故事已近尾声时,又把所谓「武当七大剑仙」(?)中的吕崇岩扯出,瞎闹一场;并一再「补叙」前情,实无必要。卒令原先所营造的凄美气氛为之大大减色,殊为可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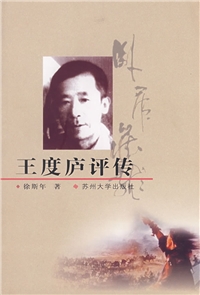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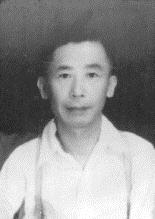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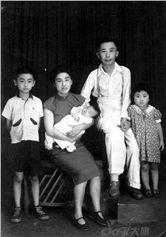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