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网友的文章(摘录)回忆《十送红军》的由来
小的时候就从收音机里听到过这支《十送红军》,徐缓优美而凄婉的节律,整齐中还有着丰富的变化,一下子就打动了我。此后,将它改编成一部无伴奏合唱并亲自指挥全国巡演成为我的一个梦想,而且至今没有实现。不久我见到了它的几个曲谱,负责的,在上面除标注江西苏区民歌外,还表上搜集整理者张士燮、朱正本的姓名,不负责的,只简单的标注江西民歌。
尽管如此,随着在下耐心细致的体悟,还是隐隐的觉得,这绝对是一首采用民歌形式完成的新创作歌曲,并为此向朋友们打赌。没有什么,尽管词曲的民歌性已经很浓郁了,但是仍遮掩不住文人创作的痕迹,在审美情趣情景的设置营造上,透着一股文人的情调。总之,它太完美了。
谜底的解开,是2001年电视连续剧《长征》将这首歌曲用作片尾曲,在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建议下,在2001年的7月3日播的第15集(待考)片尾的编创人员字幕表里打出了“歌曲《十送红军》张士燮编词,朱正本编曲”的字样。为此,词曲作者整整沉默了四十年。
原来,1960年,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出访朝鲜,看了大型歌舞史诗《三千里江山》(据说连同那部很感人的电影《卖花姑娘》都是金日成主席亲手创作的),3000名朝鲜战士的激情演出,令刘司令很是震撼和羡慕。第二年他便给空政文工团总团副团长张双虎布置了一个任务:三个月内创作一台革命历史歌曲晚会。时间紧迫不说,刘亚楼还提出了一道“禁令”:一定要采集革命历史歌曲,而不要新创作。
接到这个任务后,空政文工团立刻行动起来。当时文工团创作室的张士燮、朱正本、姚学诚、陈杰被派分头负责文字、音乐、舞蹈的创作。为了收集到足够多红军时期歌曲,刘亚楼还亲自动员老红军、老干部们到文工团来“献歌”。可是,尽管大家广为搜集素材,但在再现红军告别苏区开始长征的主题时,却找不到一首合适的歌曲来表达根据地人民送别红军的不舍之情。
“不管刘司令的禁令了,创作一首吧。”几位创作者的大胆之举,便成就了后来的这首《十送红军》。
而另一个版本的传说是:1960年以来,连续3年的困难和灾害,国际上反华势力也借机在政治上施压,新中国处于危难之境。这时,亟须一大批优秀的艺术作品鼓舞民众士气,我国的文艺工作者深感身上使命之重。
1960年10月21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把空政文工团总团副团长兼歌舞团团长牛畅叫到办公室说:“我们空军要带头,拿出一部反映中国革命斗争历史的大型歌舞剧来。”他还说:“我们的同志不了解革命历史,不懂得艰苦奋斗,你们文工团就应多唱一些革命歌曲,让同志们重温一下我军走过的历程,这是有教育意义的,既可发扬传统,又能激励斗志。这部歌舞剧可以这样弄,素材和歌曲尽量用以前的,用当年的歌曲反映当年的历史。你听着,3个月以后一定要拿出我们自己过硬的东西来,到时我要来看你们的演出!”
牛畅回到团里向总团党委汇报,定下创作方案并获刘亚楼同意后,空政文工团派出张士燮、朱正本、姚学诚等词曲作家,到革命老区湘赣两省搜集整理革命历史歌曲。为了保证有足够的红军时代歌曲,刘亚楼还动员老红军、老干部献歌。这个版本,起码在时间上得到了曲作者朱正本的佐证,他说:“1960年春(准确时间是1960年3月,曲作者等人作为贵宾应邀参加了在江西省九江市举办的江西省农村业余会演),我们空政文工团几位创作人员到江西采风。在当地我了解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战斗频繁。每当红军上前线,各个村子的百姓经常到村头、河边、大道旁送别红军,有时一边送一边唱。其中一首送别红军歌,曲调非常口语化,歌词中夹杂着不少俚语、方言,唱半句,停半句,旋律婉转优美。这首歌的曲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然后,记者的笔一转说道:“半年之后,空军司令刘亚楼和部队党委决定由空政文工团创编《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这虽不是引用的曲作者的原话,但我想,就一般采访规律来说,这个时间,是引用的曲作者的说法。而这所谓的“半年之后”,正好切合了那个“10月21日”刘亚楼司令员下命令的时间。这就不是孤证了。但是说“1960年以来,连续3年的困难和灾害”却又言过其实了,三年灾害一年还不到就让它承担全部责任吗?
真实的历史,就这样在不同权威的解说中,悄悄的走了样。虽然隔着并不遥远的时空,但我们不知道此事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到底是向张双虎副团长还是牛畅副团长下的命令,亦还是向两位副团长都下了?我看过“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这台《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牛畅和空政文工团歌舞团的名字赫然在列。就连那个去江西采风的活动,也有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了,一个说是接到命令后才有的行动,一个是在接到命令前就去了。
不管怎么说,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在1960年前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要求空政文工团三个月之内搞一个尽量采用原有历史歌曲编成的大型歌舞剧《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文工团拿出了4万余字的剧本,剧本分9场16景,共计19个组舞、46首歌曲。而在写到第四场红军长征时,担任文学编辑的张士燮觉得需要有一首歌曲来表达根据地人民送别红军时恋恋不舍的心情,这样也可从情节结构上同第三场反“围剿”的戏衔接。他决定亲自执笔,因为有这次采风经历,他笔下立时就流淌出优美而动人的诗句:“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间野鹿声声哀号,树树梧桐叶落完。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在创作中,他把自己搜集到的多首有关送红军的歌词综合起来,从一送红军,一口气写完了十送。接着在唱词中掺杂了“里格”“介支个”等江西赣南地方的方言,以进一步突出地方民歌色彩。
作曲家朱正本接到歌词后被深深打动,他立即想到那首江西的送别红军歌。《辽沈晚报》的一个版本说他“油然想起赣南的采茶戏,其中有首送别的曲调如泣如诉,欲言又止,深深地吸引了他,何不把它拿来作这首歌的音乐基调?他从中寻找到了创作灵感,谱写出了婉转优美的旋律。”这应该是真的。这首送别的曲调如泣如诉的赣南采茶戏就是《送郎调》。他说:“我采用了回旋曲式手法重新创作,把六段歌词谱成每段不同人声、不同曲调,并多次变化,以求情真意切。谱曲时,我投入了全部情感,在谱到‘千军万马江畔站,十万百姓泪汪汪’时,我也流下了眼泪。整个曲子谱得相当顺畅,总共不到一个小时。
至于为什么没有直接署创作者的姓名?是源于“反右”还是“文革”的迫害?都不是。皆源于刘亚楼的一句命令:只用原有革命历史歌曲,不另创新歌。因此在《十送红军》送审时,就有人主张要撤下。可更多人认为,拿掉太可惜,而且从剧情结构上也需要保留它。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建议朱正本、张士燮两位作者都署名为“搜集整理”。于是,为执行刘亚楼的指示,避开创作痕迹,空政文工团决定把全剧的文学、音乐、舞蹈三大创作班子统统称作“编辑”。就连曲作者朱正本也说道“由于当时刘亚楼司令为突出老区革命传统,要求我们必须注明是民歌,总团领导建议我们署上朱正本、张士燮收集整理。这样,《十送红军》就创作完成了。”
这样的解释,颇让人感觉是“空政文工团总团在欺瞒刘亚楼司令员进而欺瞒天下”之意,并让人有“嫁祸刘司令”之感。哦,领导说必须采用原有革命历史歌曲,你们招呼也不打一声,就创作了一首“伪民歌”硬塞进去充数?不让署名能怪刘司令员吗?如果据实汇报了,刘亚楼司令员未必不同意保留并准许署上创作者的姓名。即使刘司令员不让放进去,作为一首非常成功的创作歌曲,还怕它流行不开吗?全国绝大部分人都没看过那部《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不是一样喜欢这首歌吗?这就是证明。是金子,放在哪里都是闪光的。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整个创作团队都刻意的同领导保持了一个默契:谁都不敢第一个向领导提这是一首创作歌曲。可见这是当时文工团领导的意见。群众怕领导,小领导怕大领导,谁都不愿意挨领导的训,谁都怕得罪领导,事情就这样沿袭了下来。更何况,该作品赢得了刘亚楼和众多老领导们的喜爱,一失足成千古恨,越是这样,就越是没人敢说了。曲作者朱正本说,在整台节目中,刘亚楼尤其喜欢《十送红军》,人前人后时常念叨,“别人唱快一点儿他都不愿意,生怕唱快了人家就听不清楚歌词。”他还说,很多老首长也都非常喜欢这支歌,甚至会经常出来“捍卫”它。比如,曾经有人提出“三送红军到拿山,山上包谷金灿灿”写得不对,说那地方没有包谷,萧华将军就站出来说:“江西有包谷,我就在那儿吃过。”因此,直到刘亚楼去世,他也不知道《十送红军》是首“违令”歌曲。可见,领导想知道点实情,难啊!
这一现象,直接导致了中央电视台在拍摄24集电视连续剧《长征》时,作曲王云之也认为是一首地道的苏区民歌而径直拿来使用和改编。事后,他得知了情况,立马通知央视和剧组,赶紧在此后播出的剧集上署上词曲作者的姓名。
经过精心打磨苦练,这部名为《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大型歌舞剧首先在上海与观众见面。1961年“八一”建军节,从上海载誉而归的剧组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公演,更是盛况空前。其中《十送红军》一曲,“散场时就有很多观众边走边哼唱着《十送红军》。”朱正本记得,后来文工团还应观众要求,把《十送红军》的词曲都印在了演出说明书上。同年底,这台节目又在上海连演40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每周一歌》等栏目里反复播放《十送红军》,各大报纸杂志也争相刊登这首歌的词曲。《十送红军》从此传遍大江南北。
张士燮在《记作曲家朱正本》中曾写道,“不少老红军当时听了这首歌极为感动,似乎又回到了当年的苏区,回忆起许多感人的往事。因此也就自然认了它就是一首苏区的革命歌曲。这首歌在全国流传后,人们也都把它当成一首革命历史歌曲了,实际上是朱正本为当年革命历史歌曲填补了一个空白。”
此歌在刘亚楼在世的时候就已飞向了国外。朱正本说:“以前,刘亚楼司令常到团里来说,‘我们的《十送红军》已经传到国外去了。’这几年我通过音著协寄来的版权使用清单才知道,原来真的有很多国家都引用过这首歌。”自2009年起,朱正本已经接到过俄、美、英、日、意、法、荷等十余个国家寄来的版权使用费。虽然钱不算多,但却都列得详详细细,这让他体会到了身为作者的荣誉和快乐。
值得一提的是,这台《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成为日后我国第一部大型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雏形,内中绝大部分歌舞都被吸收了进去,当然也包括这首出色的《十送红军》。
而词作者张士燮,爱好音乐的应该很熟悉。他是跟李双江一样享受军职待遇的职业军队文艺家。天津人,1932年生,小曲作者朱正本四岁。17岁参军到四野十二纵队,参加了南下剿匪等战役。19岁就发表了反映剿匪生活的处女作——独幕话剧《天亮前后》,引起反响,他很快被调入专业文艺团队,开始了军队文艺工作者的生涯。尽管他创作力旺盛,佳作迭出,也一直坚持不懈的争取入党,但直到1980年12月12日48岁了才成功入党。在其五十多年的创作历程中,创作歌词数千首,有近30首歌曲获全国、全军各种奖项。《十送红军》、《毛主席来到咱农庄》、《社员都是向阳花》、《秋收起义歌》、《农友歌》、《银球飞舞花盛开》、《爱是不灭的火焰》等是其流传最为广泛的代表作。2007年7月20日(有说是21日的,可能是因晚间逝世次日才公开消息的缘故吧?)晚21时20分于301总医院经抢救无效病逝。而在此前的3月份,已是肝癌晚期了正在住院治疗的75岁的老人,一听说有创作任务,强烈要求出院,参加在河北涞水举办的全军军旅抒情歌曲创作班。那些天,他强忍着病痛折磨,天天深入一线部队,和战士们座谈,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靠药物支撑,一气写出了15首歌词。“军营门前有条河,夕阳吻着流淌的碧波,我在河边弹起六弦琴,向着那远方的姑娘诉说……”谁能想象,这首优美抒情的《我的六弦琴》,会出自一位癌症晚期老人的笔下?这位58年军龄的老战士,以自己高质量的创作和严以律己的高尚品格,诠释了对军队的无比热爱。2007年7月19日上午,张士燮的病情再次恶化,他的嘴在一直嚅动着,他的老伴文椿知道他的心事:“士燮,你是不是想穿新军装呀?”张士燮微微点头,泪水流了下来:“我……我可能等不到‘八一’了。”空政文工团团长杨月林、政委许亚西闻讯后,潸然泪下,表示一定要满足老兵临终前的惟一请求。 病榻上,张士燮终于如愿了。团领导和医护人员将一套07式“空军蓝”穿到他病弱的身上,那一刻,张士燮的脸上满是幸福的喜悦。7月20日,一生勤勉高歌的张士燮悄然作别这个日益繁华浮躁的世界。
昨天看见儿子从电脑里找出《十送红军》这支歌来听,我想起了这些,便拉拉杂杂的写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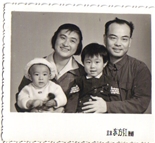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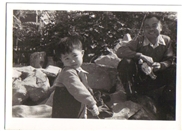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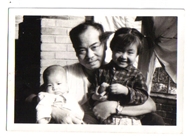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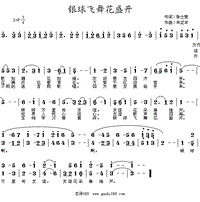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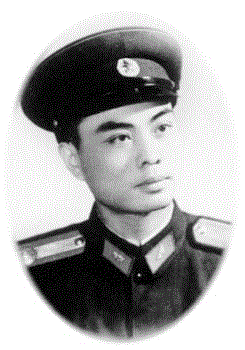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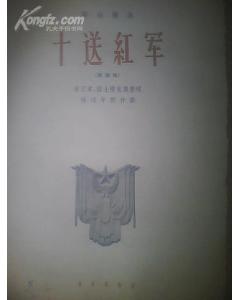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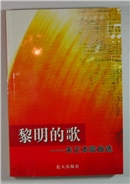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