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归故里
魂归故里
------父亲去世三周年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农历癸未十二月初九)
一
银装素裹今又是,家严魂归已三年。
二00一年一月三日,农历庚辰年十二月初九傍晚,接到邯郸传来的噩耗,父亲在邯郸病逝了。虽然十个月前曾赴邯郸看望病重的父亲,深知年事已高的病者随时可能都有危险,但仍不能抵住内心的悲痛与哀伤。如今已三年,父亲如同仍生活在我们的中间。三年里,多少次在梦中相见。三年里,积攒了比我前五十年还要多的眷恋。
父亲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农历己未年五月二十七日)出生于原籍河北省武安市儒山村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务农,到一九四八年离家到当地煤矿参加革命工作,不久到华北勘探队,一九五五年春随队北上到下花园,后随单位体制变化,该单位划到张家口第三地质大队,直到一九七九年退休。几十年的漂泊不定的地质工作者的生涯,铸就了一个普通中国农民转向一个工人而特有的勤劳俭朴,不畏困难,顽强奋勉,默默奉献的坚强品格。父亲虽只是千千万万的工人中的普通一员,虽只是围着过锅台转了几十年的一名炊事员,虽只是目前早已被人们遗忘的一个普通工人,但在我们六个兄妹中,却永远是像巍巍燕山与太行,像大山上耸立的高峰,像高峰挺立的苍松;父亲的音容,就是家乡的北明河,就是家乡的儒山,在我们的心中永存。
二
父亲留给我人生记忆中的第一印象是那样美好,并永远地被记录下来。由于自己从小愚笨,开窍较晚,幼年留下较多的印象是家乡村落的概貌,是外祖父外祖母全家及院落的情景。离开家乡迁往千里之外的下花园,有些细节如同看过的电影那样,如今还能出现在眼前,但未能记起父亲在召集全家搬迁的哪怕是最小的一个细节。
一九五五年春,塞北的气候要比冀中平原冷得多。全家安顿之后,父亲便带领全家,从下花园煤矿四井到下花园的中心市场,那是记忆中的第一次全家一起活动。我跟着姐姐,父母亲倒替着抱着年幼的妹妹,大哥领着三弟,翻过两座山,踏上了一座大桥,下面是流淌着的黄色的大水。我从桥面的漏水洞朝下一看,只见深不可测,河里的黄水在翻腾,不由得害怕起来。大概全家人谁都不会注意,只有自己知道。但我看到有父亲高大的身躯,宽阔的脊背,顿时又不害怕了,赶紧追了上去。这是多么大的力量啊!我们逛了市场,但没有太多的印象,只记得在公路街尽北头现在已成为地道桥的地方的地摊上买了一双鞋,大概是大哥穿的吧。然后我们了到照相馆,那一刻,我的记忆犹深。感到照相那么新鲜,那么大的房子。房子里那么多的灯,打开灯是那么的明亮,灯光照在墙上,墙上有那么大的画(布景),可以卷上来,也可以放下去。卷上去后面又是一张,真是漂亮,又很好玩。我们全家摆好了姿势,照相的 人拿了一个小铃铛,晃动响声,吸引我们一起朝他那看,照相的人站在高低与人接近的一个架子面前,上面蒙着一块大黑布,他一会钻进去一会儿钻出来,让我们如何如何,他再次钻进黑布出来时,铃铛一响,我们往他那一看,只听“喀嚓”一声,说“好了”,我们全家完成了第一次有纪念意义的合影。这张照片直到现在一直保留着。稍大后才明白,那是父母携家带口离开家乡后,拍得全家福寄给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给上一代老人留个想念。这张照片的拍照,使我感到,是父亲带领我们认识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父亲太伟大了。如果说幼年的记忆全是农村生活,那么从北上到火车站时开始认识城市生活的话——第一次见到暖水瓶、牙膏、面包、尽管当时不知叫什么,更没有条件买一点去吃了,但这些东西留在脑海里,——那么这次照相、逛市场,是记忆中已经过上了城市生活。与之相关的,还记得家中的电灯是那样的神秘,又那么可怕。但记得在更换灯泡时非常危险。一次大哥换灯泡,差一点中了电。电灯亮了,是多么的美好。不仅屋里有灯,连外面也亮着灯。这是农村无法与之相比的。是的,父亲把全家带出来,母亲在此渡过了53岁的一生,父亲将44个春秋也留在了这里,子女们在这里成长起来,这里成为我们第二故乡。
三
父亲一生中,对我们是严厉的。他给我留下的唯一的一次,也就成了终身的印象,尽管此后没有再发生,而且更没有在我的身上发生。还是从家乡到第二故乡下花园不久,那一天的事不知是从何说起的。
只记得父亲拿着一把扫帚,在门前的小院里,追着大哥要打,逼他去上学。在几十年之后与大哥谈起,大哥当时也是觉得自己已大(当年15岁),再去读小学,觉得没意思,同时看到家中拮据,也想早早参加工作,帮衬家庭。当时,不知是大哥没有表达清楚还是父亲为了培养下一代,宁肯自己受苦受累,再不能像他那样没有文化而受治,在我稍大一点,大哥已到宣化就读高中后,我才稍稍懂得了父亲也包括母亲为何要让子女读书的道理。父亲要填写一张什么表格,当时似乎很神秘,现在才知道,就是个人履历表。父亲认识的几个字,对于填写履历表来说远远不够用的。大概为此托人代填,也是件难为情的事。可能如同现在的人们为调动、升职、升学之类托人差不多吧。不过那时只是件人情的事,还没有像现在必须送礼才办。可能是当时是读书人少的缘故,不知父亲费了多大的周折,才将那张表填写好。我的印象很深。当时是填写了两份,一份交了单位,另一份自己保存,以备再填写时,照此抄录。直到一九九九年五月父亲离张回邯郸清理家中物品时,证实了我当年的记忆确实没错,发现了那张保存了几十年的履历表。
那个年代,书信往来是人们沟通的主要方法,也是唯一的方法和手段。只有在家中发生重大的事情时,才通过拍发电报联系。当年祖父和外祖父病故时收到电报也需找人去念,可想平时写信更是件难事了。到了我刚刚认识几个字时,收到家乡的来信,连认识带估摸勉强读给父母听,也曾为写回信使我犯愁,不知该写什么,也不知那些字如何写。这使我体验到了没有文化是多么的难!一次家里收到老家的来信,给父母念来信的地址,使他们也莫名其妙。直到事后多年,认识的字多了,才解开这一迷团,我把当时信上写的“骈山公社儒山村”念成了“马并山公社儒山村”。只要自己想起此事,都有些哑然失笑。我逐渐懂得了父亲让大哥读书的良苦用心!没有文化,作为人的一生是多么痛苦。父亲为了下一代,不论怎么做,也都不算为过。父亲逼兄上学,给我留下严厉的印象。但我却深深懂得父亲发自内心深处的对子女一种期望的爱。
父亲的严厉,在我一生中,也就是独此一件事情。正因为如此。父亲的每一句话,在我看来都是重要的,都不敢违背。在我稍大一点后,父亲就又常年不在家。每当休假回来的短短几天,我们都是谨小慎微的。每有不妥,父亲最多是不满意的瞪一下眼睛,这大概就是最严厉的批评。也正因为父亲长年在外的缘故,父亲说话时,我听起来很是吃力。父亲说不易听懂的话既不象老家的口音也不象本地的话音。父亲说的话在我们兄妹中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直到我调到张家口工作,有更多机会与父亲交流才得以缓解。听话费力,大概也是造成父亲严厉的原因之一吧。有了父亲的严厉,才使得我们众兄妹在艰难的生活中都读了一些书。长兄从小学跳级,读完初中,高中未毕业应征入伍。他是在正规教育中学历最高的。我和姐姐在初中毕业遇上文化大革命,参加工作之后便是自学,弟弟妹妹们有的是高中毕业,但也不是那么非常正规了。但毕竟为今后的工作、学习奠定了文化基础。再也不象父母那样因无文化而苦恼了。众兄妹们后来发展情况尽管不尽相同,都实现了父亲当年的宿愿。如今我虽不能像作家像名人那样为父亲争光,但却可以写下此文,用以表达对父亲永久的怀念,用以对父亲的回报。
四
父亲是勇敢的。在煤矿居住一年后,全家搬到下花园的石佛寺,远离闹市区。在一条山沟里分散住了十来户人家,顺着沟往上走,便登上了下花园最有名的山——鸡鸣山。顺沟下游走不远便到了洋河。我记得,在家家户户的墙上,都画着大大的白圆圈,说是可以防止狼的侵害。晚间,几乎每天可以听到狼的嚎叫。房前屋后,山间小道,常见一堆堆的白色的粪便,据大人们讲那就是狼粪。在夏夜,胆子大的人,可以隔窗望到成群的狼沿沟而下到河边饮水。为了安全,到冬季人们早早地关上门不再出屋。把门关上之后,里面再堵上一张门板。也是从那时起,开始听到了关于狼的故事,也就关心起了关于狼的故事。人在夜间行走,觉得肩膀上似有人扒扶,千万不能回头,以免遭狼的突袭,可猛的蹲下身体,顺手抓住扒在肩膀上的东西往前狠摔。冬季夜间行走,都要把皮袄披在身上,而不穿在身上,一旦有狼扒身,可以顺势脱衣而逃。在陷井里放上羊,人藏在井中,上盖门板,狼闻或听到有羊踏上门板,爪子必下伸,人就可以抓住狼爪,隔着门板将活狼背回家。还有掏了狼崽,母狼如何可以找到并报复掏狼崽的人等等。在那时,做了一个终身难以忘记的关于狼的梦:就在那间土房,对着远方高山的门,狼们到了门口,由于我们家的门上挂着一个门帘,门帘是用皮革作的。不是牛皮就是猪皮,门帘从门头往下有门的三分之二长,下面可以从屋里直接看到院里。那狼就在门口转,看看门帘不敢进门,我在门里站着看,既觉得有些怕,又不是很怕,看着那些狼如狗似的活动着。可是,就是再那样的环境里,父亲上下班经常是披星戴月,必须走过一段山路。这段山路绝不会碰到人的。特别是在隆冬的季节的夜晚,父亲手里拿着一个手电筒,伴随他在狼迹出没、人迹罕见的山道行走。在我的心中,那是多么勇敢的行为。正是如此,也使我在后来的独自入山的打柴采药中没有感到怕!当然,父亲也曾遇到过一次有惊无险之事,不知父亲后来记得否,在我心中永久没有忘记:那是在隆冬的一个黑夜,父亲照例下班沿那条小道回家。刚离开单位不远,便需翻上那座小山坡。小路斜着穿过山坡,到山坡顶再下去才能到家。就在半坡之处一阵狂风突起,父亲紧了紧身上的大衣,背着风停住了上山的脚步,待风稍小一点,正要迈步前行,忽然从前方的高坡上往小路下来一个庞然大物。它从高坡上不紧不慢地往下走,在小风中没有声响,只有风吹动着荆棘黄草的声音。父亲只好又把欲将迈出的脚步收回,停在原地,让它先走。这时父亲想到的可能是遇到一只熊或一只狼。退不能退,进不能进,只能随机应变了。那庞然大物慢慢的来到小路的中间一动不动了。似乎要和我父亲作对。双方僵持着,那家伙就是不再动弹。父亲想,总不能这样下去,便试探着往前挪动一点。那家伙没动,又挪动一步、两步,那家伙仍然不动。父亲此时便猛地打开手电,赶紧向前走了几步才看清楚,原来是一棵干枯的沙蓬草被风刮到路中间。父亲明白了。回到家中,才发现浑身是汗。这虽是一件一场虚惊的事,但在孩时的记忆里,是那样的惊心动魄,那样地具有征服战胜凶恶的感人魅力。后来,我们搬家到了离闹市区更近的地方车巷子街,俗称大水泉,即现在的水泉公园。
不久父亲领我和姐姐报名读书。逐渐长大后得知父母也是为了出于对孩子们的读书上学方便,才再次搬家。从此离开了偏僻的小山沟,离开了城市中的“农村”,真正来到了城市——实际上是城市的郊区的边缘。
五
父亲又是正直的。父亲不善言谈,何况在家时间不多,且说出的话音听起来较吃力。从父亲那里听到的所谓大道理不多,但只要说上一两句都是发人振聩的,永远铭记在心。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对于长年在深山人少的环境中的地质工作者,可能参与的要晚一些。但在武斗盛行之际,父亲休假回家,告诫我们“武斗总不能叫什么革命行动不能去掺和”,这与当时的大背景似有背离,但父亲的话我们还是听进去了。虽然我们不可避免地都投身于那场革命之中,但却听了父亲之言,没有表现的像有些造反派那样搞那些打砸抢之类的活动。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父亲的正直,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行动来表现来证实的。父亲的正直,给我们是不屈的、不倒的、永远的、高大的印象。他犹如列队中站立的排头兵,犹如广场上树立的旗杆,犹如山颠耸立的钻塔,犹如城市中耸立的摩天大厦!那是我即将入学读书时发生的事,尽管父母不是讲给我们的,但也没有回避我们而谈。我记于心中,指导终生。父亲单位的一位同事的钱丢失了,不知怎么父亲成了嫌疑的重点对象,似被单位的有关人员找去谈话。那是给人以“奇耻大辱”之感,果真如此,那将如何为人?父亲回来与母亲说起,只是觉得窝火,但却理直气壮!虽是“理直气壮”但在案子未破的那段时间里,父亲不免背着沉重的包袱,承受着无形的巨大的压力。在组织上和一些人眼里,父亲是很有可能的,家徒四壁和一群要吃要喝的孩子,父亲微薄的经济收入。天理公正,父亲也是不该蒙受不白之冤。窃贼抓到了!这消息,大概失主也没有父亲那样高兴!“人穷志不短”的人生课,使我终生受益。在父母的辛劳操持下,带领全家度过了最艰苦的岁月。当熬到日子趋于好转时,母亲因病早逝了。父亲与儿女们一起迎来了不愁吃穿的这一天。
父亲的正直更体现在他对任何人和事都无怨言上。当险些遭受蒙冤之后,父亲没有怨天忧人,没有嫌组织上对自己的审查,反而觉得经过认真破案,更为自己的清白增添了证明。父亲的秉性遗传给我,使我在后来的工作中不怕组织审查,经得起组织和历史的检验。父亲去世后,又因变故组织上对我的工作进行调整。我不仅不怕组织的审查,反而主动向组织提出要求,对我的工作给予审查,接受组织的考验。父亲虽交友不广不深,但也从未听父亲曾说过一句对领导、同事的怨言。家中长兄当兵、我入团和后来上工农兵大学等,都因家庭成分问题受影响,可父亲从无流露出一点不满。听母亲讲过,在土改时,因土改工作偏差把咱家的财产没收,后又返还给超过原来家产的东西。父母对此提起,都是从肯定的角度,在我的幼小的心灵中感到了共产党的伟大和正确。到长兄当兵时,我已很记事了。家庭情况调查表明,把我家的中农成分重新订为上中农。长兄很生气,父亲当然无能为力,但却没有流露丝毫对此事的不满,只是流露出一种无奈。不管怎样,大哥当兵走了。到了我入团时,学校又调查,还是因为中农还是上中农的问题不清,在班里没有被第一批吸收到团组织。当把上中农是因村中某些干部私自改动的情况调查清楚之后,我从思想上才解除了“家庭成分”的包袱。而父亲对此却依旧的坦然。长兄在部队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我少年时代感到了无尚光荣。它证明了我的家庭、证明了我的祖父、我的父亲都没有问题。父亲的正直,也直接影响了我的一生,虽然在1973年工农兵上大学之际,又因家庭材料未齐而为能去成,但却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提成了国家干部,尔后逐步走上了基层领导岗位。父亲的正直也影响着整个家庭。到现在,父亲的六个儿女有五个成为共产党员。
父亲的正直,我不仅继承下来,而且也要传下去。我加入党,受着父母的正确教育,且亲身感受到了共产党的恩情,朴素的感情是最初的动力,后来不断提高着觉悟,提高着认识和理论水平,不断成为一个自觉的努力的为党为人民而工作的党员干部。自己永远把握着:在市场经济的汪洋之中,永远了望着政治航标的灯塔,在几乎一切都成为商品的社会里,决不能将党性原则,党和人民的利益,自己的灵魂标价出售,这是做人的原则。不论别人如何嘲讽、议论,也不论别人的嫉妒、攻击,我永远是我。吃着踏实,睡着安稳,活着坦荡怡然,死时无悔无憾。我的女儿考上大学后积极申请入党,便予以鼓励和支持,递交了申请书。之后听女儿说,要入党,先得给有关人员送礼,且有送了的已入了党。我立即告诉女儿,如果是这样,我们宁可不在这里入党。掏钱买党票,是对党的玷污,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亵渎,是对人格的背叛,是对灵魂的出卖。虽然在大学其间未能加入,这没什么值得遗憾。人生的路漫长,只要追求进步,不愁加入不了。反过来说,如果所在地方或单位,如果仍以收礼为条件,那么宁可永远留在党外,不与这些“党员”为伍!我之所以这样教育女儿,就是要她学会正直,也是以实际行动证明我自己:在入党的时候,就是靠自己的政治上追求,在工作中努力,而决无人际关系;当我在企业主持党 委工作发展党员的时候,也是考虑那些申请入党人的政治和工作表现,决无与我本人有任何私人关系。假如我让女儿花几个钱入党,那女儿对党该怎么看,会把少数问题看成普遍性。那女儿对当基层党委书记的父亲该如何看,是不是她的父亲也是这样的卑鄙低劣,收受入党人的钱财?作为一个干部无法向党和人民交代,作为一个儿子无法向父亲交代,作为一个父亲,无法向自己的子女交代。这也或许不是后天的继承,而是“正直”基因的遗传,使我具有了这种难移的禀性。
六
父亲是辛勤劳做的。从我记忆中,尽管父亲写给家中的信不多,但从信的地址上看,几乎走遍了张家口区域的各个县。到过的大大小小的村落恐怕谁也一下子难以说全。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也时常不住村落,往往带着活动房屋在工地附近支起,就是地质勘探者的住所。这些只是间接的。而一次我直接看到的也是唯一的一次,父亲随队到村里工作的情况。那是外祖父去世的消息,电报到了下花园,母亲即让我去找父亲。父亲此时恰巧没有到较远的深山,而是可以说在最近的地方。离下花园约三十里地的地方——怀来县西八里公社东八里大队,我坐火车到西八里站下车便一路打听,走到了东八里村。进村后按村民的引导到了父亲的工地。我到时,正是生火做饭的时候。现在想起来,可能是父亲也刚到了所在地时间不久,炉火不太好使,厨房设在一个不大的小院,进入院落的一间房子面积不宽绰也不高,就是农村中最普通的土房。挨着窗户有一个灶火,安着一口大锅,屋里充满刚刚点燃的柴草的生烟。我走进屋里,一时难以看清父亲的面孔。父亲正在边烧水,边忙着面案上的活计。父亲听了家中的事情,便向领导请假,回老家处理丧事。此事已过去四十多年了,而我仍记忆犹新。我常想,在东八里村,对于常年野外工作的人员来说,那是很好的地方,离市区不远,交通也较方便。尽管这样,父亲在给野外工作者做饭的条件也就如此,可以想象,如果在坝上人迹罕至的草原,如果在交通不便的深山老林,那样的条件该又当如何。在一次不经意谈话中,得知父亲每到一地,现垒炉灶的事情是经常的。“兵马未到,粮草先行”,在某种意义上,父亲的工作就是地质分队的尖兵。每到一处,炊事人员必先赶到,把炊具预备好,保证分队工作人员的饮食。有时候想,父亲虽是一名普通的炊事人员,这一生如同军旅生涯一样,不知踏遍了多少沟沟壑壑,不知在多少个地方垒灶生火,冒出第一缕炊烟;不知为了垒灶的一砖一石,为了生火的一把干柴,为了解决急需的一瓢凉水,为了使工作人员吃上一次最简单的饭菜,为了这样看似很平常的小事,都不知花去多少努力,永远不为他人所知。当然,父亲的辛劳,也是那一代人,也是那时的地质工作者的缩影和写照。而父亲,就是我心中的偶像,值得我永远崇拜。
父亲的辛勤劳作还留在了家中的一些杂活上。在石佛寺住的时候,房后的荒山坡地不少,父亲利用工余时间种了玉米,在父亲做饭的厨房不远的小山坡上,父亲还种了一畦长白菜。我记得,当白菜长到抱心的时候,往白菜上面压上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块。让白菜长得心更实,更大。我隐约记得,这是父亲采取得原籍种菜的方法,而在当地的人看见此法还以为奇。搬到了大水泉之后,家的西南侧便是一片沼泽地。父亲开辟了一块地种有两种菜,至今不忘。一种是父母称为“莴苣”的而当地人称为生菜,另一种是父母唤其为“君哒”的而当地人称为甜菜。这两种菜,都是可以不断的撇下它的外面一层的叶子食用,它又不断地长出新的叶子。当时,为菜名的不同叫法深以为奇,觉得我们老家和本地就是有许多的不同。一到下花园就接触到不很习惯的大豆、莜面、西红柿等食品,给童年深深的印象便是异土风情。从那时起,很是留心父母说到的家乡与此地差别的事,而家乡的一些方言,且不说音调,只是那些不同的词汇就与此地有着很大的差异。正是因为这些差异的缘故,更加深了童年对种植蔬菜的记忆。更加体会了父母辛勤劳作伴随他们的一生。通过种植蔬菜和不同的叫法,也不只是留下以上的记忆,还给我增加了相关的知识。到后来,我逐步的知道了,“莴苣”这一菜名包括了它的叶用、茎用的两类品种。而当地人称叶用的为“生菜”称茎用的为“莴苣”,而忝菜(甜菜)的称呼,是和“莴苣”一回事,只是别名而已。只不过此人不知有此名一说。这种菜也分为叶用、根用和糖用。我们当时种得都是叶用的。这些在别人看来都是无关紧要的零碎小事。而对我来说,觉得也很有趣,他充实着我生活的内容,他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六十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困难的家境雪上加霜。然而,并没有将父母压垮。父母不仅有艰辛度日的毅力,也具有着从农村带来的战胜灾荒的经验和能力。平时,母亲在家的合理安排,带领我们挖野菜等不必提及。父亲在得到休假回家后,也一同投入到采摘野菜的“战斗”中,哪里能得到一丝清闲?哪里能像现在的人们休假,呆在家里看电视听音乐都不能过瘾,而要天南海北地旅游了!从那时起,我学到了忍饥挨饿的耐力,学到了采摘野菜充饥的本领,学到了父母不畏艰辛憧憬美好生活的人生勇气。父亲曾带领我们到渠沟哇边、上山坡洼地采挖马齿苋、(马什菜)、蒲公英、苦渠菜、扫帚苗、沙蓬菜、仁贤菜、(大头菜、杏仁菜、)茴茴菜、马奶子、叶儿薏、羊奶子、洋条稍等叫不来学名而只是百姓俗称的野菜。带领我们采摘榆钱、榆树叶、杏树叶也曾到采地里拣萝卜缨(这是上等菜、)白菜叶、白菜根。也学会了对这些野菜的鲜食、晒干以及将榆树叶、白菜根碾成面食用。学会了对这些野菜不同的“烹饪”方法,苦渠菜、叶儿葱、马奶子、蒲公英可以生着蘸酱吃、凉拌,也可用水焯一下拌菜。扫帚苗、沙蓬菜、仁贤菜、茴茴菜除了焯后拌菜吃,还可大量的掺入玉米面、高粱面、蚕豆面做菜窝窝,也可将这些菜作为馅作成菜团子,这是最主要的菜种和食用的方法。马齿苋用水焯或可晒干,仁贤菜、茴茴菜可直接晒干以备冬季食用。榆钱是不多的,因为树高,又不多,难以采摘。偶尔采摘,可蒸馈捋,也算改变一下胃口和口味。至于杨、柳的嫩叶、羊奶子、洋条稍叶子都是在开春后青黄不接时无奈才不得以食用,它们很苦,必须用开水煮熟捞上来用清水浸泡,然后每天换一两次水待五六天后可食用。一年冬天,偶尔发现菜地里的菜根,拣了回来,将土拍打干净,琢磨怎么吃它。菜根较硬,又没有多少可直接吃的东西。通过碾榆叶面便将它一并碾成了面,那时,长兄在宣化读书,星期天回家也一样去菜集野菜。在最困难的时期学校实行“劳逸结合”。“逸”就是那时学会的生字。我每天从学校早早的回家后,便不声不响地习惯拿起家中长长的布口袋,到外面去拔野菜。回来或是现用,或是将余下的晒干。困难的年代什么都不会白白扔掉。父亲因家境窘迫,抽的烟一直是低劣的品种。六一年冬,父亲休假回家带回来从农村老乡那里买到的烟草的桔杆,我们帮父亲在碾子上碾碎,以充父亲的烟袋。在那时,认识了一种不知名的野草。据说是做烟叶不错,黄豆大小的叶子微红,和叶子颜色相差无几的约二三寸长的茎匍匐地面而长。这留做了永远的回忆。
父母含辛茹苦,培养我们成长,也培养我们学会吃苦的精神。大约是从1962年起,在采集野菜中,开始了采集中药材。忘记了是怎么开始的,也忘记了是向谁学的第一次认识的药材,但时间不会错。因为一次按药材采回的一些山丹花的块茎,因药材公司不收购,将其当菜炒了不大好吃,因此肯定是还没有离开吃野菜的年代。后来,每到暑假期间,我便上山采药材,以做为家中的补充收入。而父亲休假时,也带我一同上山。当时的我,因为成熟的晚,个头较低,体质又弱,干别的活都很困难,割草可以买钱,但自己出去一次,背不了多少,挣不了多少钱。打荆条,也曾试过,打回来的条子等级低,卖不上价。有一段时间,干脆自己用条子编筐,这些筐用了一些年头。当我选上了采药之后,一连坚持了几年,认识了为数不多的几种,但以一种为主,也能换取当时认为有所值的钱。而父亲带我上山时,便更增加了我的力量。尽管我一人上山,也未曾想到过害怕,但有父亲在身边,更觉得心里踏实,采集的效率会更高。下花园附近的大大小小的山包,没有一个没去过的,有些上山的路,不知多少次走过,对那一石一木非常熟悉。一次与父亲从鸡鸣山采药,到了路边遇到一个卖香瓜的,父亲买了几个,这正是又累又渴的时候。平时,身上带个玻璃瓶子,灌上些水,喝完之后再渴的话,只能在山上偶尔发现或找到背阴处的山坑里的积水,补充一点,带的水多又是累赘,今天,父亲买上瓜之后,给我一个就让吃,这是多么香甜的瓜啊!我还从来没有个人先吃过家里买回的东西。父母给我们养成了好的习惯。不论家中有点什么吃的,大家都要平等对待,没有先后之分。烈日炎炎,酷暑当头,劳累饥渴交加,父亲破例给我一个香瓜,当时,也有点“受之无愧”,便尽情的享受了一番。我和父亲背着药材和香瓜,满怀喜悦的回到家中。下半晌,在家中也不是歇息,而是将采回的药材加工、晾晒,这种主要的药材便是远志。从我认识它起,便给我一种可爱的感觉,它的茎虽细弱,但笔挺,紫色的花虽小,但醒目。他不仅通过我的采集而可以补充家庭收入,而且它的名字是那样的给人以鼓励,它的药用价值也与名称相一致。“远志”,远大的志向,“远志”长远的意志,“远志”永远的志气。我们采集时,尽可能地刨得深一些,使它的根全部采回,加工时,用适当的力将其弄扁了,将其中心的木质去除,只剩下根上的皮,把这些皮晒干,就可作为药材出售。如果正常的话,每天可以得到干货一市斤左右,卖一元二三角。这在当时来说,也相当于一个普通劳力的日工资吧。别的药材如知母、麻黄、五加皮、柴胡、甘草等,有的是找到的不多,遇上便采,不去专门采,有的是找到了,也没有力气去采。所以便集中注意力主要挖远志这种有着响亮的名字的药材。后来,又有两年家中养家兔,虽然养的不多,也能换取个酱醋钱。为兔拔草也曾成为课余的重要工作。也曾扛着镐头上山打柴,把荆条整个刨下来背回家。再将起根茎分别晒干储存,其根的热量大概也不低于煤吧,烧起风箱(风匣)火来那是很有劲的。家中困难,本不是好事。但历来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十来岁时,就能知道拿两角钱能买几个茄子、几棵菜,眼一看,就估谋个份量差不多,连卖菜的都称奇。从那时起,就知道用仅有的一点钱采购回较多的菜(购便宜)供家里食用。从那时起,从父母那里学会了如何将一分钱掰开花。家中很少买盐面,都是块盐,用时捣碎,偶尔买一点,也轻易不用,能买每斤0.12元酱油决不买0.14元的。在若干年中,父亲每月寄回家的生活费是固定的,那时由单位代办的。每月40元,到家中是39.60元,花掉了0.40元的邮费。这些钱,要供姐弟4人上学和母亲及小弟6人的生活费,这怎能不精打细算哪?这些往事,已深深打印在脑中不可磨灭。
父亲留给的这种精神,不仅仅使我在生活中能够克服困难,而且使我在工作中同样不怕辛苦,也使我在当前的不良社会风气中站稳了脚跟,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参加工作30多年来,不论是在企业班组干活,在车间搞管理,在机关坐办公室,在企业做领导,未曾怕过艰苦,未曾偷过一点懒。无论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还没有超出当年翻山越岭打柴、采药的艰苦。尽管由于能力所限,在各个岗位上成绩不著,但却问心无愧地说:在各个岗位上都是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的!当我看到腐败风熏染着官场,金钱风侵蚀着心灵时,当我看到人们已不把大吃二喝、胡吃海喝、挥金入土当成问题时,还能义愤填膺、满腔怒火,不屑一顾、洁身自好。这不能说与从小受的艰苦的教育没有关系。这种免疫力使得我终身受益。
七
父亲对子女们的爱,也如同母亲给子女的一样,是铭刻在心的。父爱,是深沉的,是雄劲的,是能以感受而难以形容的。父爱是大厦之基,是大桥之墩,是大江之源。父爱,犹如大山将长城托起,父爱犹如蓝天将明月高悬。那是1964年春,母亲病重,父亲陪床。年长18岁的大姐至年幼半岁的小弟五人艰难度日。此时祸从天降,住房倒塌,使我惊恐万分。此后在梦中时常惊醒,暂时休学。记得是父亲曾睡在我的身边,这时记事以来在父亲身边睡觉的第一次。每当我从梦中喊着叫着醒来是,父亲亲切的说“不要怕,不要怕,爹守着你”顿时,紧张的情绪平静下来,骇人的魔魇即被驱逐。过了一段,自己也感到从病魔中挣脱出来。虽然后来多年常有从梦中惊醒,曾因失眠而休息,但这短暂的在家由父亲陪伴几天,我深深感到父爱的力量!1969年国庆节前夕,父亲从涿鹿县回张家口,从宣化下车,看看我的情况,并带来了一挎包的苹果。我见到父亲非常高兴,这是参加工作后父亲第一次来到我的工作单位,又第一次见到带来的大苹果!我让父亲留下一点,其它的带回家,父亲笑着说,都是给你的。父亲看了看我,从头到脚,突然说“孩子,都国庆节了,天都冷了,怎么还光着脚啊?”在那时代,人们天热的时候是不穿袜子的。我当时也不知为什么,没有感到天凉,还是不知换季的时间,仍没有穿袜子。光脚穿着最普通的平底鞋。我从这次起,才开始了季节变换而及时更换衣服。每当秋季换季时,每当看到苹果时,就不难想起几十年前这件事。那天,父亲呆了很短的时间便要走,我要送父亲到汽车站。父亲坚持不让送。我与父亲在厂门口的路边告别。此时,一阵秋风刮起,父亲的头发在风中颤动。我突然发现,父亲的鬓角上闪出几丝银发。我的心中突然生发出一种无名的惆怅。脑海里浮现出曾读过的一篇小说中的主人公,与母亲告别时看到母亲的白发时的情景,感到那种心情正是文中所描写的,是难以言状的。这可能是我对父爱的首次精神回报!
父亲后来因年岁已大不再到野外,留在单位的修配厂工作。我便偶尔有机会看望父亲。这就较过去与父亲相处的机会增多了。1975年,我调到张家口工作,也是母亲去世之后,我更多的和父亲在一起了。从这时候起对父亲所说的话,才慢慢的不那么“陌生”了,逐渐听懂了父亲的讲话,尽管听不懂的话还偶尔发生。从这时候起,父爱就更加深深地融进了我的心中。
那是父亲在退休之后的事情。我刚成家不久。父亲不顾年高,从煤渣中筛捡煤核,积攒起来,供我冬季夜间“封火”之用。忆起年迈的父亲如此劳作,为儿女不惜付出,是多么的撼人肺腑。对父亲的崇敬之意幽然而生。父亲近80高龄之后,曾劝父亲和我一起生活,但他不愿为子女添麻烦,而仍坚持独立生活。当他自己做饭已感力不从心后,便在居住的附近的小店买饭。1997年秋天的一天,我去给父亲送食品,在半路上遇到父亲,父亲手里提着个小马扎,步履蹒跚。此时,我才真正的觉得,父亲真的老了。父亲把家中的钥匙给我,让我送回家中。父亲在街头坐着歇息。第二年的冬季,父亲便再也不能自己支撑,才将长兄唤到父亲身边陪伴,后又来叔父与父亲相陪。父亲不让工作着的我们,分散精力来照顾他。父亲的晚年,虽退休金不甚丰厚,但他完全可以生活的稍好一点,这并不需要子女们给父亲经济援助。然而,父亲仍是节俭度日。但当子女门去看望他时,他却显的“慷慨起来”,改善一下生活,为子女们、及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们留下了更多的怀念。父亲将他所有的爱全部奉献出来,无私地送给了子女及他们的后代。
八
父亲心胸豁达,乐观向上。没有文化,生活贫穷,不善言谈,这不妨碍父亲开朗的性格的表露,不妨碍父亲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父亲的长年野外生活,在冬季休假是相对多一些的,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年了,那是冬季,父亲回家了,扛着一口袋东西。打开一看,是榛子,父亲说这是用业余时间到山上采摘的。这是第一次见它,第一次吃它。味道是很香的。记得这年冬季,我们姐弟有了香甜的“零食”。又是一年,父亲回来了,带回来的是用篓筐装的俗称酸溜溜的山货。至今也不知它的学名为何。在带刺的干支上结着一簇簇的似黄豆粒大小的橘黄色的小果实。它像葡萄珠一样,一口咬下去,便破了皮。酸酸的,甜甜的。很是可口。街头也有人在卖,如同卖酸枣那样。在下花园的附近山上没有,不曾摘到。要不是父亲下那么大功夫,将它带回来恐怕吃它也只能是以后的事了。又是一年冬季,父亲穿着大皮袄回家了,一到家中,便听到父亲身上有蝈蝈叫的声音,我很是好奇,父亲从怀中掏出来,——蝈蝈和笼子。这笼子里放着一只蝈蝈。。小笼子轻巧,玲珑。虽是用高粱杆的外皮编制的,但令人喜爱。父亲像变魔术一样,从大皮袄里不断的变出了好几个。这年的冬天,家里充满了生机。蝈蝈的叫声带来了无穷的欢乐。父亲这年所在的地方,没有什么土特产,只好想办法充实在野外的生活。父亲说,在野外的许多人,都捉到了蝈蝈。大家到了一起,蝈蝈的叫声响成一片。冲淡了野外的生活的寂寞的氛围。父亲说,他们在火车上,蝈蝈的叫声引起不少旅客的注意。那时的我,对父亲这种乐观的生活态度,很是欣赏。觉得父亲就是伟大,父亲就是了不起,如果我有一天能成为一名地质工作者,也同样会以这种精神去对待艰苦单调的野外的生活。
父亲的晚年也是乐观向上的。父亲虽然是城市中的一员,但退休后没有象城市中人们那样生活,没有老人们的晨练,没有老人们的养鸟养鱼,也没有老人们的下棋打牌,更没有老人们的唱歌跳舞。可是父亲有他自己的生活,他是闲不住的人。有一段时间,不知怎么干起了社区的清洁工作。为了负责区域的清洁,除了按时清洁卫生之外,也还对区域内的卫生进行监督。有时戴上街道办事处发的红袖章,以示在岗工作。又有一段时间,父亲去到车站拣一些啤酒瓶,卖到回收站。虽然觉得父亲这样做,不大符合退休职工的身份,但他如此做也决不是为了卖几个铜板。我也觉得,只要父亲能够注意安全,他只要感觉好,这又有什么哪?老年人,总不能一点不动弹,就权当是一种活动吧。父亲70岁后,上街还要骑自行车,实际上在家无事,上街也就是买点菜。步行也可以去的。但父亲不愿离开自行车。到后来,单位里的同事几次告诉我妹,父亲曾在街上骑车摔到。尽管没出事,父亲自己也不曾提起。当我们知道后,劝说父亲不要再骑车了。父亲说:“趁我还能骑就不骑了,一放下就再也不能骑了”。父亲说的有道理。但毕竟还得面对现实。父亲一直不服老,一直也没有老,即使在行动已有困难情形下,还提着马扎到街上去。
九
父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却保留着浓浓的家乡的乡土文化和家族文化的意识。和父亲晚年生活在一起时间较多的二十几年中,也受到了或多或少的一些影响。童年和少年时,只有母亲讲的故事、农谚记在心中。如“老狐狸过河”之类的鬼怪传说,关于认识月亮的谚语“初二小三,月亮透尖,二十八、二十九,月亮出来扭一扭”,如带有迷信色彩的活动,当天上下冰雹时,将菜刀扔到院子里就可制止等。当父亲退休之后,我在星期天或节日期间能够和父亲偶尔聊天。父亲会将家乡的一些传说片片断断的给我讲一点,尽管不完整,也使得我对家乡“儒山”这个名称有着崇敬之感,也带有几分神秘奥妙的好奇。父亲说,曹操当年就生活在家乡一带,有个村名因曹操饮马而得”曹公泉“。曹植曾在本村的儒山上读过书,本村曾留存过曹操书写的对联,后来遗失了。家乡的某处因似凤凰展翅而得名“凤凰山”等等。父亲对这些虽未能讲出来龙去脉,我也未曾能去考察,但仅此已使我产生并永存着一些对家乡美好的印象。到如今,我之所以向往着家乡,大概就是因为受这些影响的缘故吧。父亲偶尔讲起家族的情况,能把族谱“辈序歌”说给我们听,但具体是哪些字,父亲是说不大准的。父亲虽然有这样的意识,但却没有在我们这一代沿用,特别对我的改名未曾干涉。他既有传统的意识,又有现代的开放:既向下一代传播,有容许下一代的接受自愿。是后来,从长兄那里得到了“辈序歌”的文字。这才真正明白了父亲述说的二十字:“连桂庆秋光,中庭满世香。瀛高多子步,新喜焕伦常。”从我知道的,祖父排庆名积,父亲排秋名宽。到我辈应排“光”字,但却未用。到后来,听长兄告知,在族谱上我们兄弟四人名字为“政通人和”。再下一代应取“中”字。虽然父亲有孙子三人,但也未用此字正式用以名字。这就是我的父亲,这就是他特有的品格。
十
父亲从儒山走出来,从农田里走出来,在外几十年,他时时眷恋着故土。父亲和母亲一直有落叶归根的人生安排。自从长兄成家之时起,就开始了父母长远的计划。长兄通过家乡亲戚介绍,结识了大嫂。从部队退伍直接回到了邯郸。大姐又是通过家乡亲友帮忙,从邯郸物色到了姐夫。父母就这样计划着,孩子们大一个,就回老家一个。待父亲退休了,他们便一同回去。没料到,由于我的原因,没有按照父母的计划去落实,——从家乡介绍了一个没有谈成,——同本地人结婚成家,尔后的两弟一妹均就留在了张家口。母亲的早逝,不知此情,母亲的早逝,也来不及实现父母的共同计划。而父亲,对子女们改变了他的初衷,并没有生气,也没有提任何意见,而是顺应自然的发展。但这并没有改变回故里的打算。但现实的生活,又不是一切都能如愿以偿。父亲到了晚年,在张家口已经适应,并有单位和在张的子女的照顾,回到故里的愿望与实现越来越远,“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出来”。我想,父亲虽未读过这些诗句,但他会有这种亲身的感受。因此,父亲并未坚持回归故里生活。
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 。人的老,人的死,是同样的。到了一定年龄,人们大概不忌讳说“死”的事了,且要安排“死”的事了。那是1985年,长兄依父亲之言,按照家乡的习惯,在以曾祖父为祖坟的墓地,zhou(机内无此字)好了墓。人,是“视死如归”的。特别像父亲这样的工作在他乡的人,像他这样思念故乡、眷恋故土的人,像他这样知道自己已不能再在家乡生活的人,只好选择如此的安排。
父亲老了。父亲突然变老了。头年秋季,还提着马扎在街上转,而过了一个不便出来的冬季之后,便难以出门了。由叔父和长兄陪伴一段之后,便商定将父亲送回邯郸——也算是回到了故乡,去渡过眼看着有限的残生。父亲回去了。那里有长兄、大姐,那里有侄儿侄女,外甥和外甥女,那里有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可是,留给父亲的这样的岁月太短暂了!2000年初,父亲已经病重,生活已难以自理,且有一定的危险。三月一日至六日,我同三弟去邯郸中医院急诊室看望父亲。此时的父亲,已是时而清楚时而糊涂了。此时孩儿的心情异常沉痛,但又无可奈何。为了减少父亲的病痛,创造一个方便的医疗条件,兄弟们商定将父亲送到邯郸市一家具有医疗资格的养老院。我和三弟陪同父亲在医院过了五个昼夜之后,父亲在清醒时说:“你们上班去吧,不要影响了工作”。当我们告诉父亲真要走时,父亲又是一脸的迷茫。没想到,这竟是我们父子最后相见。
十一
噩耗传来,即与弟弟妹妹们商量,分批赶回。当晚三弟携媳与妹回,第二天,将母亲骨灰盒从殡仪馆取出,由小弟乘夜车带回。我新接任了的企业行政工作 ,年初正忙着整顿调整,当把最要紧的事情做了安排,才在五日晚乘车离张。经石家庄换车到邯。又乘汽车到武安,又换汽车到村,时已11点半左右。沿途漫天大雪,汽车不好走,下车后,踏着深深的积雪走向村中。白雪皑皑,好似为我准备的给父亲穿孝的孝衣;大风阵阵,好似为父亲的离逝嚎啕。此刻,孩儿带着一颗悲哀的心、一颗沉痛的心、一颗急切的心、一颗疲惫的心,赶回这永久不能忘记的地方、为父亲来送行。村里的喇叭播出的哀乐,随着风阵阵送入耳中。进了村不远 ,便有不相识的一个亲友迎住。当他领着我步入张氏祠堂后,见到哥姐都在为父亲守灵。我心里难过啊!孩儿不能为父亲尽孝,未能为您送终!当在父亲遗像前跪下的瞬间,脑海里是一片空白,犹如拍摄到的千姿百态景物的底片曝光一样,刹那间一切都化为乌有,仿佛到了一个别的世界。
雪在纷纷扬扬的漂着,风在不紧不慢的刮着,哀乐在白雪覆盖的山村上空徘徊,在儒山脚下回荡。它诉说着父亲如何在这里诞生,又如何在这里成长;它诉说着父亲如何离开这里,又在几十年的接近流徒生活中对这里的怀念。哀乐声声,是父亲将漂泊几十年的情况向乡亲的汇报,是父亲向养育之恩的父老表达的感谢;这是父亲对奔向一个新世界奏出的畅想曲,是父亲告别这个世界最后一次对故乡的赞歌。哀乐声声,儒山,为父亲眷恋故土的归来而肃立,参天古树,为父亲怀念家乡落叶归根而默哀;它在拨动着村里老年人忆起尘旧往事的心弦,它在启迪着年轻一代走出山村的美好遐想!晚饭时分,雪在继续飘,风在继续刮,乐声更加悲哀。父亲的电影告别晚会由雪代替了,但最后一晚向乡亲们告别的焰火却未能阻挡。爆竹再次划破了夜晚乡村的宁静。鞭炮与之遥相呼应,似是父亲在远处大声的向乡亲父老们呼唤,又似在近处与父老乡亲们急语告别。焰火腾空,将雪罩的山村辉映的更加五彩缤纷,这是父亲生命火花的最后一次燃烧,是父亲魂归故里的心花怒放。平静了,一切都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我和兄弟们守护着父亲的灵位,陪伴父亲渡过最后一个夜晚,最后一次倾听父亲的嘱咐。
七日早晨,雪停了,风停了。待我们将祠堂院内的雪清扫之后,“上祭”的亲友们陆续来了,他们向父亲作了最后一次告别。午饭后,按照家乡的习俗,举行送葬仪式。我们分别抱着父母的骨灰,出祠堂向村西经路口往南出村,向所有的乡亲们告别,最后走一遍父母曾脚踏的热土,往东南方向的墓地而去。入葬了,将父母的骨灰依次送入墓穴。最后的告别了,我的父亲,最后的告别了我的母亲,母亲的骨灰虽然已26年了,但曾在我身边。现在也要随同父亲去了。我们一一进入墓穴,看了看安放的情况,最后的依次抚摩了骨灰盒。入土为安。父母啊,您安息吧!故乡的土地上,又增加了一个坟丘。它将永远的停留在这里,也最终将消失在这里。而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永远在我心中。
我为父亲默默的祝颂:
勤劳俭朴谋家计,携家带口不远千里走异地;
正直坚强度一生,披肝沥胆已近百年归故乡。
我为母亲默默的祝颂:
平凡群众,操持繁重家务,景象犹在
伟大母亲,哺育诸多儿女,恩情永存
十二
雪又一次为父亲送来了素装,风又一次为父亲奏起了挽歌。
三年来,父亲一次又一次地来到我的梦中。是对孩儿放心不下的关怀,还是对孩儿未能对父亲尽孝的责备?不论是父亲的关怀,还是父亲的责备,孩儿都欣喜若狂。父亲虽然走了,但仍在我的身旁,白天父亲在我的脑海,夜晚父亲在我的梦乡。
请父亲原谅,一别三年,未能在您的坟前添一把土,献一束花,但对父亲的爱对母亲的爱却深深藏在心头!悲痛的眼泪早已流尽,要流出的即将是血!我不再悲哀,不再伤痛。父母的归宿,是大自然的安排,符合天意,父母的归宿,满足了生前的意愿。父母的品格,如仍在人世,也只能受人欺辱,也只能看着歪风邪气盛行生气,只能看着贪官污吏霸道无奈。。。。因此,父母的归宿,是对尘世的超脱,是对自己的彻底解放。如果冥府还存在的话,如果主持冥府工作的是个正义者的话,请父母在天之灵向他禀报:把去往十八层地狱的通路加宽,免的贪官污吏们走得不畅,继续危害人世;请父母向他禀报:在去往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地方,要派员严格把关,不要将披着马列毛外衣的鬼轻易放行,以免惊扰先哲,保留住圣洁的一方。决不能让贪官污吏们活着和死了都在玷污共产党人的形象,决不能让贪官污吏们死活都在扭曲共产主义的理想。尊敬的父母,不是不孝儿孩儿给父母出些难题,而是孩儿依照父母的遗传给我的品质,为了活着的死去的,为了世上的冥间的,都能公正、平等、洁净、美好,孩儿不得不央求父母再付辛劳。
我站在塞北的高山之颠,遥望群山峻岭,仿佛那里仍有父亲的身影;我站在长城的峰火台上,了望燕赵大地,努力寻找父亲留下的足迹。我站在太平山下,伫立清水河旁,面对着这座城市,心系着遥远的故乡,我向父亲、向母亲将我给父亲的一首歌颂唱:
图谋家计离故乡,几十年间奔波忙。
默默无闻献地质,锅碗瓢盆奏交响。
勤劳俭朴铸意志,正直刚强挺胸膛。
有益子女留燕山,无愧父老报太行。
让这歌唱响辽阔的草原,让这首歌铭刻古老的长城,让这歌流向父亲踏过的深山老林,飘洒父亲住过的无名营地,我要通过时间隧道,把这歌声送到父亲的身旁!
父亲在世人中是平凡的,在儿子的心中是伟大的;父亲在世人中像流星闪过,在儿子心中是太阳那样永恒。父亲给子女的爱,别人看来不足挂齿,儿子看来终身难报。从古至今,世人崇敬母爱,孩儿深以为然。然而在阴盛阳衰的年代,孩儿要倍崇父爱。父亲在祖父面前总在自责是一个不孝的儿子,但父亲在儿子面前,您永远是一个伟大的父亲!
父爱是永恒的,父亲是永恒的。我的父亲是永恒的,父亲永远在我的心中!
不孝之子 向东 泣敬
***************************************************
敬爱的母亲:
一九二三年十月三十日(农历九月二十一日)生于河北武安马会村一个贫农家庭。一九三七年和父亲结婚到本县儒山村。一九五二年随父亲到沙河县,五五年到张市下花园。
母亲忠厚勤劳俭朴,对我们关怀备至。由于家务重身体多病,一九七五年初患右肺癌,曾在区、市及天津医院治疗无效,不幸于十一月十八日(农历十月十六日)十九时三十分逝世。终年五十三岁。
我们为母亲默默的祝颂:
平凡群众,操持繁重家务,景象犹在
伟大母亲,哺育诸多儿女,恩情永存
我们永远悼念母亲!敬爱的母亲,您安息吧!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农历癸未十二月初九)
父亲三周年祭 重录
二OO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注:此文由三弟前去祭扫父母之墓时带回,后由四弟润色录入打印,在封页了插入一副由6只花的图案,这6只花象征着兄妹6人永远怀念着我们的父亲、母亲。
2004年元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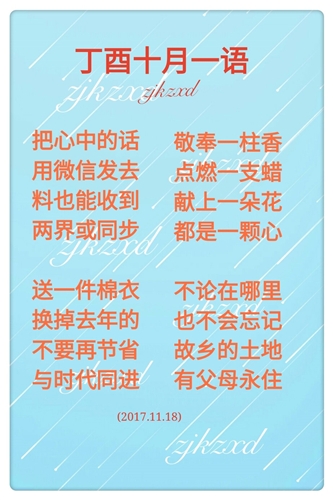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