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文艺兵泱泱大舞台
1943年,孙烈找到部队,成为青年学习班里的一员。为了把自己锻炼得更有革命胆量,孙烈和她的同伴们用了许多方法。
首先竟然是从独自走黑屋子开始。“经过这样一两次大胆的锻练之后,我就再也不怕黑了。后来到五桂山根据地要站岗,我就专门申请到山脚下站岗,晚上山里黑得很,还有不知名的鸟发出‘咕、咕、咕’的叫声,不远处的村子里还有狗吠。”但这些对孙烈来说都已经不算什么了。随后她成了抗日义勇大队宣传队年纪最小的成员,在那里她锻炼自己编剧本、写歌曲、唱革命歌,成了最活跃的宣传兵之一。
1944年1月3日,抗日义勇大队在长江崧埔村成立,四面八方的村民都赶来参加成立大会,新成立的宣传队也要开始第一次公开演出,孙烈和她的小姐妹们一共三人,现场为大家演唱了一首《中国不会亡》。第一次上台的孙烈一点都不怯场,仿佛全身有使不完的劲。
1944年,在翠亨村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会上,当时是珠江纵队第一支队流星队成员的孙烈参演了部队自编的话剧《精神不死》。“剧本主要讲孙先生临终前的一段生活,讲孙先生联俄合共抗日的故事,我当时演孙夫人。演出进行了几十分钟,表演完后远道而来的孙中山亲妹妹现场发表了演说。群众的反响也非常热烈。”
作为游击部队的宣传队,流星队的宣传任务更多集中在对战事的宣传上,有时部队第一天打了胜战,第二天宣传队就把胜利的故事编进演出节目中。有时,为了配合部队,宣传还要到群众中去做动员工作。有一次为了发动当地群众参加抗日,孙烈与几个宣传队的战友来到了当时仍在日军控制下的南朗左步村,虽然家里人就住在这里,但为了不暴露身份,孙烈和战友们只好躲在离家只有十几米远的一个小阁楼上。“我们白天天一亮就躲在屋顶天台,那里有一棵小树,我们就躲在下面。”当时正是九月份,太阳非常毒,上面烤着下面蒸着,宣传队战士们却要在上面一直呆到天黑。“我们就那样坐着,不能说话,也不能发出太大的声响,大家有时候会看书打发时间。天黑后,我们就要马上出动到邻近的几个村子去开展工作,鼓动他们参加抗日战争。”这样昼伏夜出的宣传活动进行了三天,一天三餐都由家里人送到小树下吃。
行军打仗的生活非常艰苦,游击战士们过着动荡的生活,经常天空做被地当床,吃了上顿没下顿,半夜一两点起来吃完饭后,马上行军赶路是常有的事。“有时候我们就在山里睡,冬天大约十一二月份的时候,我也只能盖一张薄薄的床单。早上起来,山里的露水把床单都浸透了。那时仗着年轻,还不觉得对身体会有影响,结果那个时候就染上了很重的风湿。”
有一次,孙烈因为风湿痛整个腰弯得像张弓,要借用树丫做的拐杖才能走路。病痛折磨着她,她的情况越来越糟糕。“我记得是一个小勤务兵带我去翠亨村杨伯母家。”在这个温暖的革命家庭里,孙烈度过了战争年代,难得拥有的安稳而宁静的三天。“每天杨伯母都会用草药煲的汤水给我冲洗关节,冲洗了几次之后我的关节就没有那么痛了。”
孙烈说,战士们每顿饭只有二两口粮,偶尔会有几条咸菜、几条小鱼已经是了不起的盛宴了。但战士们情绪乐观,有空闲的时候讲笑话、对歌,气氛活跃。
《我不能把枪放下》这首歌成了部队里最流行的战斗歌曲之一。虽然艰苦,革命者的情怀却依然浪漫,战斗的间隙,大家经常聚在一起又说又笑,或是相互拉歌,
“我们也唱情歌,像《教我如何不想她》、《夜光曲》,都是当时经常唱的歌。”
这时,孙烈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革命浪漫激情的战争年代,哼唱起那首熟悉的歌曲——“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月光恋爱着海洋,海洋恋爱着月光。啊!这蜜般也似的银夜,教我如何不想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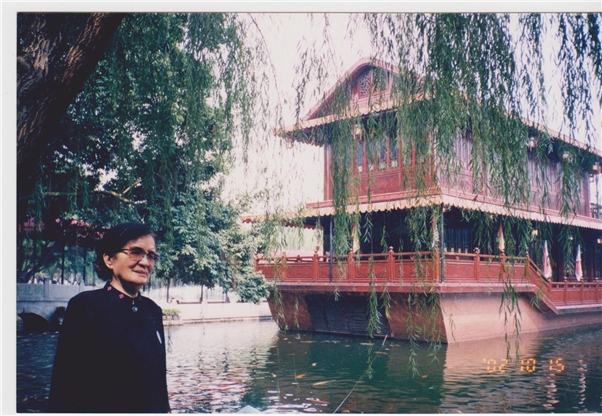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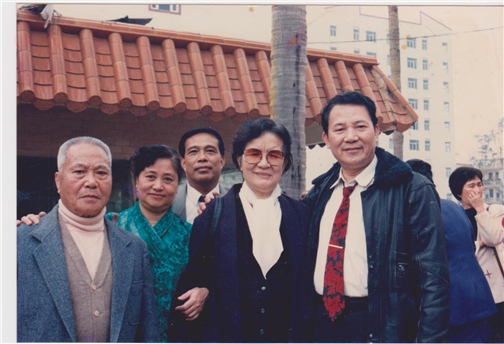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