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评论家秦兆阳先生纪念馆
天堂纪念馆:http://www.5201000.com/TT405168321
本馆由[
133*****520
]创建于2012年08月22日
发布时间:2012-08-22 18:04:11
发布人:
133*****520
(一)
12月的山风透着寒意。看着满山起伏的苍茫松涛,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秦兆阳的一句诗:“参天树为什么要深深扎根,是为了繁茂它绿色的生命。”不过,少年秦兆阳在白羊山的怀抱中勤奋读书时,大概也未想到有朝一日自己的名字竟会镌刻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
湾子里有一个小池塘,牛儿在塘边悠闲地吃着草。我向70多岁的张春华打听秦兆阳的故居,可巧她正是秦兆阳的侄媳。张春华指着临塘的两层楼房告诉我,秦兆阳当年的故居就在这里。20世纪70年代,房子因年久失修,几近坍塌,他们只好拆掉,盖起了现在的楼房。
秦兆阳幼时在父亲执教的私塾读书,12岁时到汉口求学,1934年考入湖北武昌乡村师范,毕业后在黄州中心小学任教,并开始了他的诗歌和漫画创作。1938年,青年秦兆阳怀着满腔热血,告别了家乡,奔向革命圣地延安。之后几十年,秦兆阳曾有几次来湖北,1985年他思乡情切,带病来汉参加黄鹤楼笔会,并感慨赋诗:“四十余年风月,八千里路云烟。归来双鬓皤然,今夕故乡大变。”但由于种种原因,他只在1954年回过一次枣树店。张春华至今还记得,那年秦兆阳进村时坐的是两轮推车。
对于秦兆阳的生平事迹,张春华是知道一些的,老伴秦波成常向她谈起这位叔叔。然而在她看来,自家并没有沾上多少名人的光:家里过的日子还有些穷,年过古稀的老伴仍每天挑着剃头担子穿街走巷,儿子则在家种田。张春华说:“大文学家又咋了,可没给我们留下任何东西!”
(二)
身为作家和评论家的秦兆阳在物质上是清贫的。但他78年的生命中,却留下了太多值得后人评说的东西。
秦兆阳一生著述甚丰,代表作品有《女儿的信》、《洁白的风帆》、《回首当年》、《在田野上,前进!》、《大地》等大量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以及《论概念化公式化》、《文学探路集》等论文集,诗歌、散文创作也颇有成就。
提起秦兆阳,人们无法忘记20世纪50年代一大批顶梁柱式的作家的成名作,都是在他当时主持的《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以至于中国文坛长期尊崇秦兆阳式的编辑,认为一名出色的编辑应以培养作家、出版好作品为最高目标。
1956年,秦兆阳发表了著名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对50年代以来的文艺政策所体现的越来越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提出质疑和反思,在文艺界产生重大影响。他认为在坚持追求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这一现实主义的总原则的前提下,没有必要再对各种“现实主义”作时代的划分。秦兆阳因此受到批判,说他发表这篇文章目的在于暴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这和他帮助修改、发表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一事,成为他被打为“大右派”的两大罪状。秦兆阳因而在文坛消失了长达22年。
1979年,秦兆阳“右派”改正后,回到北京,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兼《当代》杂志主编。次年,在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召集的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他列举“文化大革命”对文艺界危害最大最烈的事实,鲜明有力地指出揭露“文革”的罪过和拨乱反正,正是人民的希求、时代的需要。多年后,仍有作家撰文回忆,当时秦兆阳以洪亮的、带有浓重黄冈口音的普通话在大会讲台上一板一字地说道:“真正的歌德派,应该是我们,我们,我们!对于党中央新的方针路线,我们是要做真正的歌德派!我们通过批判来歌颂,通过歌颂来批判!我们歌颂三中全会路线之德、拨乱反正之德、实事求是之德、干部和人民不可扑灭的正气之德、民族生机之德……这也就是思想解放!”
这些观点在今天的文化界、知识界已成为平凡的真理,在那个年代却被视为惊世骇俗的言论。秦兆阳当时说出这样的话,该是拿出了何等的勇气!
(三)
秦兆阳的父母都葬在枣树店,墓很简单。1992年,秦兆阳的侄儿秦桂林到北京出差时,表示想代他重新为父母立块碑,秦兆阳却拒绝了。他说:“我是共产党员,不要在农村带这个头。”10年后的今天,秦桂林回忆起这件事,仍不由感慨:“叔叔太‘马列’了。”
“我是共产党员”,这是几十年来一直激励秦兆阳的心声。当初他被蒙冤受屈时,更使他痛苦的还不在于戴上右派的帽子,而在于被取消党籍。这令他感觉到自己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似乎心被摘掉了,灵魂无依了!即使在“脱帽”后,他想到的仍是何时能重新入党。
秦兆阳曾自嘲是一个“板大先生”,说自己从小较真、认死理,参加革命后,共产党又培养了他认真的性格。其实秦兆阳的“呆气”,正体现了一种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追求。这使他的人生因背负太多的历史责任感而显得格外沉重,却也成为他不折不挠、战胜困难的精神动力。在他的遗作《最后的歌》中,就作出了一段精彩的总结:“在魂梦中我独自旅行在祖国的大地上,询问追求想找到一个人生的答案:为什么我这一生极少哈哈大笑,而痛苦有时也是感动的眼泪却流了许多许多……在我苏醒的时候,一个不是答案的答案,却涌现在我的心头:毕竟,你是笑在最后,虽然是带点苦涩的,当然也是庆幸的微笑。”
50多岁的秦桂林现住在回龙山镇上。他曾当过回龙机修厂厂长,后来又一度把石制品加工抓得有声有色,在镇上也算是个小有名气的人物,当地人都亲热地叫他“苗子”。他对秦兆阳是非常敬仰的。在他家里,他小心翼翼地摊开一幅秦兆阳亲笔绘就的国画给我们看,并讲述了和叔叔来往中的一些故事。
秦桂林之父是秦兆阳的堂兄,战乱前住在武汉。秦兆阳少时在汉求学时曾寄住他家,受到资助。秦兆阳成名后并未忘记堂兄的深厚情谊,每月都会寄来10元钱,一直持续到1957年前。那时秦桂林就很崇拜这位闻名已久的叔叔了,经常写信给他,不会写的字就空着,为此没少挨叔叔的骂。但直到1967年秦兆阳到黄石去探望胞弟秦会涛,秦桂林才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见到叔叔。只是他没想到,遭受许多磨难的叔叔竟会看起来这么年轻,这么乐观。那几天,秦桂林关在房里,跟叔叔学了几天的围棋,这成为他记忆中永不褪色的一个片段。
(四)
秦兆阳只是从团风走出的众多名人中的一个。包惠僧、林育南、张浩、地质学家李四光、哲学家熊十力、经济学家王亚南、思想家殷海光等也诞生于此。大别山南麓这方并不富裕的土地,何以能孕育如此多的杰出人才?是重视教育的传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还是当地人聪明勤奋的个性使然?团风人自己也未得出明确的答案。
或许团风人的血液里真有着奋发的因子。走在县城里,规划有序的政治文化中心区域、初具规模的招商工业园、热闹着沸腾着的老城区,都令你深深感受到团风人踔厉风发的精神面貌。据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童春珍介绍,建县6年以来,团风的年财政收入已从最初的2000万元跃升至8000万元,整整翻了几番。今年起,该县又加大了招商引资的力度。她说,团风县拥有如此丰厚的文化名人资源,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但以前发掘利用还不够。今后,他们将把这作为对外宣传、招商引资的一块金字招牌。
离开团风前,我再次来到枣树店。秦兆阳故居前有一株枣树,据说是秦兆阳还在村里时就有了的。不知哪年突如其来的风雨使它倒在了池塘中,却仍奋力地向上生长,形成一幕极为奇特的景象。几十年过去了,它竟枝繁叶茂,在冬日的萧瑟里透出生命厚重的红。
- 上一篇:著名作家评论家秦兆阳先生传略
- 下一篇:秦兆阳先生印象 作者:杨爱伦
到过这里的访客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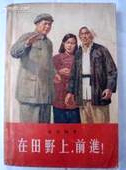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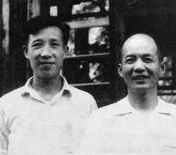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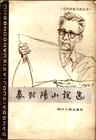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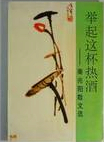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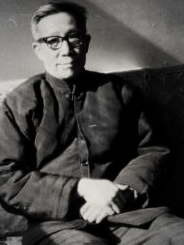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