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阳和他父母的回忆,平民歌手的魅力
“是不是?”——这是她的无论疑问句还是陈述句中的惯用句尾。1993年夏天一个微阴而闷热的下午,我在她二炮文工团的小家里听她对自己作盖棺之评:“我从小依赖父母,上学依赖老师,我的性格就是这样,胆小,依赖性强,是不是?”
一般而言,女孩子大都有些胆小和依赖人,至少表面如此。“弱不禁风”、“小鸟依人”之类性格表象,似乎是可爱少女的天然禀赋,借以刺激大男子的保护欲,直到她们成为少妇大婶时,才毕露出胆大包天剽悍泼辣的原形。可见示弱于人是一种克故制胜的聪明策略。但也不能否定,世上真有死不改悔的懦弱女性,李丹阳即其例。“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化合为李丹阳骨肉的是西蜀盆地清柔软滑的古井水,致使她比喝高钙自来水长大的同龄女儿更多几分懦弱。她的懦弱性格部分来自正直而严厉的父亲,多年的军旅生涯把他的挚爱煅造为兵营式的纪律。对传统的恪守使李家三千金最终成为传统文化的理想作品——诚实、忠厚、温驯听话,稍有些压抑内向。
迄今为止,她向之索取与付出爱的最大目标,仍是那个处于《死水微澜》发生地的家。她爱父母,他们的疼爱与严厉使她的童年充满回味无穷的温馨记忆;她爱两个姐姐,在争夺父母青睐的持久战中她们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二十年后回顾那温倩脉脉的战争,尚余一丝未能挥发净尽的小女儿醋意:“大姐是头生子,最受优待,每天放学回家都吃一个鸡蛋,所以现在长得很胖。二姐聪明伶俐,善讨父母欢心,厂里人都叫她‘洋葱头’。只有我,老实憨厚,一点话都没有,从不敢主动跟大人说话。”
这种早年罹患的社交恐惧症,成为她将来对友情与爱情的追求中巨大的障碍。尽管在成名后随着环境对名人的趋附而逐渐缓解,但其流毒足以使她在繁杂的人际交往中,因灵魂的紧张而做不到真正潇洒自如。“是不是?”这个惶惑的口头禅,可以让任何一个公鸭嗓子平添成为她声乐导师兼人生导师的信心和勇气。
二、差一点成了三流武师
个人的一生与人类历史的规律大抵相仿,总是企图进入某个房间却敲错了门,于是在一连串偶然的推拥下或落茵席,或入粪沼。按照退伍军人父亲的设计,性格柔弱细腻的李丹阳本应成为韦小宝式的混世大侠,用注定练不成的花拳绣腿混迹江湖,从而为中华武林平添一个喜剧人物。可惜她至今悟不到结局的幽默和悲剧性质,反而向我炫耀读小学时其腰腿是如何柔韧利落,因武艺如何出众而连任班体育委员,又如何为后来投师未遇而遗憾。当时我攥着一把冷汗想,倘若没有命运的宽厚,我们今天就不得不目睹一幅林黛玉打沙袋的滑稽而酸楚的惨景。
这时命中注定的指点迷津者降临了。一个平凡的中学音乐老师,姓夏。他及时出现的意义,在于阻止了一颗明日之星向武林沙坑的急速坠落,以此成就了自己的半生和学生的一生。我们大多数人终生记得和感激的人,多半是些小人物,据说朱德终生不渝的朋友就是一个马夫。小人物施惠于人多想不到索取回扣,而大人物滴水之施往往期待别人涌泉相报。那时的李丹阳不过是个贫穷且不出众的中学生,看不出将来有什么出息,只好白白享受别人的好意。“我很幸运,一生中遇上过几位好老师,”说这话时她假装看着窗外以掩饰激动。在她的描述中夏老师是个武训式的人物,教师的奉献精神几达痴愚程度。她说夏老师是个不会做家务的男人,有次演出前她因病失声,急得夏老师生平第一次学着熬中药,忙碌了半天终于把药罐打翻在地,此事使老师在学生心目中无所不能的超人形象随药罐破裂一朝解体。
“没有夏老师,我可能不会走上音乐这条路。”大凡一个教师能有这样的评语就足以瞑目了。需知今日之中国,盗窃他人花木以市高价,时不时还凑着人多的场合高唱一曲园丁之歌自我标榜的“园丁”并非鲜见。由此我对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夏老师感佩不已,也在不攀附名家以提升自己的李丹阳身上,看到中国歌星的灵魂还可拯救的一线希望。
三、与自己作战的丑小鸭
鉴于“演员”这个旨在把一切精神的东西表象化的职业,李丹阳像所有演员一样不擅长逻辑严密的思辨,偶尔迸发的哲理性思维火花犹如夜空流星,突兀而来又突兀而逝。例如在一次闲聊中,她毫无先兆地冒出一声沉重的浩叹:“唉!我是个充满矛盾的人,彻头彻尾地矛盾,是不是?”
倘若没有十一年的相识垫底,这话也许会被理解为“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卖弄,演员常弄不清台上台下的区别。但这次她是有感而发,因为不久前她刚刚详细地对我谈了一段漫长的经历,时间是1982年至1989年,地点是终年雾雨迷蒙的山城重庆。
1982年初秋,是川西坝子上又一轮收获季节。芳龄十七的李丹阳告别父母桑梓,到川东缙云山麓那座四季滴翠的校园去圆她的大学梦,从此步入充满烦恼、孤独和兴奋憧憬的少女花季。 ˉ
那时的李丹阳是一只不折不扣的丑小鸭。良好的声乐潜质被技术上的一张白纸包裹得严严实实,入学录取时差点被筛选掉。在新生汇报演出会上,她的演唱像一只病鸭子在呻吟,全系声乐老师无人相中这只五痨七伤的丑鸭子,只好作为“买一送一”的搭配硬派给一位年轻资浅的老师。十一年后她在3000公里外的北京仍为之伤心:“我敢说,当时谁也不认为我会有什么出息。”
大学第一学期是她的炼狱。大学对一个既没有专业知识也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十七岁少女来说,不像天堂而像个屠宰场。乐理、钢琴、视唱等一大堆陌生课程,衣食住行难以自理加上某些睥睨不屑的白眼仁,像三把杀气逼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她小脑门上;而同学的博闻强识使她如一只误入天鹅群的野鸭,全部的体验只剩下自卑与失落。此时父母温热的怀抱散发出空前的诱惑力,使她一度想退学回家重温被溺爱的旧梦。那时她绝想不到十年之后音乐系会恭请她回校讲学。世事如轮。
环境的压力在一番肆虐之后往往会显现出正值效应,如同唐僧要成正果必须要历九九八十一劫。祸福相生否极泰来。丹阳身上有股川妹子特具的柔韧生存本能,后来的事实证明非有压力不能激活它。一天晚上在被窝里照例清理了一番泪腺之后,她决定要做几件事情证明鸭子比天鹅漂亮,从此抱着卧薪尝胆的阴暗心理在琴房、图书馆和寝室三个点上,日复一日准确无误地画三角形。第一学年结束,她的各科成绩悄悄上窜;第二学年末,这个全班最小最沉默寡言的小女孩成了三好学生,总评成绩也进入前六名。如同维多利亚式长裙再度走俏一样,这次轮到鸭子走俏了。当年那些白厉厉的眼球一齐转青,又来争当她的伯乐。
1986年她二十一岁的生命到达第一个波峰,随之又很快跌落进比1982年更低的波谷。这年她毕业,顺利分配到重庆市歌舞团,并经过区、市、省“三蒸三煮”的选拔,到北京参加了“孔雀杯”(由文化部和国家民委主办的声乐比赛)和CCTV第二届青年歌手大奖赛,并获此生第一个全国性比赛奖——银屏奖。正当她“踏花归来马蹄轻”、为浮云般的声名陶醉时,黯淡的日子拉开了帷幕。
她命相属蛇,据说属蛇者感情丰富但外表冷漠,与初交易受排斥。当她走出校门开始其社会人生的头三年,命相似乎一直在冥冥中支配着她的际遇。这是一个关于孤立无助的女人在一连串冷遇、天灾、谣言与嫉妒中挣扎的悲剧故事,一个自身消化不良的人却成为别人的消食健胃丸的喜剧故事,一个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频频发生的、毫无新鲜的老套故事。因此笔者不愿为此多费笔墨徒惹人厌。总之在山城求学与谋食的七年,于她性格的定型是个重要时期.一个自卑与自尊激烈冲撞、成功与失败反复交替的战略相持阶段。她以一只绒毛初萌的丑小鸭闯入这个时空,最后作为一只拔光了毛的小天鹅逃之夭夭,完成一次否定至否定的三段式人生论证。
对于她个人的一生来说,这七年抗战的价值在于最终把她造就为一个无休止地与自己作战的斗士。源远流长的自卑感似一架经久耐用的风车,经过一次次的毁灭而愈加坚固;而与生俱来的自尊心亦如固执的唐·吉诃德,历经一次次的挫折而愈益好战。这是一场旷日持久且双方均无获胜希望的战争,因为这双重人格的主人只有一个,无论胜败都将致人难堪:只有自卑的人叫可怜虫,只有自尊的人叫自大狂,而既不自卑亦不自尊的浑人,通常称作“二百五”。因此我不无荒唐地认为,倘没有自卑与自尊的通同作弊,李丹阳大概不会有能力与机会在歌坛上弄出点动静来;亦因此,她该为自身“彻头彻尾地矛盾”庆幸得四脚朝天地打滚儿,而不该叹息怅惘才是。
经过数年秋雨梧桐的面壁困思,她在1989年的某一天灵台清明大彻大悟,发现自己身处臭气熏天的牛圈,既无力清扫又不甘就此闷煞,只好学困顿天竺的菩提达摩,把东方作为唯一逃路。1989年的上京进修,本质上是一次盲目的狼狈逃窜,但这精彩的一窜使致命的环境压力扑了个空,她的命运随华盖西坠再次否极泰来。
四、前面有路但很难走
与八十年代以后成名的所有歌星一样,李丹阳也是通过电视蜕变为新偶像的。自1986年伊始,她越来越多地在CCTV的大奖赛、春节晚会和音乐节目中曝光,借助现代科技的强大媒体溜进千家万户,使电视观众在不知不觉的被动接受与主动选择中,认同和喜欢上她。二十世纪制造名人最大最有效的作坊就是电视,正如香港歌星成名发财的不二法门:出名靠电视,赚钱靠唱片。不信你看,无论多么虚骄佯狂傲气十足的歌星舞星笑星哭星,在电视这个剽悍凶猛趵鸨母面前都会“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挤出娇滴滴羞答答的媚眼。
正是无所不能的电视——这个工业商品经济典型产物——的介入,为社会包装出一大批赝品名人。这些名人浮浅无文愚蠢得惊人,格调低下俗不可耐,但也正因如此很对市民阶层胃口,因为观众可以平视甚至俯视他们从而油然生出些优越和亲切感。即便是狂热的追星者,也难保骨子里埋伏的不是玩宠物的阴险。与此同时,传统的“严肃”艺术由于太过精致复杂,让心灵不够细腻的市民们仰视得很累,甚或因为终于搞不懂而弄出些自卑感来。一物降一物,作为电视台衣食父母的市民阶层一皱眉头,电视就不敢拿父母们给的钱接济那个捞什子“严肃艺术”,城隍庙的判官亦因此就只好眼看鸡脚神们大嚼供果而干咽馋涎。十三年来,昔日自鸣清高双目倒插的“严肃”艺术家由于日渐营养不良而虚火上升,超然出世的优雅矜持已所剩无几,竟也时时在电视这个鸨母面前扮出些半老徐娘的幽怨和残存风韵的卖弄。
当然不是说打上MADE IN TV印记的名人都是赝品,正如《聊斋》上的鬼不都是恶鬼一样。董文华、阎维文、李丹阳等人的成名,证明中国电视并没有为败坏传统文化竭尽了全力。他们是一群在夹缝里求发展的歌星,一方面要忍受高傲的“美声学派”的卑视与嫉妒,另一方面要与通俗歌星争夺听众;既要迎合电视台和市民的审美趣味,又不愿出卖艺术贞操——这就有点像旧时的“清倌人”,为既要笼络住客人又要幸免于被梳弄而绞尽脑汁左右为难。
迄今为止,在夹缝里穿行的李丹阳还是幸运的。民族音乐文化的根深蒂固,加之她对自身实力——包括歌唱技术和知识修养——的一贯注重,使她的民族风格浓郁的歌喉仍能争取到相当的听众。她在艺术和生活之路上走得很艰难但很执拗。她擅于用表象进行理性思考,譬如在与我关于民族唱法前途的辩论中突发奇想:“只有民族唱法能代表中国音乐,如同我李丹阳,皮肤黑一点,如果白一点就不是我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对她选择艺术道路起了决定作用,这中间也包括父母赋予她的恪守传统的道德信条,和功利权衡上的狡黠:“有人劝我改通俗,但现在人们说起李丹阳这个名字,是与我的演唱风格联系起来的。如果唱通俗,风格没有了,李丹阳就死了。”
现在她是个军人,每年要下基层为部队演出几个月,这对一个明星维持知名度不利,但她认为战士对她的喜爱足可弥补这个缺憾。作为一个女人,她渴望有个家,家里有丈夫、一个女儿和一只白色小狗,但至今小姑独处。作为一个歌唱家,她有好多计划——开独唱音乐会,录四川民歌专辑和MTV,演一回歌剧,积累一批曲目……,但至今还未及实施。面对未来,她还有好多路要走。
在她的故事要告一段落的时候,金马车的辚辚轮声正一路响近但不知是否划门而过,水晶鞋已套在脚上但不知找上门的将是王子还是巫师。因此她目前还只能是个灰姑娘,尽管已作好了人主艺术王宫的心理和物质准备。命运是很难逆料的,等待她的也许是公主的水晶冠,也许是泰极否来的又一个三年自然灾害。当然,最大的可能还是像一休小和尚在光头上画个圈,说声:“到这里,就到这里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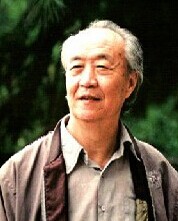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