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评价
杨朔所讲究的“诗意”,包括谋篇布局的精巧、锤词炼字的用心,以及“诗的意境”的营造。其中最重要的,其实是“从一些东鳞西爪的侧影,烘托出当前人类历史的特征”(注:杨溯《东风第一枝?小跋》,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的那种思维和感情方式。如见到盛开的茶花而联想祖国欣欣向荣面貌,以香山红叶寓示历经风霜、到老愈红的革命精神,将劳作的蜜蜂比喻只问贡献、不求报酬的劳动者等等。在杨朔写作的年月,寻常事物,日常生活不具有独立的价值,只有寄寓、或从中发现宏大的意义,才有抒写的价值。杨朔的散文,在贯彻这种从一切事物中提取宏大政治性主题的写作模式时,靠某种带有“个人性”特征的取材,也靠与古典散文建立的联系,给这种已显得相当僵硬的文体增加了一些“弹性”,使观念的表达,不至那么直接、简单。这种“弹性”,在当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因此得到广泛的赞扬。
而在写作的个人想像空间有了更大拓展的80年代中期以后,杨朔散文的“生硬”(注:周立波在《1959-1961散文特写选?序》中,谈到杨朔这个时期散文是,“笔墨简洁,叙述明白,是作者的特长;然而也许因为过于矜持吧,文字上微露人工斧凿的痕迹”。这种矜持和斧凿的生硬,不仅是艺术追求上的“过度”,而且来源于当代这一时期,诗和散文创作在提炼政治意识形态命题,建立一种寓意、象征关系上的紧张心态。)在读者的阅读中便急速凸显,“开头设悬念,卒章显其志”的结构模式,也转而为人们所诟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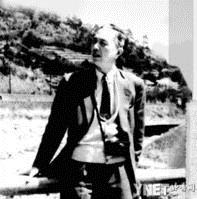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