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0-09-29 14:42:47
发布人:
孝行天下
那些令人肃然起敬的细节
——瞿同祖先生辞世周年祭
刘显刚,为《民主与法制》杂志作
2009年10月3日,是瞿同祖先生辞世一周年的日子。一年以前,当先生谢世的噩耗传来,浮躁的学界在齐声扼腕之余,亦多出了几篇久违了的追思缅怀的文字。一年以后,健忘的人们似乎已记不起先生——他们中的很多人重又开始日复一日地忙碌于时新话题的拣择和学术泡沫的鼓吹了。
予生也晚,得窥真学术的门径更加迟延,因而对于瞿同祖先生,从来只是积存了一份晚生后学的敬重的心意,并无缘亲往拜见。随着先生的谢世,这份深藏心底的敬意终于也失去了尘世的此在的寄托,转而化为一种薪火承续的惋叹与志愿了。一年以后的这个冬天,在四围的寂静中再次重温瞿先生一生的行状与言述,最令笔者动容的,仍旧是那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学人生命的细节。
自学《尚书》:“就是想从难的入手”
先生出生世家,其祖父是晚清重臣瞿鸿禨,因此孩提时代便受到了扎实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清廷退位,鸿禨隐居上海。时同祖先生一岁,亦随迁沪上,陪伴祖父,前后八年。因家学渊源,同祖先生之文史知识远远胜过同龄儿童。祖父教学方法独特,一是让爱孙为无任何标点的《论语》断句;二是自己以朱笔写正楷,命爱孙上面描摹。这种教学方法一直延续到祖父去世为止。经过上述两项基本功训练,九岁的同祖不但练得一手好字,更培养了阅读古代典籍的能力” 。(邸永君:《瞿同祖先生的家学渊源》)
翰林后裔、家学渊源,这些已久为世人所瞩目,然而最能反映瞿同祖先生年少时节进学特质的,可能还是他在中学时自学《尚书》的经历。根据一般的说法,《尚书》之难,居五经之首,甚至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也说它“佶屈聱牙”。那为什么不找一本稍为容易一点的书来自学呢?对于这个问题,瞿同祖先生的回答是“为什么要选《尚书》,那是因为知道它难,自己想学,就从《尚书》入手,就是想从难的入手”。(赵利栋:《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瞿同祖先生访谈录》)
“就是想从难的入手”,这朴实无华的话中不仅仅包含着为学不畏艰困的少年意气,更重要的是,它为瞿同祖先生壮年治学的心境与志趣提供了一种智识养成阶段的心向烛照。
拒绝“被翻译”的诱惑:“尚有自知之明”
一如众知,瞿同祖先生的第一本著作是他在燕京大学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封建社会》。这本书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5年后被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其时,国内多所大学亦将此书列为研读中国社会的重要参考书目。
然而,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实际的学术价值与知识意义,瞿同祖先生本人一直有着清醒的认知。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他之婉拒这本书英文版的翻译出版上。“我写此书时年纪尚轻,才疏学浅,我个人认为20多岁写不出好的书……《中国封建社会》一书,我自己并不满意,自认为是我的著作中最不成熟的一本。我在美时,华盛顿大学拟请人译成英文,已译了一章。但我认为无翻译出书的价值,便婉言谢绝了。可谓尚有自知之明。”(赵利栋:《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瞿同祖先生访谈录》)
这“婉言谢绝”本身不仅仅是一种“自知之明”的呈示,更是一种恬淡放达、不昧虚名的心灵境界。放眼今日之浮躁学界的现实,试问有几人能有如此之气魄拒绝大洋彼岸递来的“被翻译”的诱惑?而且公允地说,作为先生之研究中国社会史的最初尝试,《中国封建社会》一书虽或不尽成熟,但其影响的广布已经说明了其学术史上的意义与价值。
问心无愧:“我比较认真,不乱写书”
在被询及为什么学术成果数量有限时,瞿同祖先生回答说:“我不认为数量的多少是重要的。学术是对知识的求证过程,没有结论的求证是缺少实质意义的。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如果没有新的观点、新的见解、新的方法,没有自己独到的思想,就不要写文,也不要写书。有些人为了出名,愿意多写,写了没有意思。当然,如果条件好,我也可能会有更多一些的成果。写书容易,人人都会写。可写本好书,就不容易了。要写本传世的书,就更难了……所以我一定要自己感到可以通过自己的标准时才写,有点新观点的时候才写,否则就不写。我问心无愧的,就是我比较认真,不乱写书,一定要有值得发表的心得才会写。”
瞿同祖先生的这段话中有两点值得当世学人留意:一,是他对于作文写书的自我省察的标准,是必须要有自己的新的观点、新的见解、新的方法,要有自己的独到的思想、值得发表的心得,否则就不去写;二,是他对于学术“生产”数量与质量的关系的看法,即“不认为数量的多少是重要的”,相对于数量,他更看重的是作品的质量,要写就应该是“好书”,最好是“传世的书”,作为学者,就应该在“不乱写书”的前提下努力写出好书和能够传世的著作。
先生的这一种主张在当世自然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我们早已进入了学术的工业化生产时代,太多的学者已经不仅是著作等身,而且是等好几身的高产“大师”了;太多的学者沉浸在自己所堆砌的文字构件里不能自拔了,他们并且存有太多的出版和诉说的欲望,其间往往又裹挟着职称学术与吃饭学术的钻营与投机。于是,大师的标签漫天飞舞,教授的头衔满街都是,博士的帽子被成批量的生产和复制,规划学术与等级学术也成为国家学术的常态,而每年数以百万计、耗资数十亿的学术作品的工业化组装和生产亦着实为国家学术GDP的成长做出了“贡献”。
只是,浮华终将散去,对于每一次学术文字的发表与出版的意义,历史终会做出公正的审判。在日复一日地陶醉和忙碌于炒作、制造和出版的时候,当世的知识小众们是不是也应该偶或想一想瞿同祖先生的“不乱写书”的自我省察,想一想先生的“写本好书,最好是能够传世的书”的自我砥砺呢?当所有的源于权宜和个人的小得意的文字构件在历史的暗河中疾速消隐的时候,只有真正认真而独到著述才会最终经受住时间之水的冲刷——一如先生那不多的几本书和论文,久远地绽放出夺目的光辉。
未招学生的“博士生导师”
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官方讣告里,瞿同祖先生有一项“博士生导师”的头衔。事实上,先生是新中国第一批获得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的学者,但他从来没有招过学生。个中原因,瞿同祖先生的儿子瞿泽祁后来解释说,是因为父亲年纪大了,精力不济,如果他要收学生,倘若不能够亲自教授指点,他是宁肯不做这件事的。
任事须克其功,育人必收其效,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真正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境界。因为年龄和身体的原因,瞿同祖先生晚岁未能收一二门徒弟子传承学术之衣钵,这本身是一件颇为遗憾的事情,但坚持在精力不济的时候不招学生,这件事本身却正又说明了先生任事的认真与执着,对于这一点,他问心无愧,也为当世之人树立下了一种永堪垂范的标尺和高度。
学风问题:“国内对于抄袭行为的处分太轻”
在生前所接受的最后一次访谈中,先生专意表达了对于学术风气的意见,直言“国内对于抄袭行为的处分太轻”。
“比如有人的书一字不漏的抄了我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二节的内容。《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重印后,一个外地读者发现了,写信告诉我,我通知中华书局,中华书局通知那个出版社,那本书由出版社收回,而那个作者继续在原单位供职。要在国外,此人马上开除,不但本单位开除,而且美国所有单位都不要他。国外发生了这样的事,一辈子都完了,而在中国却无所谓。后来社科院有人来看我,说要允许人犯错误。可这是关系到学风的问题。为什么外国学风那么好,就是一发现就不要他。” (赵利栋:《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瞿同祖先生访谈录》)
学术抄袭行为“在中国却无所谓”,“要允许人犯错误”,这是瞿同祖先生所不能理解的。先生的敏觉与介意并不是什么不允许人犯错误,而是一份对于学术伦理与职业道德的自觉的守护与坚持,因为这是“关系到学风”的大问题,学风不正,则假学术横行而真学术不彰——这显然是不需要复杂的逻辑建构就能得出的简单的道理。
对于学风呵护的迟钝,对于学术抄袭行为的无原则的宽容甚或是纵容,终于引致了中国学术界造假与抄袭的风行;学术伦理的缺失与职业道德的缺位,也使得中国学人在集体上面临着一种诚信危机。那些被曝光的抄袭者,要么矢口否认,要么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动作,很少能够反躬自省,在根本上,这正是因为那些无原则的“要允许人犯错误”的论调所造成的恶劣的学术风气。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每常悲愤于假学术的横行无忌,悲哀于真学术的精神缺失,那么就让我们一起记住瞿同祖先生的叮咛与坚持,从我做起吧!
在被要求对自己一生的治学心得做总结的时候,瞿同祖先生回答说“我一生治学得力于‘勤奋’、‘认真’四字。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的精神,这是我的座右铭”。勤奋认真、一丝不苟,这简简单单、朴实无华的几个字,没有丝毫的浮华,传递出的却是最平易也最深刻的为学为人的道理。
中国社科院青年学者赵利栋说:“瞿同祖不能够算是同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出身就决定了他的不具代表性,使得他有能力不求名利、努力工作,永远不会因为受到一点挫折而走向偏激。”世家之出身固然使得瞿同祖先生更加豁达,但他的不求名利与努力工作,却或者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出身的特异,还因于一种深深镌刻于灵魂中的对于真学术的敬畏和坚持。
关于瞿同祖先生一生行状,署名紫川的作者曾在一篇文字中作了很好的陈述,兹录如下:
“平心而论,瞿先生并不是西人所谓的传奇学者。他不是体制内或学术圈的宗师或学阀,没有一长串的行政、社会和学术头衔;他并不是著作等身的“学术大师”,毕生只有4本书和几篇论文,其中有两本他自认学术价值“不高”,一直不情愿再版;他经历近百年的人生历程,主要学术成果却主要完成在52岁之前;他跨越社会学、历史学、法学和政治学等多个领域,却多半因为这个原因缺少同道,也没有嫡传弟子,他的几代仰慕者几乎都是从著作中知道他的名字。加之,瞿先生虽然家学渊源,名师良友甚多,但他的性格未免太过于平和温顺,并没有太多奇闻佚事、壮怀激烈供后人评头论足或者缅怀。”(紫川:《书生天下事,生前身后名——追记瞿同祖先生》)
不知不觉间,瞿同祖先生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了,时间会冲走生命的记忆,然而,瞿同祖先生的谦和淡泊、认真勤奋、敏觉坚持,以及不以学科自限、敢于突破藩篱而直面问题的治学姿态,都将继续照映在后代的仰慕者与追随者的心中,给予他们坚持下去的勇气和力量,使他们能够擎起真学术的火把,继续行走在那条洗尽铅华也明净澄澈的智识小路上。
是为祭,先生千古!
[作者简介:刘显刚,男,汉族,1982年生,安徽淮南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2006.7)、法理学硕士(2009.7,现为内蒙古农业大学法律系中英双语教学专任教师。]
- 上一篇:瞿同祖先生的家学渊源
- 下一篇:瞿同祖:由博而专由专而通
到过这里的访客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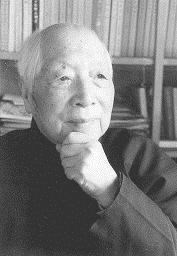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