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父亲夏征农
不能忘却的纪念——忆父亲夏征农
【作者简介】
夏小华 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高级经济师。曾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交通银行总行、广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等工作,现为华夏银行上海分行行长。
1
到今年10月4日,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一年了。去年的冬至前,我们全家齐聚于父亲的灵前,将父亲和离开我们已经整整40年的母亲,合葬在一起。冬天的寒风,阵阵袭来,心情,就如同父亲喜欢的那首晏殊的词所描述的: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鸾无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父亲以105岁辞世,这对普通人而言,已是难以企及的高寿,按照中国民间的说法,算是“喜丧”了。可是我们全家,却仍在心理上难以接受这残酷的现实。一年来,我们像是在寒夜里突然失去了遮挡,在行路中突然失去了路标,心中总是空荡荡的……
这种心情,并不仅仅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也并不仅仅因为他有着100多年传奇般的人生,更不是因为他曾担任过什么职务,在政学两界曾享有崇高的威望,而是因为无论他一生如何坎坷,却总是那么达观,那么充满活力,从不无病呻吟,甚至有病也不呻吟;从不怨天尤人,甚至在个人受到栽赃诬陷时也决不气馁,几十年来,似乎总是保持着一颗年轻的心,并用这样一颗心深深感染了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忽略了他的日渐衰老,甚至忘记了他的高龄,乃至于如今竟无法接受:一个具有如此旺盛精神力量的人,怎么会老去?!
2
父亲漫长的一生,恰逢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激荡年代。父亲从少年时即投身于那时代的激流中,必然使他一生充满了波折,充满了艰辛,充满了生死的考验,充满了精神的淬炼。也许,他那几十年始终如一的旺盛精神力量,及由这种精神力量所体现出的顽强的生命力,恰是来自于那个时代的锻造。他那波澜壮阔的人生,也只是到了他最后几十年,才逐渐地归于平静。而恰恰也就是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使我们子女才不仅仅总是看到他忙碌的背影,而是有机会与他发生更多正面的交流,并进而对他有了更深的认识,也受到他那强大精神力量更多的感染。
在60岁的时候,父亲作诗:“半是书生半战士,一行政治一行诗”。虽然三十年代,父亲曾在上海文化界做过一些文化工作,嗣后又曾长期从事文化宣传工作,但他却将自己定位于一个“在文化界跑堂”的“书生”,一个用手中的笔与敌人斗争的“战士”。过去古人对士大夫的要求是要有“道德文章”。今以观之,文章做得好不易,始终坚持一种高标准道德也不易,能做好文章又不是“无行文人”,有较高道德,达到“道德文章”要求的,则更为不易。父亲对敌斗争坚决,无论是在敌人的监狱中,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下,还是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他从来是无所畏惧。对同志,他却总是光明磊落,从不玩手段、整人,不要说对与他意见不同的人,即使是对那些曾经为了某些目的打击诬陷过他的人,也往往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但是同时,他又是一个敢于坚持原则的人,对于他不认同的观点,无论当时潮流如何,辩驳批评从不容情,甚至不计个人后果。这种秉性已预示着他在“文革”中不可避免地将遭到噩运。事实上,父亲是“文革”中上海第一批被“打倒”,“文革”后最后一批被“解放”的高级干部之一。
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动荡混乱之中,转眼10年过去了,父亲步入了70岁的高龄。他作诗总结自己的这10年人生:“七十方知六十非,书生意气不趋时;铸成僻性终难改,月夜花阴忆子规。”人已到了“古来稀”的年纪,又在“文革”中被打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刚从狱中出来,正面临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党的党籍要被终结,政治生命似乎已看不到前途之时,他却做如此的总结:因为是个书生,不会趋时逢迎而遭此噩运,但因为这已铸成 “僻性”,故而也决不准备为了改变个人的处境而改变自己,而是仍要像杜鹃啼血般地坚持自己的信念,真是“死不悔改”啊!
1976年10月,“秋风骤起乌云散,雨过天晴,盼得天晴,十月阳春快众心。”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父亲与全国人民一样,生命仿佛突然焕发出了青春,虽然在1976年后的近两年的时间,父亲一直没有被安排工作,但怀抱着新的希望,精神振奋。他与一些老同志,十多年来第一次走出上海,游西湖,登雁荡,看山河,吟新诗,豪气冲天。1978年夏天,在所谓“历史问题”还没有给出最终结论之时,组织上先安排他任复旦大学党委第一书记,1979年初又调任上海市委书记。在此期间,父亲抱着要将“失去的时间夺回来”的心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工作秩序,推动思想解放,贯彻拨乱反正,不顾自己已年届80,日以继夜,拼命工作。80岁时,父亲作“八十抒怀”:“行年八十不痴聋,岁月催人道未穷,历尽‘三灾’成铁骨,尚留余勇正歪风。无知应更勤探索,有口仍当发聩蒙。检点一生聊自慰,毋骄毋谄少盲从。”而就在前一年,父亲在检查身体时,被诊断出患了前列腺癌,但从诗中,却完全看不出他患了所谓的“绝症”。实际上,当医生做出诊断后,曾希望不要告知他本人,怕他像常人一样有精神负担。可是父亲很快就知道了自己的病情,竟生气地说:“有什么可瞒的?难道共产党员还会怕死吗?!”那无所畏惧的气概和完全不受影响的精神状态,给我们做子女的感觉是:根本就没有什么疾病可以将父亲击垮!在父亲患病后的治疗过程中,曾一度使用对癌症常用的“放疗”,但不久就因为父亲感到不适而在他自己坚决的要求下停止。其间父亲一方面坚持服药、自我锻炼和用一名老中医发明的一种“中医西疗”法治疗;另一方面继续坚持工作。一年后,去医院复查,癌症竟奇迹般地消失了!面对父亲这样一种情况,岂能不使人怀疑:父亲难道真是一个“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老人吗?
匆匆又是10年,父亲已年届90。回顾这十年,父亲作诗:“九十开怀”。60“述怀”,70“感怀”,80“抒怀”,到了90却“开怀”,境界日高。诗云:“雨雨风风九十秋,年年月月在追求。文坛试马明知险,逆水行舟不调头。自愧才疏少建树,全凭党性斗寒流。喜看大地百花放,晚节无亏一老牛。”诗中再一次表现出他那作为一名为党的事业奋斗不息的战士的坚强意志和只有年轻人才有的精神活力。而恰恰在这些年,由于他的那种“坚持”,受到了思想界、文化界各种时尚或不时尚的潮流的左右夹攻。
3
记得过去母亲曾评价父亲的性格,说他“大事胆子大,小事胆子小”。什么是“小事”?也就是一些涉及生活上的事。对于这些事,父亲总是非常淡泊。在我们的记忆里,父亲从不关心吃什么,常常是有什么吃什么,家里往往是几样清淡的小菜几年不变,许多菜时常是上一周没吃完,下一周我们去父亲家又被热一热端上桌。父亲且从来不吃什么“人参”、“鹿茸”之类的“补品”,他不相信这些东西;从不关心用什么,一套因为家里实在没什么像样的家具,1978年因工作上需要买的沙发,用到他临终都没有换;从不关心穿什么,除了有一套用于在开大会、见外宾时穿的毛料中山装较好外,其他的衣服不是补了又补就是已洗得发白,而就是这套服装,也是购置了几十年未换;至于公家为了工作配的公车、住房等,他更是从不提任何要求,让他坐什么车就坐什么车,让他住什么房他就住什么房。节约下来的钱,他则毫不吝惜地捐给“老少边穷”地区,为孩子办教育。
为此曾有同志说父亲并没有什么“严于律己”的问题,因为他早已将自己的生命完全融于党的事业之中去了,根本没有什么个人过多的“物欲”,淡泊至如此,也就没有了那种要严格克制自己物欲的“律己”必要。而恰恰由于这个原因,父亲在政治上却又总是“不趋时”的“胆大”。检点他解放后的政治生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正确性”是反右,他却总是“右倾”,乃至于50年代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60年代又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曾保存着一本“文革”时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造反派印制的父亲的“反动言论”摘编,其中有些“黑话”,从当时的背景看,确实出奇的“大胆”。而到了“文革”结束,虽然他是在上海第一批站出来支持“真理标准”讨论,支持“解放思想”,并在1978年恢复工作即发表“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文章,冲破“两个凡是”禁锢的人,但是当为了突出地证明自己是极左的“受害者”,反“左”因而成了思想、文化界某些人的某种“政治正确性”之时,他又被一些曾经的“左派”和“右派”说成了“左王”。尽管如此,父亲即便到了90高龄,却仍然不改他那早已铸成“僻性”的“书生”和“战士”的本色。
4
记得那一年的国庆,全家再次聚首之时,父亲忽然举起了手中的酒杯:“祖国万岁!”父亲是一个感情很少外露的人,乃至于母亲曾说父亲“外冷内热”,因此没有人想到父亲在这样的时候,用这样的祝酒辞,一时全场震撼。但在经过短暂的静默之后,我们的内心都被父亲的祝愿所激动起来:“父亲说祖国万岁!”于是“祖国万岁!”之声此起彼伏。我们忽然明白:无论加之于他头上的是“右派”还是“左王”,在父亲的心中,他那始终如一的坚持是:实事求是,一切为了祖国!
光阴荏苒,不知不觉之间,父亲已到百岁。一天,父亲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让我到家里去。进门上楼,父亲如往常一样,坐在书桌前用纸牌接着“长龙”,神情却是若有所思。见我进来,父亲微笑起来:“我写了一首诗,你看看。”说着从桌上拿起一张纸,上面用铅笔写着:“百岁乐怀:人生百岁亦寻常,乐事无如晚节香。有限余年仍足惜,完成最后一篇章。”从90岁到百岁,从“开怀”又到“乐怀”,10年的年龄增长,在父亲好似又上了一个台阶的登高,境界更为深远。
实际上那几年,父亲的老年性白内障十分严重,已经看不清任何东西了。作为搞了一辈子文字工作的“书生”,这种无法“工作”的状况常使父亲感到难以忍受。作为子女,也为父亲的病而感到揪心。正在束手无策之时,恰巧遇到一位曾经当过医生的朋友,说北京同仁医院开白内障的医生,在国际上都是首屈一指的,开这个刀应无问题,她可以负责联系。这燃起了大家的希望。经再次请求组织,终于获得同意。记得那天将父亲推入手术室前,父亲情绪很好地说:“我很快就会出来。”果真十几分钟后,父亲被推出来了,手术很成功!当医生让父亲看手指测试他的视力时,父亲果断地数着:“1,2,……”兴奋得就像个孩子,从此又恢复了他那“开怀”乃至“乐怀”的情绪。
我曾一直对父亲“百岁乐怀”诗中的“完成最后一篇章”不解,不知他所说的“最后一篇章”究竟指的是什么。为此,尽管我知道父亲认为回忆录往往成了为个人树碑立传,而要讲真话又可能伤害一些人,因此不愿意写,仍试探地问他:还是要将一生的经历记下来。没想到这次他深思了一会儿说:“现在还有人愿意看这种东西吗?”已经年过百岁,他却好像对社会上的事了解得非常清楚,令人惊异。我说:“这是历史,历史由亲历者讲,才更真实。”他思索了一会儿道:“好吧,既然你认为还有点价值,以后你们如有时间,我讲,你们记。”他终于觉得有必要做这件事了,却已感到力不从心。
5
2007年,我们党要召开十七大了,当组织上通知父亲,这次党代会他仍是特邀代表的时候,父亲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当时方尼同志因心脏病复发住院,父亲由于年纪大了,难以每天探望,为了就近照顾,也“陪住”在医院里。父亲告诉我们:虽然一些人生活水平比过去提高了,但是现在还有很多人生活困难;虽然现在经济看起来很繁荣,但是天下并不太平。他认为,关键的问题,还是要解决好教育和“三农”问题。为了参加这次党代会,他已就“三农”问题构思了一篇发言,找时间准备写下来。那段时间,他还要护士帮助他在医院走廊里练习“迈大步”,说现在因为年龄大了步子迈得太小,怕届时跟不上代表们的步伐;他要秘书找来国际歌词曲复印给他,一遍遍地复习,说会上要唱,不能走调……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组织上考虑到他的高龄和身体状况,这次却未同意他赴京参会。通知下来,父亲沉默了。不久,父亲就突然发起了高烧,高烧又演变成肺炎,高烧和肺炎又造成父亲心脏衰竭!
但在医生的精心治疗下,终于高烧退了,肺炎消了;在心跳已降到每分钟40多次,医生又冒险为父亲施行了安装起搏器的手术。手术成功了!一切的一切,似乎预示着父亲又将创造一个生命的奇迹。然而此时,父亲沉疴已久的胆结石突然移动,堵塞了胆总管,身体状况又急转直下!一天,从昏睡中醒来的父亲,看到我们围在他的床前,忽然说:“我的病是不是治不好了?告诉院长,我这么大年纪了,治不好就不要治了,不要浪费国家的钱,如果我这个身体还有用,可以做医学研究,为什么我能活这么大岁数,也许可以研究出点什么,帮助别人延长寿命。”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作为子女,我们从在他身边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却感受到一种平凡得如同空气般的“伟大”。使我们真的无法相信:这样一颗灵魂,怎能离我们而去,怎会消散?这应当是一种永存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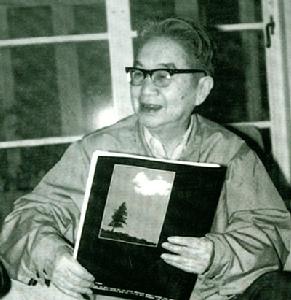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