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鸿业教授自述
寸草报晖暖心头
我出生于中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高勉之,是孙中山先生建立的同盟会的会员,曾任我原籍(江苏徐州)出版的第一家报纸《醒徐日报》的主编。1925年,他因揭露当时徐州的军阀县长贾月壁贪污救灾款项而被贾杀害。当时,我才4岁。母亲张莲修,小学教员,含辛茹苦把我拉扯成人。我的生活和教育得到了我父亲的挚友滕仰支先生的大力支助。
我的童年和青年时期处于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年代,特别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之下,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当我中学毕业时,已经是抗日战争开始后的第二个年头。那时,中国存在着被称为“科工救国”的思潮,意思是说:日本鬼子之所以能欺负我们,原因在于我们科学落后,工业不发达。要想拯救国家,必须走振兴科学和工业的道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并不特别擅长于理工科的我,也同许多青年一样,选择了学工的道路,进入当时已搬迁到重庆的交通大学机械系。1944年春,当我快要毕业时,国民党政府下令征召中央、交通、复旦和重庆这四座大学的应届毕业生,让这些学生充任驻华美军的翻译。那时美国和中国是抗击日本的同盟国。
通过位于重庆的复旦大学专门为这次征召进行的几个星期的英语培训,我随后被分配到昆明炮兵学校,任炮兵战术课程的翻译。一年多以后,在1945年夏,我和100多翻译一起被派遣到美国,据说是为了美军在我国沿海登陆袭击日军之用。到了美国才知道,这批翻译是被用来培训国民党政府的留美空军,而我则被分配到密西西比州的凯丝洛飞机场充任飞机修理翻译。14个月以后,到了1946年秋,翻译任务结束,我进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读书。
这时,抗日战争早已胜利结束,对我说来,“科工救国”已无必要。因此,我改读经济。
从改读经济到取得博士学位,花费了我特别长的时间。这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方面,由理工转入文法科,需要补修许多额外课程。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我完全没有经济来源,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我通过奖学金和充当家庭教师、厨房打杂、餐厅服务员、农场收获工、帮教授改卷子、实验室管理员等取得经济来源。1951年,我完成并通过了经济学博士学位所要求的所有课程和各种考试,只剩下论文写作。按照美国大学的常规,论文写作并不一定要学生住校进行。学生可以离校就业,只要在规定的年份以内呈交论文并获得通过,便能取得学位。我采取了离校写论文的方式。因为,几年的半工半读的生活实在很辛苦,有时因没有钱每天只吃一顿正规伙食,剩下的两顿以方便食品充饥。我想找个正式工作,改善一下经济状况。找到的第一个正式工作是西部地球物理探矿公司的计算员。该公司的业务是寻找石油矿。我的工作很简单,不过是根据给定的公式把勘探仪器得到的数据换算成石油蕴藏量的指标。这样,我便成为石油勘探队的一员,随着勘探队在田野中过着流动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很难使人接触到书本,更读不到什么专业书籍;如果这样生活下去,我不可能完成我的论文。因此,当了三四个月的计算员以后,我便辞职不干,到旧金山另谋新职。
在旧金山,靠着我学工的背景,找到了一份助理工程师的工作。干了一年,虽然经济情况有所改善,但是,论文仍然只字未写。因为,工作一天下来,已经很累,不想再干些什么;另一方面,工程师的生活也不能提供写论文的条件与环境。为了完成论文,我只好再度辞职,到加州大学经济系当了两年助教。助教的收入给我提供了经济来源;更重要的是,它使我易于向知名教授和学者请教并能经常和同行的青年教师进行切磋和交流。这种有利的环境使我在两年的助教生涯中基本上完成了论文初稿。
带着论文初稿,我于1955年回到科罗拉多大学。修改和通过论文占用了约一学期的时间。在取得博士学位的时候,已是1956年初。到了那时,取得学位后是否回国成了必须决定的问题。我总的倾向是回国。但是,已经离国12年了,在长期的远离之后,又怕难于适应国内的环境。因此,关于回国,一直在踌躇,心情经常处于矛盾之中,非常苦恼。
正在此时,密苏里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访问我校,谈到急欲聘请一位商业统计教授。由于我博士学位的辅系(即第二专业)是统计,我的一位老师推荐了我。通过面谈之后,这位院长聘用了我。这样,我想不妨暂过一段教书生活,令人苦恼的回国问题可以拖延一下,再作决定。于是,我成为密苏里大学管理学院的副教授。
教授的物质待遇是令人满意的。我添置了衣物,购买了汽车,一天三顿正规的伙食,穷学生的处境一下子转变成为中等程度的生活。尽管如此,我在精神上却很苦恼。已经快40岁了,成家立业似乎不能再拖。一旦在美国成家,家庭的拖累使回国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情。许多朋友的经历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那时正是朝鲜战争结束不久,中美两国处于没有外交往来的敌对状态。如果留在美国,势必终生为外国人服务,不能为哺育我的祖国做一点哪怕是力所能及的小事。对此,我将终生引以为憾。况且,留在国外,我也未必会有什么成就。在旧金山的唐人街区,当时有一个小街心公园,我经常看到一些退休后的老华侨在公园的草地上晒太阳。我留在美国的归宿也会如此,顶多有一辆汽车和一幢住宅。况且,在当时的美国,种族歧视依然存在。我经常有“二等市民”的感觉;正如一位华侨小姐告诉我的那样,她自己可以说是“一个团体的成员,却永远不属于这个团体”。那种滋味并不好受。考虑到所有这一切,我决定回国。1957年春,我向学校辞了职,经由香港回到祖国,被分派到人民大学经济系教书,一直到现在。以我个人的经历而论,回国的决策是对自己有利的。改革开放后,我曾于1983年、1987年和1992年三次重回美国。前两次分别应科罗拉多大学和国际管理研究院之聘,去两校任客座教授,各讲学一学期。后一次是作为富布赖特学者进行西方经济学的调研工作。旧地重游,不免遇见一些昔日来自大陆的同学和朋友,他们都已退休或接近退休,而正如我过去所预料的那样,物质生活比我优越,一般都有汽车和住宅,对此我固然羡慕。但是,他们却为此而付出了一辈子为外国服务的代价,在这一点上,看来他们也并未取得突出成就。得失相比,回国对我有利。当然有的时候,怀疑自己对祖国所贡献的力量是否能补偿自己从它那里取到的报酬。
总的说来,已属垂暮之年的我,心情是舒畅和愉快的,能够看到中国从一个四分五裂、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转变为独立自主的统一国家,特别是看到香港的回归,消除掉了昔日的奇耻大辱,我的一生已经算是值得了。特别令人振奋的是:我们的国家前途光明,照我看来,只要能维持政治稳定和使人口受到控制,我国的富强一定会实现。然而,我现在也有不安的感觉,甚至是恐惧的感觉。我国目前仍然相对贫穷和落后,而国际上的敌对势力正是想利用这种贫穷和落后,处心积虑,觊觎我国,企图从我国的失误中捞取好处,或重新获得他们失去的天堂。这些都值得忧虑并且必须加以警惕。我此时的心情可以用我的一首打油诗表达出来。现录之如下,以作这篇自述的结束:
龙套吟以明志
落叶归根意未休,甘跑龙套跟旗走。
愿为梨园添春情,不卖色相充名优。
末座有愧冷板凳,寸草报晖暖心头。
老来犹唱满江红,只缘群夷窥神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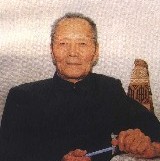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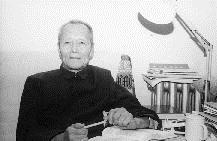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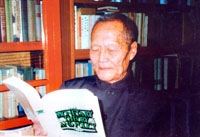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