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者的戒尺---忆恩师罗齐亮 张映碧
师者的戒尺---忆恩师罗齐亮 张映碧
我是在四川自贡长大的,那既是一座抗战中诞生的小城,更有着两千多年井盐历史的古城。
小时候外婆曾给我看过一次手相。外婆是母亲的继母,可给外孙女看起手相来,那个仔细劲儿跟邻家亲生的外婆也无两样。记得一个夏天的晚上,外婆说:小平的命好,日后会走运,还会远行。我母亲当时正低头搓着一盆衣服,她大约并不信手相,但一听女儿要远行,突然抬起来看着我们,表情有些诧异。外婆安慰道:“你莫担心,小平命里多贵人,过不去的门槛都过得去的。那时我刚入了红小兵,听不惯外婆这些四旧,就冲着她喊道:迷信!全是迷信!到如今我还记得母亲制止我的眼神
. . . 许多年过去了,外婆和母亲都去了天上,彼时的红小兵也近知天命,还真地远行去了地球的另一边。不仅如此,几次落难还真的会有某一个贵人突然冒了出来,于是峰回路转,逢凶化吉。的确,自己走到了今天仍然能够一双脚着地,还多亏了好些贵人的帮衬,本文的罗老师便是其中之一。一个人的梦常常是始于青少年时期的一位老师,以至于我无法想象今生今世若是没遇上罗老师,这辈子的路又将是怎样的一个走法?
其实,我从没上过罗老师的课,这拜师的机会多少是了些“文革末班车”的时代特征。许多年后,每次与我的那些高鼻子邻居、同事、朋友聊起中国文革期间发生的事,他们好像总有问不完的问题,我这才意识到为什么那十年放生在遥远的东方的事竟然对这些隔岸观火的洋人有着那样的诱惑。巴尔扎克说:机缘是最伟大的小说家;而中国文革时期的混乱确实错出了西方世界不可能发生的种种机缘,如我父亲与罗老师夫人的不期而遇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1976年毛主席去世前的那个夏天,上面突然来了一道行政命令,我那本来做着刑事法官的父亲只能放下手中未决的凶案,同那些跟他一样中了签的机关干部们临时组队,住到乡下去了。倒也不是城里的干部就不能下乡去插秧、种树、挖水坝,只是下去的方式让我那些高鼻子朋友大惑不解:为什么你父亲会放下他该做的事不做,而要去农村种稻谷?毛要他城里的干部去农村干活,谁又来管城里的事呢?是农夫吗?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们总是无法释怀。西方社会太有序了,除非是打起仗来,比如1942年初夏德国兵快到巴黎了,城里人这才携家带口逃亡去了乡下。而在和平时期,除非你乡下有亲戚,如我们的两位欧洲朋友,他们一到农忙季节都会去乡下打个帮手,两三周而已,绝对不会像我父亲那样,八、九个月住到乡下去一边务农一边干革命。问到这样的事,凭你跟他们怎么解释也是秀才遇到了兵,说不通的。
总之,父亲那年下了乡之后,还在一个五七干校”的什么工作团里当了个什么工作组长,组员之一就有罗老师的夫人李孃孃,一位水利局的财务干部。当父亲得知这位女同志血压很高,根本干不了重活,便叫她该看病看病,该休息休息,并说如果上面查下来自己会替她担着。不曾想,这件小事被李孃孃夫妇记在了心上。父亲回忆说,当时已是家乡教育界名人的罗老师曾陪妻子来家里坐过一个晚上(我当时一定不在家)。罗老师在师范学院教英文,当他得知这家有个女儿在自贡二中读书时,便主动提出我可以每周一次去他家里答疑。然而,我父亲却婉拒了罗老师的好意。法官先生不是没有顾虑:罗老师的父亲解放前是自贡市最大的四位盐业大资本家之一,而父亲经手的特嫌案可能让他觉得有理由让女儿远离里通外国的可能性。到了次年春节期间,罗老师夫妇在一家饭馆里请我父母吃饭,罗老师又旧事重提(由此可见他的厚道),并说中国可能恢复高考。这一回父亲说容他考虑考虑再议。
父亲着实考虑了几个月才点的头,我记得第一次去罗老师家已是77年的盛夏。那时中国刚刚回复了高考,或许邓小平复出后渐渐缓和的政治气候让父亲打消了里通外国的顾虑,父亲一直景仰罗老师的学识因而成全了罗老师的美意。总之,我第一次去罗老师家时暑假已快过完了,当时我在啃着第一本英文小说《基督山伯爵》的简写本,啃得万分费劲。那个夏天罗老师介入了我的生活,他对我的影响类似于早早地发给我一张通向未来的签证那样的东西,为我日后人生之路打下了伏笔。
罗老师家住在高山井,一个以盐井命名的地方。第一次是母亲陪我去的。到了约定的傍晚,母女俩手挽手地从法院那扇酱色的大门出发,拐进了那条狭长的白果巷,朝着那条至少有几百年历史的“半边街”方向走去。自贡是一座山城,一条运盐的釜溪河穿城而过,1938年中国纪录片开山鼻祖孙明经先生来自贡拍片,一下子迷上了这个城市。那天晚上我和母亲一路爬坡上坎,穿街走巷这才来到高山井。当我们走到一排长长的台阶前,正要下去迎面走上来一位婆婆。母亲便问她知不知罗齐亮老师家住哪里,婆婆反问道:是师专的那个罗老师吗?我们说就是就是,于是婆婆把手一指:他家就在那边!听那口气,这一方天底下仿佛并没有第二个罗老师似的。
那是一户普普通通的旧式平房,家具摆设简朴实用。进门是堂屋,堂屋的灯下很亮;灯下有一张八仙桌,还没进门就看到一位头发花白、长相极精神、仪表极洋派的老者坐在那里悠然地吸烟。这就是罗老师。母亲说到,捏了一下我的手。不知为何,罗老师突然让我想到了那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白求恩大夫,发式、长相、风度都很接近。直觉告诉我,罗老师属于那种人:你只消望一眼便知这是一位有学识、见过大世面的人。
那天李孃孃下乡去了,罗老师一见母亲和我便站起身来招呼:来坐,进来坐。”他个子很高,嗓门低沉却带有一种十分自然的诚恳。我那时怕生,喊了一声罗老师之后还回避着他打量我的目光,一进堂屋就挨着母亲坐下。我们板凳还没坐热,一位婆婆来到我们面前。这是我岳母,退休前教算术。微笑着,罗老师说起李婆婆收集过三百道算术难题,从前她天天晚上都要守着外孙们做三百难。李婆婆正忙着泡茶,不知从哪里一阵风似地旋出一位翩翩少年来,同样是又高又帅,明眸皓齿地冲我们这边一笑,便去帮外婆泡茶。这是我的老幺,开学就上高一了。”罗老师说着,面色一下十分柔和起来,眼神追踪着老幺的一举一动,看他帮外婆把两个茶杯端过来摆在我们面前,看着他旋回了一间屋里这才开始问起我来:你读二中哪个班?教英文的老师姓啥子?男的还是女的?一听我的英文老师姓刘,罗老师便说出一个名字来,见我摇头,罗老师说要是这个刘老师就好了,她当年是燕京大学英文系的高材生(这位刘老师后来教我的高中英文)。他又说了一个名字,正是我的老师,但我心里却很雾数:二中的事罗老师怎会这样清楚?罗老师大约看出了我的疑惑,便解释说他曾在二中教过很多年书,什么班都教过,从初中班到高中班;还什么课也上过,从语文、历史、英文到数理化。
我以前听班主任说过二中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这所中学从前叫蜀光,是抗战大移民的初期由南开大学兼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先生一手接管成立的。当时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天津及沿海所有的海盐场,并封锁了长江的船运来切断重庆中央政府的盐资源,侵略者企图通过人为地制造盐荒,
逼迫以四川为中心的未占领区军民在数月之内不战而降。我日后写《盐路》,还听说过一个故事:第一次长沙大战前夕,国民党抗日将领薛岳的部队已经断盐半月有余,兵马尝尽啖食之苦,士气不振。信号大战的前夜,自贡的盐从水路运到了,一顿大餐之后次日便大胜日军。庆功会上,薛岳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今日长沙大捷,功在自贡的盐!日本人根本没有料到,地处四川腹地的自贡盐场使他们制造盐荒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他们当然更不知道天平天国时期,当闯王的军队封锁了淮盐运往湖北湖南的长江水路之后,自贡的盐在第一次历史上称作川盐济楚时已渐渐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手工业作坊。到抗战时期自贡井盐第二次川盐济楚,故乡人能在极短时间内开发出巨大的盐业生产潜力而成为中国未沦陷区最大的井盐生产基地。战时盐业生产利润很高,有人把盐比作白金,故乡也因此辉煌一时而富甲全川。抗战时期这个仅有21万人口的小城,所付盐税(关税已被日本人夺去)一度成为自由中国军费和财政的一大重要来源,所以蒋介石才1939年9月1日签署了一道手谕,特准自贡因盐设市。彼时家乡的几位大盐商便联合盐务官和教育界人士,并聘请抗战大移民入川的张伯苓先生、喻传鉴先生等教育家,仿南开中学的模式成立了私立蜀光中学。据说学校的建筑图纸是南开中学的翻版:男生部、女生部、初中楼、高中楼、大礼堂、足球场、田径场,游泳池的布局都一模一样,连许多老师也是从天津南开和重庆南开中学聘请来的。
日后我慢慢知道一段姻缘把本来在重庆南开上高三的罗老师带到了蜀光,毕业之后他考入了西南联大,抗战时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合并而成。当日本人占领了宜昌之后,联大从长沙搬去了昆明。罗老师念的是化学,彼时最时髦的专业,因为大学生们一个个都梦想着能科学救国。而联大名师汇集,如陈省身先生、华罗庚先生都在联大教书,日后罗老师曾还说就数杨武之先生的安徽口音最难懂。联大的教学方式很西化,老师鼓励学生要创造、要独立思考而不是死背书本。有了联大的底子,难怪罗老师1950年回到蜀光任教时,哪门课缺人他都能顶得起,并且哪门课都教得有声有色的。阴差阳错的缘故,本来学化学的罗老师后来在二中主持了许多年的英文教学,并成为文革之后四川省第一位英文特级教师”。
罗老师的风格是西式的,这一点在首次见面的晚上就很明显。那天晚上告辞时,他要我下周再来时,一定要带着问题来;不一定非得是英文,别的功课有问题都可以问。又说:不过,我只答疑,从来不辅导。说罢,罗老师坚持送送我们,
一直送到那一排台阶前才肯留步。当我和母亲上了台阶,过了马路我回头望了望,只见昏暗的路灯下,那个高高瘦瘦的身影还直直地站在那里目送着我们离去。
再去时我第一次见到了李孃孃。她个子也很高、体态却因健康的原因有些发福,然而长相很标致漂亮。多年后我才知道原来李孃孃既是蜀光当年的校花、又是田径场上的全能冠军。难怪那个高高帅帅、已在重庆南开念高三的罗家大公子有一次去蜀光找妹妹时邂逅了这位丽人,当晚便写起了情书。随后还转来蜀光重念高三。多情少年写得一手漂亮非凡的毛笔字,加上他的殷殷之诚终于修得了正果,有情人终成眷属,一年之后,李孃孃生下了十斤重的老大亦孝。
言归正传,那晚上罗老师问我可带了问题来。我一边点头一边从书包里掏出一个作业本,上面有几个好不容易才凑出的英文问题。我一个一个问了,罗老师一个一个答了;前后三分钟不到他就答疑完毕。那之后发生的事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上一次很健谈的罗老师突然没了话,只顾抽他的烟,并且一点也看不出再要说什么话的意思。那时的学生不兴提问题,在学校里老师从来不让我们提问题,只要听话、背书、考试能拿高分就万事大吉。
堂屋里静极了,我一下子傻了眼。
许多年后我跟一位在冰岛出生的加拿大朋友聊天,他问我:Belinda,你知道我们冰岛人最怕什么吗?怕冷,对吗?我们倒不怎么怕冷,我们最怕冷场。接着他问我是否尝过那滋味:两个人干坐着,你看我、我看你,可谁也挤不出一句话来。哦,我明白你在说什么了!我答道,当时脑子里一下子想到的正是我那晚在罗老师家的一幕。我窘极了,脑袋短了路,口干舌燥的。想走又太早,不走又挤不出一句话来,眼睛也不知该往哪儿看。就这样僵持着,最后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说要走。罗老师看我一眼,说:也好,我送你。慌忙中我忘记了告辞,跟着罗老师走出门去。左拐右拐又来到了那一排台阶,我便请罗老师留步。他却说:走哦,我送你回法院。不用,天还没黑。我找得到路。我推辞着,巴不得他早点回去,罗老师却把手上的烟头往前一点,说:走哦,走!他用的是英文里的命令句,不容争辩。我心里虽然不情愿,但也莫法。
一高一矮两个影子在街灯下走入了半边街,年久失修的青石板路坑坑洼洼的。有一刻罗老师开始问我是哪年生的;我答了。这一年碰巧是他家老大老二同时考上大学的年头,不仅如此,老大亦孝还做了四川省的理科状元。一说起他家的四子一女,罗老师忽然变了一个人,口气也和婉起来。他从老大如何优秀一直说到老幺如何顽皮。尤其说到老幺打麻雀手段如何高明,罗老师好像年轻了半个世纪:有一次我看见老幺,腰杆上栓了一串麻雀,迈着方步,俨然一个武将军得胜回朝!拽式得很咯(四川方言:异常骚包的样子)!”
我没有插话,心里却奇怪:这罗老师好像跟从前教过我的任何一个老师都不同。结果老幺的事还没讲完,法院的大门已远远地横在了面前。大门已关,有扇小门虚掩着,罗老师站着点了一支烟,叫我下周同一时间再去,挥挥手算是作别。日后都是这样,他每次必看我进了小门才肯往回走。当然,那时我尚不知他送我之后还要赶去另一处听诗的事。
那次冰岛式的冷场便是我平生挨过老师的第一鞭戒尺,我们四川话叫做打板。那一顿闷板子,敲过来时没声,却一记记都敲进我心里去了。再去时,本子上便凑了一堆问题;问完英文问中文,问完中文问数理化,从此不再冷过场。但凡是没有好好动脑筋的问题,罗老师总是半句话就搞定,决不多费唇舌。偶尔我也问到一点有意思的东西,他就会很高兴;还不厌其烦地举例,旨在一次性说透解决问题。记得一次问到英文的不定式和动名词在用法的区别,灯下的罗老师马上直起身来说道:这个问题问得好!你能注意到这两类词用法上的微妙,说明你动了脑筋。那一刻他看我的眼神也会出奇地柔和,仿佛我一下子成了他家的另一个老幺似的,那时他家的老幺已提前一年考上大学去了南京。
有一次我准备数学竞赛,我问了一道几何题;头一晚上俩人都没想出来。次日晚上罗老师早早地就来了我家,跟我一起继续啃那道题,一直啃得停了电。我说算了吧,罗老师却喊我母亲:邹孃孃,你去点蜡烛来。于是母亲便抹黑楼上楼下地找出两支白蜡来点燃。后来罗老师硬是想出了要加第二条虚线,证明才一下之出来,又简又巧。那一刻罗老师笑了,烛光下和颜悦色的脸上,眼睛亮亮的,大有类似于他家老幺得胜回朝时的快感。这一道题让我懂得,give-up(放弃)这个词不在罗老师的字典里,也不应该在我的字典里。人无弃人,物无弃物,这便是我从罗老师解这道几何题中得到的启迪,受用一生。
我快上高二暑期里,罗老师来我家与父亲和我开了一个小会,讨论我该读文科班还是理工科的事情,因为一开学就要分班了。我父亲希望女儿继承父业学法律,进文科班;我那时很喜欢英文,暗想考外语学院,也得进文科班。开会的晚上,罗老师坐在我家客厅里的一把老式藤椅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听完了父亲和我的意见,罗老师这才发了话:你们说的我都懂,但映碧不能够学文科。她又不是数理化搞不起走!(四川方言)”听口气没太多可商量的余地,父亲和我虽有些诧异,但罗老师认定的事错不了,于是分班的事就这么板上钉了钉。
那时我照例每周去他家答疑一次,只不过回来的时候,两人深一脚浅一脚走在半边街和白果巷里,我已可以随心所欲地问问题了。
“我爸说你出过洋留过学,是吗?”
“我没出过洋,我父亲倒去过一趟美国。”
“他去过美国?什么时候?”
“抗战胜利以后。”
“他去那里干啥呢?”
“生意上的事。”
“那你为啥没一起去?”
“他生意上的事我向来不懂,我不是那家人。”
其实,我那时也晓得了罗老师的父亲是大盐商。家乡上了岁数人,哪个不晓得解放前的侯、熊、罗、罗四大盐商里,最后那个罗就是罗华垓,罗老师的父亲。有一次去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受教育看展览,我进到一间展厅是看到过这么一幅宣传画:画的上部是一个驼背老盐工,弯腰背着一大筐盐,嘴里吐着血,一滴滴鲜血自上而下流进了画面下部的一只高脚酒杯里,杯子里有大半杯鲜血,被一个南霸天那样的胖盐商举着正要喝。那人身穿马褂长衫,带着一顶瓜皮帽,笑得满口金牙,画的标题是诸如大盐商罗华垓剥削盐工之罪状一类的文字。我一读罗华垓”心里就碰碰乱跳起来,匆匆地走出了展厅。然而,那幅画面太生动了,一直梗在我心上。明知不该问,有一次我还是问了:听说你父亲过去是一位大...大盐商?”
“对头。罗老师的声音更低了。
“那他一定遭了许多殃。这些事我看得太多了,文革时我们住的法院大院成了红卫兵总司令部。
“我父亲是遭了不少殃,但遭殃的还不止他一个。你看我家老三,我等一会儿还得走去听他念诗’。”
他家的孩子个个都是大学生,唯有老三做了时代的牺牲品。文革时老三下乡十几年,等所有的知青都回城了,偏偏他遭人刁难回不了。老三又愤怒又孤独,有一阵便闷头写诗,到最终精神崩溃才回了自贡。而罗老师这些年,每天晚上必赶去刚刚成家的三儿子那里,一安抚情绪,二增减药物。老三清醒时,常对父亲说:爸,我遭孽;你也遭孽。罗老师每次跟我说起老三的事,苦笑的脸上总是带有一种深刻的同情。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是老天下刀子,他每天晚上照例必去老三那里,听儿子念完了诗,再数了药片倒一杯开水,送到儿子手里,看他吃下去之后自己再回家休息。
正是从这位异常尽职的父亲身上,我懂得了责任两个字的含义。亦孝大哥日后告诉我:我父亲其实是个极怕麻烦的人,生活上也很容易凑合。明知要下雨,他也懒得带伞;有时候出差,他也是插一把牙刷就走。然而,罗老师却能在老三生病的二十多年里,每天晚上都去听诗、送药;对于我则是每次答疑之后都必须亲自送回法院大门口才回去;其他学生来看他,也总要送出很远很远才肯回家。他是这样的人,自己怕麻烦,却总是怀着极其愉悦、极其慈悲的心境去关怀身边的人。有时我觉得罗老师既是一位行者,又像一条船,他一生以渡人为乐趣,从不去区分这些人与他是血缘或是尘世间错出来的机缘而带来的缘分。
高考的那个学期我不再去罗老师家,而是他来法院,每周总有两三次。若是某一天收到了老大从兰州中科院近代物理核物理所(亦孝大哥旅居美国前曾任该所所长)的来信,当天晚上罗老师一定来我家里。说起来,我是读着亦孝大哥的信考上大学的;而核物理学家的信里总有好消息:要么是他的课题组发现了某一种放射性新核素,要么是他又去了某一国宣讲论文。每逢读信的晚上,罗老师倚在我家藤椅上的姿势也会跟平日不同;他身体微微前倾,脸上总有愉悦的微笑,目光异常悠远仿佛可以穿墙越壁。通常,他会先让我问完所有的问题,再同我父母说一会闲话,这才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封兰州来信,递给我念一念。我偶尔念错了字,一定逃不出罗老师的纠正;读到某一处字迹不易辨认,一看我慢下来,罗老师马上就能把那句话一字不差地念出来。念信的晚上总是愉悦的,但我最近才突然悟到或许罗老师让我念信,并非完全处于希望我们一家都来分享他那份满满的喜悦,说不定这里面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因为老大的信于彼时快要高考的我来说其实代表着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更广阔却是可能到达的彼岸;而对于我父母来讲则又意味着一个无声的问号:女儿要远行了,你们准备好了吗?这件事我没有问过罗老师,他现已90岁高龄,很多事他记不得了,所以也不必问了。有时生命中还得有些悬念,偶尔回首当年才会更有想象的空间。
高考考场设在二中,除了罗老师每晚必来家里询问情况安慰情绪之外,我的班主任栾老师、数学课的马老师也会从二中走40多分钟的路到法院来问长问短的。罗老师家曾出过一个状元,两位老师也对我给予了非常殷切的期望,只怪自己心理素质太差,高考三个晚上竟彻夜不眠,影响了发挥... 升学志愿是罗老师、父亲、还有老幺一起帮我填写的;这回命运差我去了西安,在母校西北工业大学一呆就是十年。
自从18岁离家去了西安,每月除了收到父亲的信和汇款单,还总能有一两封罗老师的来信,所以我是读着父亲和罗老师的信走上人生之路的。在那一隅民风淳朴的黄土高原上,我上完大学、研究生又留校任教,。春去秋来,就这么一天天地行、一点点地走着,十年之后居然也跟罗老师家的老大一样走到地球的另一边去了。核物理学家如今就职于旧金山附件的凡德比尔特大学物理系和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而我则经过了加州-德州-麻州的大迁徙之后定居在宾州伯利恒(Bethlehem),一个依山傍水、曾在一战二战中兴旺发达过的钢铁城市。十年前“机缘先生”不仅让我遇到了怀东的祖师爷陈省身先生,与数学大师的“百岁书约”更是一举改变了我的职业。几年前弃工从文,年逾不惑的人从零开始,先是坐进了文学的课堂,后来便不务正业地写起一部故乡盐都的二战传奇历史来作为送给陈先生的一份寿礼。而写作的语言正是当年经过罗老师每周一次调教了又调教的英文。
《盐路》一书的调研期间,我阅读了好些自贡盐史资料。从《自流井盐业世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授Medeleine Zelin
博士的英文专着《The Merchants of
Zigong》(《自贡商人》)、以及罗老师的老二编著的《罗氏家族史》等史料里,我了解到罗老师的父亲是一位“新派盐商”。他不但长得一表人才,还是一位作风正派、有能力有魄力讲信用、极受人尊敬的实业家。他17岁就只身从家乡简阳来到当时充满了就业机会的自流井,仅凭自己一手好字便被自流井一位大盐商一眼看中,留下做了学徒。与同时期的其他三位大盐商不同的是,罗华该百手起家的资本不是金钱,而是他兢兢业业做事、公平诚恳做人;既果断务实又具有一般盐商所不具备的儒雅风度和非凡的外交能力。抗战时期,富甲全川的自贡盐商们需要跟迁都重庆的中央军政要员打交道,罗华垓总是自贡商界出面斡旋的主帅之一。更为难得的是,二战时期自贡众多的大小盐商因第二次川盐济楚爆发之后,一个个纷纷置田产、起洋宅、建公馆,而彼时已拥有巨款家产的罗华垓却毫不动心。他无心置产,却选择了办教育。他出巨资在家乡简阳办起了一所水准很高的西式“纪云中学”。抗战胜利之后通货膨胀,罗华垓动用更大的财力来维持这所中学的运作,直到解放后无偿捐给人民政府,而罗华垓自己却成为自贡唯一未置过一栋房产、一辈子都靠租房度日的大盐商。
从罗华垓的故事里,我看到了罗老师是从哪里来的。于是我决定《盐路》里应该写一写这位新派盐商。2008年的夏天我采访了罗老师,想了解在他眼里,罗华垓是怎样的一个人物。
“我父亲?他是能写会说的一个人!”八十九岁的恩师是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的。当我问到抗战时期罗华垓当年办井办灶的辉煌过去时,向来认定在商场上自己不是那家人的罗老师却说:我记不得他那些事了。我只记得小时候,挨过我父亲不少板子。”
“是吗? 为什么呢,你逃学吗?一听他也挨过板子,我立即来了劲。
“没有,我没逃过学。”
“那他为什么打你呢?“
“我记不得咯。只记得在堂屋里头,他经常弄我来训。”
“训些什么呢?”
“他训的东西多了,也记不得了. . . ”
“是用古文训的吗?四个字四个字地整?什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你从前说过的。”
“差不多。总之,经常是我一回来,娘就告我的状;每回都是我自己去屋里拿篦片---”
“自己拿篦片?”那是很厉害的一种体罚工具,猛地扇下去,会搜搜的发出风声。
“是啊,自己拿了篦片来,交给我父亲,我喊牙牙(注:江西人这样称父亲,罗老师祖上是江西入川的移民),他总是打我十三个屁股。”
“为什么是十三个?我好奇,13碰巧是西方人很忌讳的一个数字。
“不晓得,反正总是十三个屁股。严重的时候,还要拿一个矮板凳,要我给看热闹的人磕转转头。说罢,罗老师笑了起来。童年的记忆,就是打板子也是愉悦的。
“那时候你多大?”
“十二、三岁吧。我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反正挨打最多的就是我!”
“你是老大嘛,你父亲对你的期望最高。”
“每次十三个屁股,要话说。他边说边摇头,照例是烟不离手,面部的笑容却舒展开来。
罗老师在家中,冰岛式的冷场发生在18年前
那一刻, 我突然很想跟他说一说我在他那里挨的那顿闷板子,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因为那一刻罗老师还沉浸在儿时的回忆里。他表情极生动,连鬓角上的白发和额头上的皱纹也活泛了许多。打是爱,他的父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当儿子经历的许多往事都已烟消云散,却还能以他特有的幽默来笑谈父亲当年的体罚,谁能说这联系感情的方式里少得了挨篦片、打板子之类的东西呢?或许我当年挨他那一鞭戒尺,也属同一类性质?
毕竟,罗老师当严师的时候少。我做他的弟子也这些年了,也就那一次冷板凳而已。他更好无为而治,有一次他说:别人问我,你家的娃儿是怎么教出来的?我说,什么都不管。总而言之一句话,娃儿不能太乖(四川话,听话),大人不能太严”难怪他家的孩子跟他那么亲,亦孝大哥说父亲是一位很细腻、很幽默、很有爱心的人,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为师之道。更何况罗老师的性情还很西式,自由平等博爱,他那种自自然然的智慧颇有老子式的通达却没有孔子那样的牢骚,跟他聊天不但轻松自在,还是一种审美的享受。此外他也是一位很有心的听众,但却绝不苟同任何一种随大流”的说法,他说人要有自己的见解、想法,还要能够准确诚恳地表达出来,否则无法让人口服心服。虽说师者这一行以操舌根为业,但我觉得罗老师以身教为主,育人的责任大于教书。他既是一位行者,更是一位舵手;曾那样的不辞辛苦舵了一班又一班的船,把弟子们一个个从此岸渡到彼岸。而这位渐渐老去的舵手如今仿佛慢慢地化作了一抛锚,静静地泊于水中,而我这样的弟子犹如远近飘摇的轻舟,忆起这一位特别的恩师,心心念念之间还能感到昔日的依傍。
今年“父亲节的早上,我给父亲大人请过安之后把电话打去了罗老师家。这一次是李孃孃接的,一听是我,她焦虑地说罗老师又摔跤了,胯骨粉碎性骨折,正住在重症病房里。“他这个人,一辈子我行我素,叫他不要出去走,就是不听。他又不愿意坐车,都是走着去汇东去看老三的孙孙。一走就是一个多小时,我拦也拦不住,结果摔成这样. . ..”那天聊了很久,放下了电话,心里虽乱,我却能够懂得为什么罗老师要走老远的路去看四世同堂的重孙。那是老三的血脉,或许这位感情细腻的曾祖父一看见这孩子也就看见病逝多年的三儿子;或许他还看到生命延续的奇迹
---毕竟,这孩子身上代表着无限的生机。
稍后我找出了两贴罗老师从前送我的墨宝,一是李后主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 . . ;一是白居易的琵琶行:
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 . .
.当我舒卷于灯下细细品来,果真是字如其人:一手行云流水的字,内秀而脱俗,字里行间还另有一种张力,另有一种玉树临风、挺拔飘逸却毫不张扬的风骨神韵。一时间,我脑子里又出现了当年那个颀长挺拔的身影;在昏暗的街灯下,那熟悉的身影缓慢地朝前走着、走着,一直走到月亮高高升起。
那是一个行者该有的身影。在我心中,他一直都会这样走下去,走下去 . . .
2009年7月13日,法国马赛(《基督山伯爵》的诞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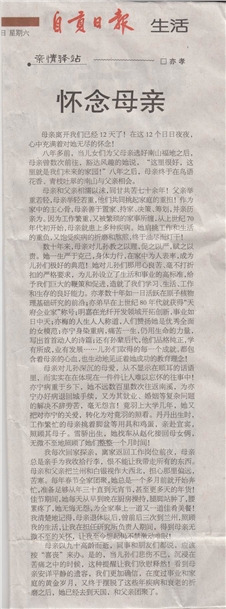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