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爸爸 亦弟
忆爸爸
亦弟
(2012年8月16日)
如今操劳一生的爸爸已经离开我们去往天国,对爸爸的无限思念打开了我记忆的大门! 从小到大, 体现爸爸对子女的深沉的爱,体现爸爸对子女舔犊之情的桩桩件件一一浮现眼前。我想写下这些看似平淡的往事,在这些看似平淡的往事后面,展现了爸爸不平淡的伟大父爱。
幼儿时代,爸爸对我的关爱还依稀留在我记忆之中。大约是二、三岁时吧,爸爸、妈妈在公公创办的简阳纪云中学任教,全家居住在教学楼二楼上。当时的教学楼都未建有室内厕所,每晚半夜都是爸爸把我和哥哥抱到窗口”提尿”。三岁了,爸爸给我们兄弟俩买了玩具左轮手枪,我喜欢玩枪,成天在鲜花满园的花园里用手枪打蜜蜂。被打死的蜜蜂,就成为我的战利品,还用手指头蘸食被打破的蜜蜂身上的浆体 — 我以为那是蜂蜜。为此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爸爸总说我是“油蜡瓜儿”。一次不巧被蜜蜂蛰了手,肿起来并且很痛,于是嚎啕大哭。爸爸闻讯赶来,只能吹吹揉揉,无计可施,爸爸的同事谢伯伯很有办法,用肥皂水涂抹,才慢慢止住疼痛。儿时在纪云中学生活的记忆是美好的。
快四岁时回到自贡,在家乡一直生活到1962年高中毕业。自贡的夏天非常炎热,那时没有风扇,更不用说空调了。傍晚人们都喜欢在门前放一块门板或凉板,睡到半夜退凉才进屋。而进屋睡觉还要饱受蚊虫的侵扰,那时是用大约一米长,两公分粗的锯木面加六六粉外裹皮纸做成的蚊香用以驱蚊,由于这种蚊香含有剧毒农药六六六粉,人也受不了它。蚊香本不足以完全轰走蜂拥的蚊子,如果蚊香受潮半夜熄掉,熟睡的人就更要被蚊虫饱餐一顿了。所以,尽管再热,我们睡觉都要放下蚊帐,睡前还要把蚊帐里的蚊虫拍死。蚊帐经多年使用,已经破损,不仅要经常用线或胶布补上,还要防止拉蚊帐时把它撕开一条大口子。酷热之夜闷在蚊帐里的滋味至今记忆犹新,半夜常常被热醒过来,满头满身大汗,凉席上赫然一个汗湿的人印!经常在朦胧中突然感到一阵清凉,那是爸爸半夜起床为我们用湿毛巾擦身子,打扇,那种凉彻肺腑的舒适感觉直到现在都非常清晰。
我这句儿时的话,爸爸却记了几十年,我工作以后,还听妈妈说过:你爸爸经常一个人念叨“是狗狗把我挤zhuai了的呀”。绘声绘色地反复模仿孩子们稚气的话语是爸爸的最爱,往往持续和重复很多年而激情不减 ── 那是爸爸爱儿之心最典型的表现形式之一! 右侧图片里就有挤倒我的大黄狗,此时我们倒是相安无事。
婆婆懂得种植程序,刨土、下种、浇水、施肥、除草无一不通。那时大哥和我都还小,在婆婆带领下拿锄头,担粪桶。有时爸爸从学校回家时遇见我们三婆孙正在地里劳作,爸爸会立即下地和我们一起劳动。到了收获的季节,去地里掰几个玉米,放到柴火灶里烤熟,送一个到爸爸床边 — 爸爸回家后多半是躺在床上的,爸爸非常喜欢吃烤玉米。
五岁时的一天清早饭后,妈妈给大哥收收拾拾,拉着大哥的手出门。我问妈妈去哪里,妈妈说大哥要上小学了。我说我也要去,于是妈妈另一只手拉着我就出发了。在解放路小学经过简单的测试,我们都被录取了。大哥分配到解放路小学念书,我被分配到后山坡小学。
爸爸从不因孩子打破酱油瓶或者摔碎饭碗而责罚孩子,但是对于不用脑筋,不负责任大而话之而犯下的错误,或者达不到目的就去破坏之类行动却不能原谅。爸爸给孩子答疑,从不“抖巴巴”给孩子讲题,而是启发正确的逻辑思维。爸爸批评孩子用得最多的话语是“大起个脑壳” — 指不用脑筋。小时后妈妈对我的要求是入少先队、共青团。而爸爸的要求则是“用脑筋”。
那时我是走读,午餐是早上带去的饭菜一并装在布袋里的午饭去食堂蒸热吃。爸爸经常带我去校门外高耸入云的楠竹林中,一家东北人开的小面馆吃面,那里还有甜甜的开花馒头,好吃极了。有时爸爸上课去了,他的书桌上会有小堆炒花生,周围用粉笔画一个圈,旁边写上“食之”或者“吃掉”。爸爸非常理解孩子的心理,在细处关心孩子。爸爸理发时,经常不吹风,省下几分钱,买两块花生糖,苕丝糖,油炸粑或者豌豆粑,摊在扇子上带回家,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吃。
后来学校搞政治运动,路过办公楼时,经常听到楼上传来楼板被撞击的响声和 “老实交待”的大喊大叫,令人毛骨悚然。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是反右斗争。爸爸在反右斗争中没有受到冲击,爸爸说学校的领导事前曾经关照过爸爸,在“鸣放”中不要随便讲话,有保护爸爸的意思。
爸爸在蜀光师资队伍中是难得的全才,哪门学科缺老师,爸爸就教哪门。爸爸曾先后教过语文、数学、历史、化学、俄语、英语,最后长期任教的是英语,而且长期担任蜀光中学外语教研组组长。
我在二中平平淡淡地读完初二,适遇住家从三台寺搬到煤炭坝,上学路程就更远了。爸爸妈妈商量给我转学。我在自贡一中校长办公室找到杨相辉副校长,呈上爸爸写给杨副校长的信件,杨副校长告诉我拟将我和大哥编到同一个班。在一中我初三的学习成绩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 进入中上水准。当时,大哥是品学兼优的班长。
1959年初中毕业参加高中升学考试,我和大哥一同考入爸爸任教的蜀光中学,大哥分在五班,学俄语,我分在二班,学英语。高中要求住校,我和大哥住进了爸爸那间不到十平米的蜀光教师宿舍,在爸爸床前以两条长凳支撑一块床板,就成了我和大哥的床。大哥严格按照学校规定作息,我则经常睡懒觉,爸爸从不叫醒我,爸爸常说: “我就最讨厌睡觉被人打扰。” 那时没有风扇,真不知道那几年,夏天酷暑我们父子三人同住一间小小的单身宿舍是怎么度过的。
我的英语老师,高一是张用九老师,一位令人尊重的老者。讲课时上牙掉下来与下牙碰撞,发出脆响,我年龄小坐前排,听得真真的。张老师发音准确,读perhaps [p?''hæps]时,要求我们发æ音时要“吊起下巴说话。”
高二英语老师是罗达仁老师,讲疑问句时,让学生把肯定句“社会主义好”作为例句,变为疑问句,即是“社会主义好吗?”,我在台下惊愕了:反右时他就被打为右派,为何还这么大胆?下课后我把此事告诉爸爸,爸爸笑了。
作为爸爸的学生,我没有辜负爸爸的教导与期望,我的英语成绩一直是全班最好的,也一直担任班英语课代表。高三时蜀光举行年级(三个班学英语)英语基础知识竞赛,我获得第一名,爸爸向我颁发了奖品 — 一个活页夹,上面的奖项说明是爸爸手书的,因为爸爸是学校外语教研组组长。为了提高学生外语水平,学校组织了外语学习经验交流会,大哥介绍了俄语学习经验,我介绍了英语学习经验,学习经验交流会的主持人就是爸爸。会后,一些同学开玩笑:学习经验交流会就是你们三爷子唱完了。一些同学总以为爸爸会单独给我上课开小灶,其实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在爸爸的课堂上,我也走过麦城,那是令我终身难忘的。课文是《伊万苏萨宁》,写一个苏联名族英雄伊万苏萨宁把德国士兵带入沼泽的故事,其中一句是: “士兵拖着疲敝不堪的身子跟着前面的人走着”, 爸爸的问题是:“前面的人”指的是谁?已经有十几个同学因错答“前面的人”是伊万苏萨宁而站在那里了,爸爸因这么多学生答错而生气,学生因担心被抽答而紧张,课堂气氛越来越凝重。我经过紧张地思考,除此之外想不出别的答案,而爸爸已经否认了这种解释,所以我也十分紧张。就在这时,爸爸的目光扫过我的眼前,这是爸爸要抽我答题的前兆,我站起来无可奈何地回答:是伊万苏萨宁。这时,爸爸终于控制不住情绪,愤怒地大声说我: 脑子里只有一条线。…。我心里委屈极了,不就答错一次吗?犯得着发这么大火吗?为此,我几天不跟爸爸说话。对于爸爸震怒的原因,后来我想通了,爸爸是恨铁不成钢,我不应该为此不理爸爸。此问题的答案是: “前面的人”指的是走在前面的士兵,即是说,后面的士兵无可奈何地跟着前面的士兵。这个答案当时我的确是难以想透的。
大跃进年代,学校也组织学生搞生产,我被派去参加生产尿素。在酷暑之下伺候火炉,大汗淋漓,又没有水喝,终于中暑了,眼发黑,汗如雨下,站立不稳。有人飞跑去告诉爸爸,爸爸赶来扶我回到寝室,给我喝水,打扇,服了十滴水,我才慢慢地恢复正常。一次我患了重感冒,不停呕吐,连喝水吃药也被吐出来,爸爸找来热水袋放在我的胃部,才逐步止住呕吐。其实爸爸对治疗小灾小病还是很有些办法的。比如胃寒或吃生冷引起的胃痛、腹痛,以香烟灸内关、合谷有奇效,此法我多年来一直在用。再如如厕结燥,揉双腿足三里穴位立可见效,爸爸多年使用此法,对我们几弟兄多次传授,我也一直在用。
回忆爸爸,不能不说到香烟,爸爸烟瘾极大,须臾离开不得。凡有人劝爸爸戒烟,爸爸都不高兴。大约在55年前后,爸爸也曾在妈妈的劝诫下,试图戒烟,妈妈买糖果以替代香烟,其结果如妈妈所说,是“烟也吃了,糖也吃了。” 学生中关于爸爸烟瘾极大的传说很多,有高年级的同学告诉过我,说爸爸在上课前站在教室门口同时吸两支烟,狠狠地吸几口之后,才熄掉香烟走进教室。在课堂上45分钟不吸烟是很难熬的。我倒没有见过爸爸教室门口同时吸两支烟,不过上课铃响之前,爸爸在教室门口猛吸香烟倒是常见的。后来才知道,那时爸爸一天要吸4包烟,几乎是一支接一支。
在困难年间,香烟计划供应,计划之外,有爸爸的学生经常寄来苏联的莫合烟草,也有民盟供应的两条香烟,其中爸爸要支援二爸几包。妈妈凡去郊区出差,也要设法替爸爸买香烟。以爸爸的烟瘾,香烟缺口极大。大哥和我担起责任,要帮助爸爸度过难关。我用一根筷子,粘上一张矩形牛皮纸,就做成了简易卷烟器。在字纸篓里搜集爸爸扔掉的空烟盒,周末再和大哥一起去电影院检烟锅巴,从中抖出烟末,加上爸爸吸剩的烟头烟丝,再混和一些往届学生寄送的莫合烟草,就可以卷成“无字牌”卷烟。烟丝经常不够,大哥和我常混入一些剪碎的橘子皮凑数。卷成的香烟很长,再用剪刀剪成两根,放在爸爸书桌中间抽屉里。当时我和大哥有不成文的约定,谁先回寝室谁替爸爸卷烟。这些自制无字牌香烟的确帮助爸爸解决了大问题,每当我们从各自的教室闻到教员休息室飘过来的带有橘皮味道的香烟味,心中就充满一种成就感!从那以后,爸爸即使在外面抽烟,烟头也从不乱扔。关于此事爸爸还多次讲过一个笑话:一次爸爸在正街小食店吃面,吃面之后抽了一支烟,香烟快要燃尽之时,对面一个烟瘾大发的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烟斗对爸爸说: “(烟头)拿来栽在这里头。” 他哪里知道,这个烟头爸爸是要带回去做无字牌卷烟的。
困难年间的最大问题在于不能填饱肚子。我们的口粮定量被一减再减,后来干脆换成红薯,还要学生自己到公社的地里去刨,然后过称担回学校,再分配给个人。我们父子三人的口粮 — 红薯就堆放在我和大哥的木板床下,每餐用称称出定量红薯,送到食堂去蒸熟。爸爸多年以后还在笑话:每次亦弟称红薯,亦孝都要一再提醒“平点,平点”,而亦弟总是希望“旺点”。那时学校对教师有些照顾,设法搞来一些老菜帮子,老藤藤菜,晚上给教师加餐。这对于饥饿中的人们无异于莫大的喜讯。遇到加餐,爸爸总是把菜端回寝室,叫我和大哥一起吃。每餐饭后,大哥和我总能从爸爸的菜碗中得到一点“补充” ── 那是爸爸为我们留下的一点菜,虽然是毫无油性的老藤藤菜,却多少缓解了那难忍的饥饿感!
饥饿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和孩子是无法体会的,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我坐在爸爸书桌前复习功课迎高考时,饥饿难耐不得已起身去爸爸书架上取出酱油瓶,喝一小口,又看书,又感口渴,又喝口水,最后被水灌饱了肚子。
一九六一年,进入紧张的高考准备,一天,我和大哥在寝室看书,爸爸进来说:你妈妈生了,去医院接她回家。我们立马跑到医院,由大哥抱弟弟,我提脸盆茶瓶衣物,把妈妈接回家。妈妈和爸爸决定弟弟随妈妈姓李,大哥建议为弟弟取名“明嘉”,明是字辈。
高考后,我和大哥在酷暑中等待发榜,轮流去蜀光“值班”,等候录取通知。一天我去学校“值班”,突然有人来告知父亲:“蜀光收到第一批共十三封录取通知书,你老大老二都有。” 我和爸爸急忙跑到收发室,果然有大哥和我的录取通知书!爸爸在拆录取通知书时激动得手发抖, 拆开一看,大哥考入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我考入四川大学。大哥得知后,兴奋地对爸爸说: “爸爸,第一志愿,终于如愿以偿了!” 当时,我家的喜讯在自贡广为流传,亲朋好友都为我们高兴。
经常会有人向爸爸讨教: “你的娃娃都考上了重点大学,你有什么培养娃娃的经验?”爸爸总是笑着回答: “我的经验就是不管。” 其实爸爸不是真的不管,我zao得太过分要管, “大起个脑壳”做事则更要管,仅此而已。其它方面,是天高任鸟飞,任由我们自由发展。
大哥学习踏实认真,而我凭小聪明。高三时我获得过年级物理竞赛第一名,英语竞赛第一名,但是高考成绩却远落后于大哥。大哥高考总平均九十一点五分,我的平均分是八十一分。后来才知道,如果我的志愿填写得当,当年我是大有可能录取北大或清华的。1962年科大录取生平均分数八十六分,高于北大清华,我以五分之差落选科大,但却完全够了北大清华的录取线。错就错在当时我和大哥一样,填写的升学志愿顺序是:科大,北大,清华…,川大…,川大是第六志愿! 显然,北大清华没有录取我是因为我没有把北大和清华填为第一志愿,他们不可能录取一个“狂”到不把北大清华填为第一志愿的人,尽管你考分够了!而川大本来也只录取第一志愿考生,这次录取了以川大为第六志愿的我, 是因为我的考分如此之高 ── 在录取川大的人中我属少有的高分。语文是我高考中拉分最多的学科,尤其是作文。爸爸曾多次这样评价我的作文: “语句是通顺的,也没有错别字,但是内容是干巴巴的。” 对于爸爸的如此评价,我向来是服气的,因为我的作文的确如此。大哥的作文却总是被语文老师作为范文在班上讲评,这是我远远不及的。
蜀光的外语教学水平很高,学生考入大学后外语成绩都是名列前茅。我一考入川大无线电电子学系,就被委以英语科代表。
每当寒暑假,我就迫不及待地买火车票回家。在家里享受爸爸妈妈的无穷关爱,尽管当时家里经济拮据,总是要尽量多买肉给我吃。记得一次爸爸带我去灯杆坝菜市场买菜时说过:“你们每次回来,家里都是尽兜兜甩,”“尽兜兜甩”的意思是竭尽所能。每逢假期结束要返校时,心里就十分难受,尤其是走进学校食堂就餐时,学校的环境与家里的温馨的强烈反差使这种难受就更加剧烈,一直要延续好多天才能适应过来。
亦梅小时患紫斑症,发病时人事不省。爸爸妈妈到处寻医问药均无结果。当时医院院长甚至还说,你们也可以送到成都去医,不过多半成都医院也没有办法,为此爸爸妈妈十分着急。一次爸爸参加市里政协会议,听一个冉冉老者对爸爸认识的一位教师说:“女儿肺病三期,医院不收,我叫她回来,给她治好了。”爸爸闻之欣喜若狂,立马请这位老师引荐这位老者,原来老者是成都中医大学退休的教授梁公公。爸爸把亦梅病情作了介绍,梁公公说,不用带女儿来,我开一副药,服下就会有好转。之后,爸爸几经奔波,经过一段时间的中药治疗,亦梅终于痊愈了。
爸爸一生为人清高, 从不求人,连学校要给爸爸评职称让爸爸写个申请,爸爸都不愿意写。可是爸爸为亦梅上大学的问题,却破天荒地找了领导。亦梅所在的铸钢厂按照条件计划推荐亦梅上大学,可是名额被一名干部子女挤占。爸爸为亦梅不平,在家准备好亦梅的证书、奖状等资料,向有关领导申诉,由于领导的干预,亦梅终于如愿以偿进入泸州医学院学习。事后爸爸说,我一辈子从不求人,可是亦梅读书的事情我不得不管。
每次回家都可以看见爸爸晚上为嘉嘉洗胶鞋。嘉嘉好动,不管泥里水里都去跑,所以胶鞋里面总有泥土。爸爸每晚以毛刷清洗胶鞋及鞋垫,洗出来的水就如泥浆,洗净后放到灶头烤干,以备嘉嘉第二天穿。直到嘉嘉上中学,爸爸一直都在默默地做着这件看似平凡实则不凡的事情。
一九六八年,我川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宜宾市刚刚组建的地方国营军工企业 — 宜宾电声器材厂工作。那时还处于凭票供应年代,为了帮助爸爸解决缺烟的困难,我把烟票、油票存集好,存多以后买成香烟、菜油,周末清早乘火车送回家,再赶下午的火车回厂。一次下了火车,背着香烟、菜油回家,走进煤炭坝家门,清风雅静,疑为无人,但又大门洞开。疑惑中进入里间,见爸爸躺在床上,有气无力,问:有烟没得?我说:有。爸爸立时挺身而起,我在书桌边解背包带子,爸爸已经忍耐不住,接过一包香烟,横向撕开,抽出一支点燃猛吸,一口之后香烟已然去了大半截。看来爸爸那次是饿烟太久了。爸爸说,没有烟抽简直手脚都找不到地方放。
爸爸酷爱书法,年轻时主要习王羲之、赵熙字体。多年来爸爸每天习字,外出每遇好字都要驻步观摩良久,并以手指在空中写字。即使爸爸在成都生病住院期间,也经常以手指在空中写字。我也爱好书法,每次回家,都要站在爸爸身旁看爸爸写字,经数年练习,颇有长进。爸爸书法的功力是集数十年勤学苦练之大成,在自贡、乃至全川已经甚有名望,而我的书法水平则不及爸爸之万一。
爸爸学识之渊博,英文水平之高超,是我工作之后才领略到的。为了业务需要,我在工作之余大量翻译英文专业书籍、杂志,遇到不少解释不了的语法现象和字典上查不到的英语单词,就在回家时向爸爸请教。一个语法现象,爸爸可以滔滔不绝地讲解十几、二十分钟,而这些内容语法书上是查不到的。记得有一次,一个长达15个字母的英语单词难住了我,几本大字典上都查不到,我只好连同其他几个难字一起记在一张纸上,回家时向爸爸讨教。爸爸随手掏出钢笔,一一在难字后面注上对应的汉语,爸爸为我注解单词从不查阅字典。爸爸年轻时外号字典,翻过字典就扔掉,同学们记不到单词都问爸爸。到这个长达15个字母的英语单词时爸爸笑了,爸爸说:“你的书上把这个单词印错了一个字母,所以你查不到。”说完把汉语意思写在旁边,按照爸爸的解释,原文的上下意思都通顺了,此时我心里对爸爸简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爸爸又笑眯眯地从里屋拿出一本毛边纸印刷的老英汉字典,一下找到那个单词,说: “你看这里,你的书上把这个字母a印成了e,所以字典上查不到了。” 爸爸作为全川第一个英语特级教师,这个称号真不是白给的。遗憾呀!未能传承爸爸的渊博学识,惭愧呀!
说到字典,又想起爸爸多次说起过的一件事情:抗战期间,热血青年纷纷投身革命,走上前线。爸爸和后来在中央党校担任领导职务的李公天等几个进步青年来到北京,寻机奔赴延安。众人里面只有爸爸家境更好,所以数众人的吃住开支都得靠爸爸提供。可是公公对子女严于管教,不会无端给钱。爸爸想到的要钱理由就是买字典,字典用于学习,公公支持,而且价格高,可以多要到钱。 “买字典”次数一多,公公起了疑心,去信问爸爸:你究竟要买多少字典?在爸爸联系妈妈“把老大老二送到荣县,去京汇合共赴延安”的密谋被妈妈泄露给公公后,爸爸赴延安的愿望终于没能如愿。
进入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工厂工作越来越忙,特别是担任厂长之后,回家的次数减少了,每次在家待的时间也更短了。回到家里,除了爸爸妈妈想方设法做好吃的饭食款待我之外,每晚必然长时间聊天。我感到爸爸妈妈对我有说不完的话,也想听关于我的一切,所以有时这种聊天我就成为主角,而且会通宵达旦。爸爸妈妈精力不济,就轮换去休息,轮换和我聊天,而我则始终在聊天,直达天明。
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八十年代的一次回家,到返厂时爸爸送我到火车站,火车徐徐开动,爸爸在站台外栅栏边向我挥手送别,我在车厢里透过窗户远远看见大风吹乱了爸爸的头发,爸爸的头发已经花白,我猛然感觉到,爸爸已经老了!一丝酸楚涌上我的心头,我顿时感到难受极了,这种难受的感觉一直伴随我多年。
爸爸六十岁时,我发现爸爸用筷子、写字时手发抖,我问爸爸,爸爸说是脑血管硬化。四年前,爸爸关节变得僵硬,手抖更加严重,被医院确诊为帕金森综合症,而脑血管硬化正是帕金森综合症的诱因。三年前的一次摔跤,造成爸爸股骨头粉碎性骨折,手术之后再也不能站立,更不能行走。从此爸爸再也没有回过梦园小区的家,而辗转于康复医院、成都傣家楼老人公寓、铁路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长期的卧床,使爸爸体质严重下降,内部脏器功能急速衰竭,各种疾病不断蔓延。在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医疗诊断书上,爸爸所患疾病包括癌性胸水、帕金森综合症、肾功能不全等26种之多。爸爸于2011年2月住进铁路医院,最怕打针的爸爸每天被输液扎针,承受着时有发生的感染引发的高烧、蛋白丢失造成的水肿以及长期胸腔积液的侵扰。
当天下午,亦康、陈康携外孙女函函去了医院,陈康给爸爸敬了一支烟,爸爸抽得很香,不幸这支烟成了爸爸有生之年抽的最后一支烟。
2012年8月8日凌晨3时,饱经折磨的爸爸终于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爸爸虽然去了,却给儿女们留下了许许多多宝贵的精神财富,留下许许多多难以忘怀的珍贵记忆。…
爸爸住院期间, 妈妈多次去医院看望爸爸。四爸两次专程来蓉看望爸爸,亦康、陈康三次来蓉看望爸爸。大姐、二姐多次前去看望照顾爸爸。从美国回国探亲的学锋、嘉兰,在蓉的筱玲、亦青、亦松也去医院看望了爸爸。
忘不了雪儿每次去看望祖爷爷时,爸爸脸上露出的久违的喜悦!见到雪儿,爸爸总是满脸笑容,伸出手去拉住雪儿的小手,久久地不松开。雪儿也很喜欢祖爷爷,每次我要出发去医院前,只要雪儿在家,她都会跑过来对我说:我要给祖爷爷带句话, “祖爷爷打针不要怕痛!”“祝祖爷爷早点好!” 。
爱儿疼儿,父亲给了我们伟大的父爱,善解人意,是爸爸最令人尊敬的品德, 爸爸把爱心和同情给予了周围!
爸爸,可敬可亲的爸爸,您的音容笑貌永远长存我们心中,我们永远怀念您! 爸爸,爱儿疼儿的爸爸, 您对儿女深沉而细腻的伟大父爱,将永远温暖着我们的心,永远激励着我们,去书写正直,丰富,多彩,幸福的人生篇章!
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珍贵的瞬间,祝愿爸爸在天国也如此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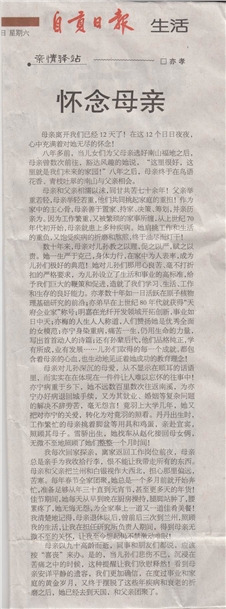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