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托尼·朱特:轮椅上的知识分子
纪念托尼·朱特:轮椅上的知识分子
核心提示:知识分子的责任难道不是要永远站在受害者的一边,在一堵墙和一个蛋之间永远选择站在蛋那一边么?

在2005年出版的《战后欧洲史》中,托尼·朱特(Tony Judt)还在感叹欧洲大陆知识分子群体的式微。一个世纪之前的欧洲,在维也纳、柏林、布达佩斯、还有巴黎,在这些欧洲的重要城市中涌现出了知识分子踊跃参与政治的第一次热潮,但在随后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知识分子的后继者们对马克思主义、极权主义、人权和经济转型等热点问题已经毫无兴趣。
知识分子即便没有消失,也已经被迅速边缘化,他们能起的激励作用虽然没有消失,但是却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该把人们引向何处。他甚至有几分戏谑的口气说,现在欧洲知识分子唯一能把自己的道德真诚和普遍政治结合起来的领域就是外交事务,这样就不用考虑本国内部政策制定时的大量需要妥协的因素。2010年8月6日,这位对美国外交政策、以色列和欧洲未来等一系列问题都有着深刻犀利看法的学者和知识分子托尼·朱特在纽约曼哈顿的家中去世,享年六十二岁。他的去世无疑又加深了我们对知识分子群体日益衰落印象的认识。
一、轮椅上的知识分子
托尼·朱特于1948年生在伦敦犹太中产阶级家庭,父母虽然没有宗教信仰,也很少沾染政治,但却鼓励他参加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多交朋友。不久之后,年纪轻轻的朱特成为了一名犹太复国主义的狂热追随者。1967年六日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他以翻译的身份志愿参加了以色列国防军,正是在此时他才惊讶地发现了许多以色列士兵的暴虐和傲慢,从此改变了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信仰,意识到以色列对犹太人、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造成的巨大伤害。战争结束后,他返回英国,进入剑桥大学,于1969年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又去巴黎高师深造一年,重返剑桥大学,并最终与1972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
从这种游历式的学习过程中,我们仿佛嗅到了朱特终生的学术兴趣,事实上,他的一生所著之书大都是关于法国和欧洲历史。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法国左派,他最有名的几本著作是出版于1994年的《并非完美的昔日:1944—1956法国知识分子》、1998年出版的《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新星出版社2007年9月版)以及2005年出版的煌煌巨著《战后欧洲史》(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版),后者令他荣获了汉娜·阿伦特奖,也入围了普利策奖,奠定了他欧洲史研究领域独一无二的地位。
朱特并非是一个书斋型的学者,像他的好友爱德华·萨义德一样,他无时无刻不关注外界局势的变动,尤其对巴以冲突,欧洲统一,美国的霸权都有着极为敏锐和深刻的观察。2008年朱特和霍金一样患上了罕见的“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全身无法动弹,身体丧失了对肌肉的控制,四肢瘫痪,只有头颅和头脑中思想仍预示着这个人的生命仍然存在。
身在轮椅上朱特,依靠着呼吸机维持生命,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写作和思考,他用口述的方式完成了大量的文章,在《纽约时报》上刊载。在今年一月份的《纽约时报》中,他还很乐观:“比起其它致人于死地的大病来说,在健康不断恶化的过程中,我的病还能让我自由思考,不适的程度也最轻。”不料时隔几月,我们再也听不到这位身患重病的知识分子振聋发聩的声音了。
二、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欧洲的重建
朱特的学术生涯始于他对法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独特兴趣,这种兴趣源于法国大革命对欧洲历史施加的强大影响,用朱特的原话说就是:“对1789年巴士底狱陷落以来的10年法国史的理解,具有和政治理论与实践同等重要的地位。同时,不仅限于法国——此后两个世纪里,对法国大革命的恰当解读在许多情况下给世界各地的激进和反动思想制定了意识形态纲领。”
朱特在他的法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中,重点分析了萨特、波伏娃、布鲁姆、加缪以及阿隆等人,剖析他们在面对二十世纪一系列政治和文化变动时所选择的知识立场和政治阵营,诠释他们心理变化的过程,沉思他们对二十世纪法国以及欧洲历史所产生的影响。二十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不言而喻,对他们的研究也俯拾皆是,而朱特的独特之处在于,他选择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站在欧洲历史的全局视野之上对他们进行剖析。
二十世纪法国的知识分子,身居欧洲的文化中心巴黎,对政治的介入,对各种主义的痴迷,对革命和暴力的颂扬,对战争的清算,对左与右的挞伐都纠缠了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魅力,但是也带来了很多危险性的症状。朱特在《责任的重负》中说:“一种独特的知识分子式的不负责任充溢着我所考察的整个时期,尽管它要晚至战后数十年间才达到巅峰。这种不负责任与其说和知识分子所作的公开选择,或基于选择而陷入的道德混乱有关,不如说与‘知识分子’的这一行本身从事的工作——学者、作家、小说家、新闻记者等等选择思考、选择设法去理解的东西——有关。这把我们带回到我早先关于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观察之中:他们倾向于用最传统的方式反思和回应身边的政治文化分歧与冲突,而不是致力于把民族的关怀引导其他方向,引导到前景更为宽广的轨道上。”
某种程度上说,朱特在法国知识分子的个案研究中看到了欧洲历史发展前景的所有缺点和优点,而且法国这个欧洲的中心之地,在战后历史的发展成为了欧洲恢复活力和多样性并且能对抗美国文化和政治入侵的希望之光。
朱特最初动了书写《战后欧洲史》的念头,是在1989年12月,柏林墙刚倒闭不久,当时他经过布拉格,留意到哈维尔的《自由论坛》的剧作家和历史学家正在强行去除一个“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将它们扔进历史的垃圾桶。这个特殊的时期,东欧的很多国家都要直面后共产主义政治的挑战。这种政治状况让朱特意识到了时代变迁的阵痛和惶惑:“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欧洲正在诞生。这非常明显。但是随着旧秩序的逝去,许多长期以来实行的制度就会发生问题了。
曾经看来是永久性的、不可避免的事情却转瞬即逝。冷战对峙;东欧、西欧分裂;‘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竞争;繁荣的西欧同它东面的苏联卫星国集团的故事是各自分离、互不传播:所有这一切都不再被理解为意识形态需要的产物或政治的钦定逻辑。它们只是历史的偶然结果——而历史却正在将它们推开到一边。”欧洲的历史并非同步的、统一的、同质的历史,各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宗教等都存在各式各样的差别,如何在这种多样性中寻找同一种发展轨迹,一种同一的历史叙事就成为了朱特书写战后欧洲历史的关键所在。
二战以后的对战争的清算,对大屠杀记忆的承担、对苏联共产主义的亲近或恐惧,对美国的印象都可能成为了划分敌我阵营的标准,但是更重要的是,对欧洲文化和记忆的继承才是欧洲历史的重点所在。可想而知,战后欧洲历史的全局该是如何的宏大面貌,对它的整体书写又是如何的艰难,为了弄清欧洲“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们很容易被诱惑去追溯它的内部分裂、不合、决裂。但是,恰恰是这种对历史的追溯让朱特意识到了不同的面向,因为经历过了战争和法西斯主义,“欧洲人对自己的身份和生活的看法取决于让他们团结的事情,也同样取决于让他们分裂的事情——而且他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

三、站在受害者一边
在《战后欧洲史》下卷的最后部分中,有一篇很独特文章《来自死者之屋:论现代欧洲的记忆》,身为犹太人朱特在这篇跋中重点论述了二战后的犹太人大屠杀问题。其中值得提及的是,他提到了这样的一个论点:对大屠杀的承认,是我们进入当代欧洲的门票。欧洲犹太人在二战期间蒙受的灾难无可异议,但是在二战后,对待大屠杀问题上的遮掩和逃避却成为了很多欧洲国家的自然选择。
朱特的愤怒在于无法对这种选择性的遗忘或曰集体失忆症状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对他而言,一个国家只有实事求是地理解历史和记忆,直面大屠杀问题,才能放下过去,继续前进。大屠杀和犹太人的问题是欧洲历史的原罪,我们只能选择面对,而不是逃避。但是对犹太人和大屠杀问题的关注并没有让他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朱特在这方面显示出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所有责任和担当,我们已经了解到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异议和不满,在众多知识分子面对巴以冲突选择闭口不言的时候,身为犹太人的朱特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谴责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造成的侵略和危害。
他先主张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各自建国,后来改为这两个民族应一起建立一个国家,他认为只有这样犹太人才不会成为侵略者和权威者,以此要挟和欺压巴勒斯坦人。作为一个犹太人,却站在巴勒斯坦人,站在受害者的立场思考问题,用他的好友文化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的话说:“巴勒斯坦人的一个大不幸是其所受压迫来自一个罕有的敌人,一个本身也经历过长期和深重迫害的民族。”巴勒斯坦人成为了受害者的受害者。知识分子的责任难道不是要永远站在受害者的一边,在一堵墙和一个蛋之间永远选择站在蛋那一边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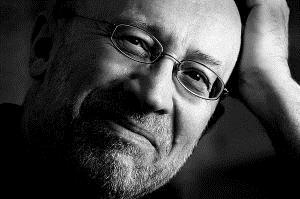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