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延续 文/雷松柏
一说到家,故事可就多了……
在共和国成立前,我家祖祖辈辈是佃的地主的地,住的是地主的房;共和国成立后,地主佃给我家的土地.房租及家用器具都分给了我的祖父和地主家的丫鬟冯氏。听说祖父当时还不敢接手,祖父后来传下:我们从湖广填到四川,不知佃了多少家地主的田,也不知搬了多少次家?切不可忘了那块养育了我们的土地,希望子孙万代再也不搬家,再也不去佃地主家的田土;告诉后代子孙一定要守好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才是我们的家!
转眼间,从49年算起,70年过去了,这个家一路走来,真还有好多去值得回顾,也值得珍惜;尤其分得的那块大田和那座高屋大瓦。据母亲讲,土改过后,58年大跃进,所有从地主家分得的田产都集体入了社,直到1979,改革开放的那一年,那些属于自己的那份田土和房产再次回到了我父母的手中,田土到户,家家富裕,吃的饱饭,穿的好衣。可我家就偏偏惨遭横祸,当年我在县城无线电培训班突然接到父亲在罗家区医院抢救,记得身上钱不多,急忙把手里的双零手表以70元的价格卖给了厨师,我赶到医院,求医生想办法,医生说,只是昏迷,会好的。我苦等了2天,父亲仍昏迷不醒,我又求医生,要求转院,医生说:你有钱吗?转院是要化钱的,你有吗?20岁,20岁对我,钱是什么?没有了救命的稻草,就这样守着无语的父亲,第七天,父亲终于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但就这一眼竞成了我和父亲的永别,父亲无语离世,我看见父亲躺在病床上,双眼留出了血泪,后来才有人告诉我,这是脑内出血最后表现,父亲在痛苦中悄然无声的走了,留下孤独的母亲和我四兄妹,也留下了他那一年种的最好的稻子,就是因为在那一天雷雨交加后的第二天清早,父亲怕稻田满水水把田埂涨垮,才急忙去看稻田水的,才在溜滑的田坎路边摔下崖坎的。后来有人看见父亲站了起来,还看见父亲用田边的水洗了头上的泥巴,从这时起,父亲起身走路不正常了,歪歪倒倒靠着锄头巴一步一步撑回家的。回到家,幺妹妹看见父亲跨过门槛,歪倒在坐椅子上。幺妹急忙把母亲找来,母亲马上叫幺妹找来了本院子的赤脚医生,又把70多岁的婆婆从叔父那边接了过来,经赤脚医生初诊为犯了破伤风,可眼下又无破伤风针药,并提出了马上送公社医院,到了医院,经医生观察,觉得严重,并没有施行抢救,而是请车送到区医院,后来想,如果公社医院先做抢救处理后再送走会不会有一线希望,这自然是自我安慰的说法,在那个贫穷的年月,谁又拿生命当一回事呢?
当时有乡亲资助,我坚信父亲是有救的!如果救活了父亲,那我以后的命运也会随之改写。就如那年他们阻止我参军一样,一切都是上天安排!可是那年月哪有乡亲来出手相救?众亲戚也都刚刚从田土中挣脱出来,他们也只能解决了最初的温饱,家家户户的钱除了购置柴米油盐,交了提留款和购买农具、农肥、种子等,个个也所剩无几,几乎是入不敷出。由此可见,谁又有能力来资助我家呢?一些近一点的亲戚来医院看望的除了眼泪还是眼泪,除了叮嘱我还是叮嘱我;父亲走了,他们来给父亲送葬的除了纸钱也只有纸钱!过了N年以后,我后悔20岁的我竞是那么不懂世事,当时为什么不同母亲作一个破斧沉舟的决定,即使把分得地主家的房子卖了也要转院救活父亲,不能像医生数蔑说我没有钱,凭什么去为你父亲办理转院!可是我可以贷款,我也可以给有钱人下跪求助!母亲和我一样也亳无主见的在医院白熬了七天七夜,20岁的我就这么无知!现在想来,当时的生命太不值钱了,人情太冷漠了,没有现在这么好的社会救助、人情救助和临时借贷的多方合力,尤其在哪个年代,在哪个低层百姓中的医院里是看不到医护人员的抢救急救的紧迫感,这是当时白马袿在我20岁的心里所下的阴影,但记忆中有时又莫名其妙地看到一些工干家属人员在医院里进出,他们的表情和表现完全不一样,他们的行为举止似乎与对待母亲、对待生命垂危的父亲不一样?多年以后才想明白,地位、金钱!细想起来,一个面临生死的人住进了的医院,他们竞连一个最起码的汇诊也没有,更不用说给我们提出什么可行性急救方案,我每找一次医生,医生说3天不醒,要7天、7天不醒要9天,我有时呼唤昏迷中的父亲,父亲还能偶尔睁开眼睛看看我,就是开不了口说话,有时也还能喂些稀饭给父亲吃,再看看他手背市挿了盐水针,以为这样就能救活父亲,缺乏医学知识、急救知识的我,后来多次在医生的说教下,我同意了医生的意见:耐心的等!会有奇迹出现!我同母亲天天在医院求上帝保佑,母亲信耶稣、信耶和华就从这时候开始了。因为反对信迷信,信耶稣、信耶和华就不用烧纸钱,拜佛、拜观音!这样母亲也不不会遭到当年带我时的举报烧纸钱信迷信了,只有信上帝在安全,这是母亲一直开导我的,这也叫科学和环境保护,因为把烧纸钱改为了信上帝,还省了多少陈规陋习!以上这些就是当年的父亲在公社医院、区医院抢救时的一些残缺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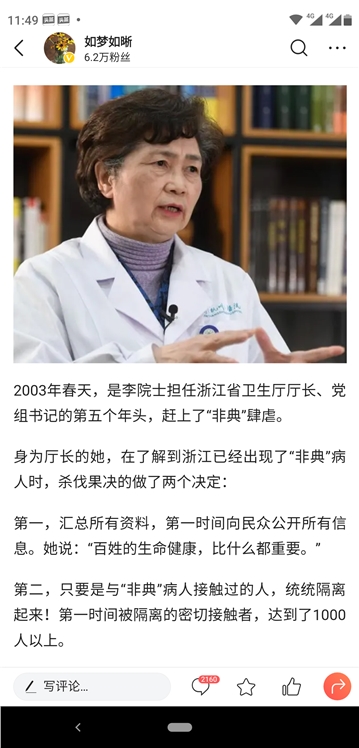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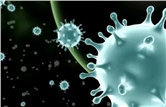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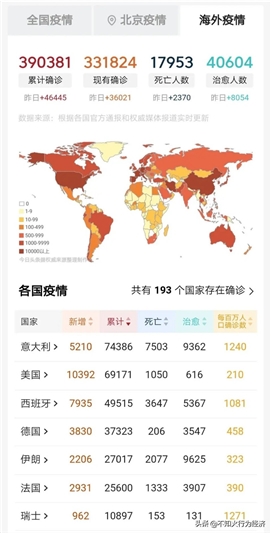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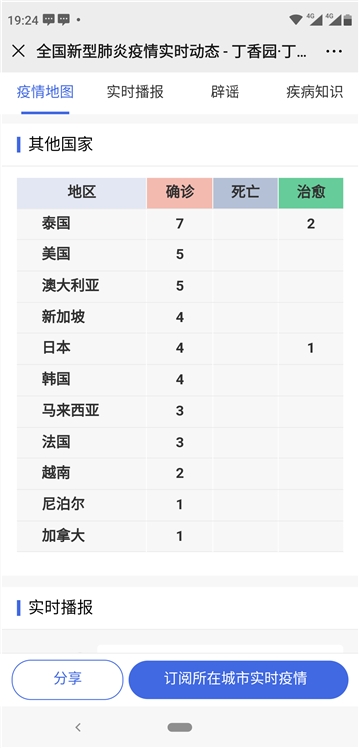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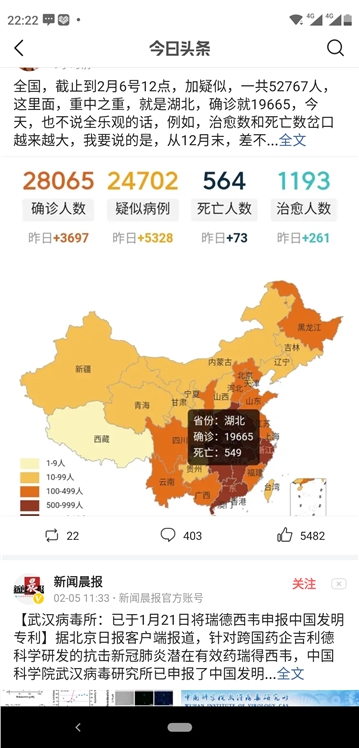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