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父言菊朋言慧珠校长原文今天发在这里纪念言校长
十六年前,我父亲以衰幕之年,在北京三庆园,演出了“全部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之后,就一病不起了!那年他才五十三岁。
我们家是蒙古旗人,世代当着满清的武官,所以我祖父就把我父亲送到陆军贵胄学堂,原想要他走读书做官的路,可是父亲从小喜欢西皮、二簧,以致连陆军学堂的那套戎装打扮都穿不整齐,因此同学们都叫他邋遢兵,他也毫不在意。学堂毕业后,父亲在蒙藏院得了一个小差事,最初月薪才八块钱,要养活祖母、母亲、姊姊、大哥和我一家子,可是他还要挤出钱了听戏,只要谭鑫培老板上台,不管刮风下雪,他总是脚踏钉鞋,手拿一把油布大伞,上园子买张最便宜的票子,靠着大墙坐下去过他的戏瘾。我父亲始终不曾接受到谭老先生的亲炙,他只潜心观摩谭老板的演出,这期间整整有十多个年头。那时我年纪还小,不懂得什么,后来等我年纪大了些,也懂得一点戏了,听父亲告诉我他年轻时看谭剧的心得,才知道父亲的看戏是深入的看戏,不的一般的看戏。
我父亲除了看戏之外,还千方百计的认识了谭老板的左右手——唱花脸的钱金福和唱小丑的王长林两位前辈,从他们嘴里,抄录了谭氏的剧本和学得了谭氏的身段;后来,他又向熟谙谭派唱腔的著名琴票陈彦衡讨教,尽得谭派发音方法和运腔的妙处;同时我父亲又和谭氏合作最久的杨小楼和王瑶卿结交,希图从他们那里得到片言只字,来增加自己对谭派戏的理解;总之,凡是对他学谭有利的事情,他总不辞辛苦,全力以赴,这样,“谭派名票言菊朋”的声誉,也就在北京京剧界渐渐传开了。
一九二三年,梅兰芳先生第五次在上海演出,因为王凤卿先生有病不能南下,北京有位名士就介绍我父亲和陈彦衡先生去协助梅先生演出,双方言明,我父亲的月薪是三千块钱,比他原来的月俸不知要大多少倍,我父亲为此还大费踌躇,因为那时候一个所谓官家子弟下海唱戏是件很严重的事情;况且当时正传闻我父亲要升科长,他怎么可能丢弃这个机会呢?后来,辛亏那位名士和我父亲的上司相熟,说可以设法为他请假两月,唱戏回来保他官复原职,于是,我父亲也就欣然就道了。
我父亲在上海初次演出的两个月当中,除了和梅先生合演《探母汾河湾》等戏外,也演出了谭派应工的《卖马》《骂曹》《战太平》《定军山》等戏,他老人家的戏和陈彦衡的琴,都得到了观众的好评;正当我父亲演出演的高兴的时候,衙门里忽然给他撤了差了,原来旧上司调了差事,那位新上司就以“请假唱戏,不成体统”八个字,把我父亲裁掉,于是我父亲就不得不“下海”正式唱戏了!这是他一生精力最为饱满,信心最强,也是最用功的时期,他一心想继承谭鑫培,做一个好演员。
我父亲享名之后,更加勤奋了,那时在我北京的老家里,傍晚,我放学回家,往往人未进门,就已经听见天井里一阵匀称而快速的棒打声,原来父亲和钱金福的儿子钱宝森在练把子功;有时,厢房里传来了一声声清润动听的白口:“啊,妈妈,儿子把你认下了,你可不要忘了我啊!”于是另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答道:“啊老老,儿子把我认下了,我哪里会忘了你吆!”原来父亲正和王长林的儿子王福山在对《天雷报》的词儿。到了晚上,灯下,我们兄妹二人在温习功课,父亲就在天井里调嗓练功;逢到风雨如晦的日子,他就站在檐下,我只要一听见父亲高唱“一轮明月照窗下,陈宫心中乱如麻......”的时候,就禁不住为他凄凉苍劲的歌声所吸引而不觉神往了。
有时候,我一觉醒来,朦胧中看见一个身扎大靠颔下长须的人,站在床前对我说:“唉,这孩子睡觉不知道关灯,真太阔气了!”原来父亲还没有睡,正在练《定军山》呢!估计这时间总在深夜一两点钟。有时候,我也被一阵疾风骤雨般的鼓声惊醒,原来父亲在练《打鼓骂曹》中的“渔阳三通”。父亲常说,在“骂曹”这出戏中,祢衡无端遭受屈辱,他一肚子闷气真到打鼓这一会见,才得一吐为快,也是这个人物显示才学,一露光彩的重要时刻,所以这个鼓非打的听者动容不可;父亲还说他的腕子没力,只有勤练,才能弥补这个缺陷。
记得是在抗日战争后的一年,我曾和父亲在上海黄金大戏院同台演过三天戏,第一天是我自个儿的《扈家庄》;二三天是父女合演的《打渔杀家》《贺后骂殿》,在排练《打渔杀家》到萧恩嘴里念“也......罢,待为父送你回去!”以后,紧接着,场面上要“刮儿......仓”、“刮儿......仓”地连打两下锣,父亲看我动作不很确当,就问我,你知道场面上为什么要打这两下锣?我说:不知道!父亲就说:那是因为萧桂英尽力用橹把船刹住,不让她父亲掉转船头把她送回家去的动作做个衬托。在这两个动作之后,萧桂英就要念“孩儿舍不得爹爹......”可是我念了好几遍,父亲都说不对,他说王瑶卿先生就不这样念,王大爷念到“孩儿舍......”时突然拔高,把父女之间难舍难分的感情,全部集中在这个“舍”字上,然后在“爹爹”两字上放声一呼;这样跟着场面上一声“扒拉......青仓”,老生萧恩口中那声悠扬而凄凉的哭头才能托的出来。父亲这番话,给我印象很深,至今每当我念到这句白口时,感情还会立时涌现,不觉热泪盈眶。
我父亲常带我们兄妹们带什刹海去玩,那里集中了北京的各种杂耍和家常面点,我们刘宝全《长坂坡》《别母乱箭》等,听完了,就小摊上吃碗面或豆腐脑,父亲还说:刘宝全的玩意里面有谭鑫培、杨小楼的东西。有一次,我们听了刘宝全的《大西厢》回来,他不住哼着“二八的俏佳人她懒梳妆......”的调子,他喜欢刘宝全圆转浏亮的歌喉,和他那种似在板上而又不似在板上,自然而又动听的曲调,他说刘宝全口中的赵子龙,同样具有舞台上杨小楼那股叱咤风云的气概,在描述人物上,刘宝全口中的赵子龙,往往能跟着情节的发展,越来越生动地描绘在听众眼前,使你不能忘记,杨小楼的赵子龙也是如此。当其初出场时,在一台人中,杨小楼只亮一个赵子龙的侧像,很难让人注意,差不多的观众还不知道杨小楼站在那里哪?可是随着剧情的发展,虽然满台的人,你却只看见一个杨小楼在台上活动,他的光彩压倒了所有的演员。我父亲就是喜欢杨小楼善于把精力集中到剧情到达高潮时神彩毕露的表演。在“定军山”中,他吸收了这种表演方法,父亲演黄忠接到夏侯渊书信之后,随着锣鼓的节奏,做着思索计谋的表情;跟着锣鼓越打越紧,动作也越来越美,最后忽然一个亮相,眼神一亮,就非常明确的告诉观众,计谋已定,胜利在握了。在表演黄忠下场的时候,父亲也非常喜欢杨小楼台步矫健轻快而背上靠旗文风不动的功夫。
我父亲在文化生活方面的兴趣也是很广泛的,他喜欢唐诗,他的那出“吞吴恨”就是根据杜浦《八阵图》诗中“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的意思改写的。他喜欢研究声韵音律,他自己编的“让徐州”“白帝城"就是按他自己的选择的字音制腔的,所以分外动听。他受古文学的熏染很深,在“卧龙吊孝”中那篇诸葛亮的祭文,就是他自己执笔的。他喜欢书画,常说:习字要从正楷入手,就像唱戏要练基本功一样,功夫有了,才能吸收其他流派,达到得心应手、挥洒自如的地步。他又喜欢种花,特别喜欢梅兰竹菊,这种爱好,就像他的唱腔一样澹雅宜人。
我父亲四十岁以后,由于环境不好,心情欠佳,体力日衰,就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改走精致纤巧,讲究韵味的路子,又引起了北京一些保守派的非议,他们认为言菊朋既然学的谭派,就只能做谭派的“孤臣孽子”,不能有所改革,他们把言腔斥为怪腔,口诛笔伐,不遗余力,加上我父亲个性耿直,不善交际,所以约他演戏的人就越来越少了!那时候,红角儿在夏天和大冷天是不唱戏的,可怜我父亲就连那种日子都不大轮的到,时常在腊月尾边,我父亲望着那雨雪霏霏的天空,眼看还没有人上门来约他演戏,就仿效古人“插了梅花便过年”的办法,折枝梅花往瓶里一插,说声:“唉!今年又要依靠梅花点染年景了!”那时不但没人上门来请他演戏,后来就连帮他调嗓、替他拉胡琴的人都找不到了,那些琴师们说:言三爷老不上台演戏,傍着他没有什么意思,而且言派戏九回十八转,真伺候不了!
我父亲虽然在心境非常恶劣的时候,仍然很有幽默感,爱和孩子们逗笑,譬如北京那些专卖上品的店铺,往往取些“青云斋”之类的吉祥市招;有一次我父亲上街买鞋,我们问他上那去买呀?他就说:上“低头斋”去!我们就知道他上天桥地摊去买鞋了!晚年,他绝望空虚之余,笃信佛学,自称老和尚,大有冷眼看世情之慨!
有一年,我父亲到南京演戏,我们一家人也就跟到了南京。一天,突然一位同台的演员把我父亲拉回家来,原来我父亲因为满腹牢骚,恰好经过励志社门口,就指着里边骂:“你们配谈新生活,你们连什么叫好戏都懂!”辛亏那位同台的演员跟卫士打招呼,说父亲喝醉了,才把他拉了回来。
我觉得我父亲晚年的“骂曹”和“卖马”最好,他在生活中经过一番波折,饱谙人情冷暖之后,已能把剧中人的心情和自己的心情溶而为一了。在“骂曹”中,他把祢衡怀才不遇,无端被人贬辱的心中愤懑不平的情感体会得最为深刻。在“卖马”中,他那两句“遭不幸困至在天堂下,还你的店饭钱无奈何只得来卖它!”听了令人落泪。
我学戏的时间很晚,十七岁才开始,原因无他,就是我父亲不愿我做坤角,已免辱没家风。在我刚学戏的时候,因为自己十分崇拜程砚秋先生的艺术,所以拼命学程腔,而在学的时候,也根本不考究其神韵,只是逼住嗓子想把它学像。学了一个时期,像是有点像了,但自己的嗓子确越逼越细,越来越不得劲。有一天父亲发现了这个情况,就很耐心地开导我,指出这样学程派一辈子也学不好,同时像我详细地分析了自陈德霖、王瑶卿,以迄梅、程、荀、尚各派的渊源和特色。再说明梅、程所以能够在王瑶卿之后发展成两大流派,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够充分运用自己的天赋,而不是依样画葫芦。程先生的嗓子差,为了弥补这个先天不足,他就接受了王瑶卿前辈的建议、帮助,自己再穷钻苦研,不断的加以丰富,加以发展,终于自成一家。梅先生的嗓子好,他创造的又是另一种特色,因为天赋不同,所以所走的道路也不同,而我的嗓音,比较清亮,根据上面所讲的道理,就应当宗梅,而不应该宗程,否则,就很难得到应有的发展。
我父亲的这番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从此我就改弦易辙,潜心学梅。二十年来,我之所以能在艺术的道路上勉强跟住同辈艺人之后,除了诸位老师的尽心传授之外,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于我学戏的时候,走准了道路,这样就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而这,应该归功于父亲的训诲,如果没有他老人家的教导,我就不可能一心一意毫不动摇地按着这个方面走下去,那末所得到的结果,自然也不会跟今天相同。
事实上,他老人家要我弃程学梅,是不是他厚梅薄程呢?绝对不是!他之所以要我这样做,完全是根据上面所说的真理,无论学哪一家哪一派,都必须结合自己的特有的条件,而不能削足适履;同时在学习的时候,又必须求其神似,而不能求其貌似,所谓“神似者是佳品,貌似者是下品”,也就是这个意思。
关于父亲的艺术,我想谈的还很多,容我慢慢的回忆,有系统地整理,并向父亲的老友以及同台过的老前辈请教,和哥哥(言少朋)、嫂嫂(张少楼)以及言派爱好者共同研究。
一九五九年八月纪念父亲七十寿辰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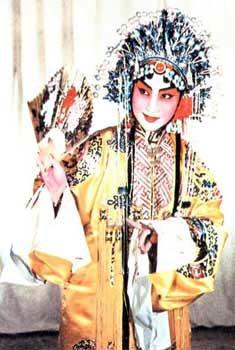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